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docx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docx
- 文档编号:9159262
- 上传时间:2023-02-03
- 格式:DOCX
- 页数:9
- 大小:24.03KB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docx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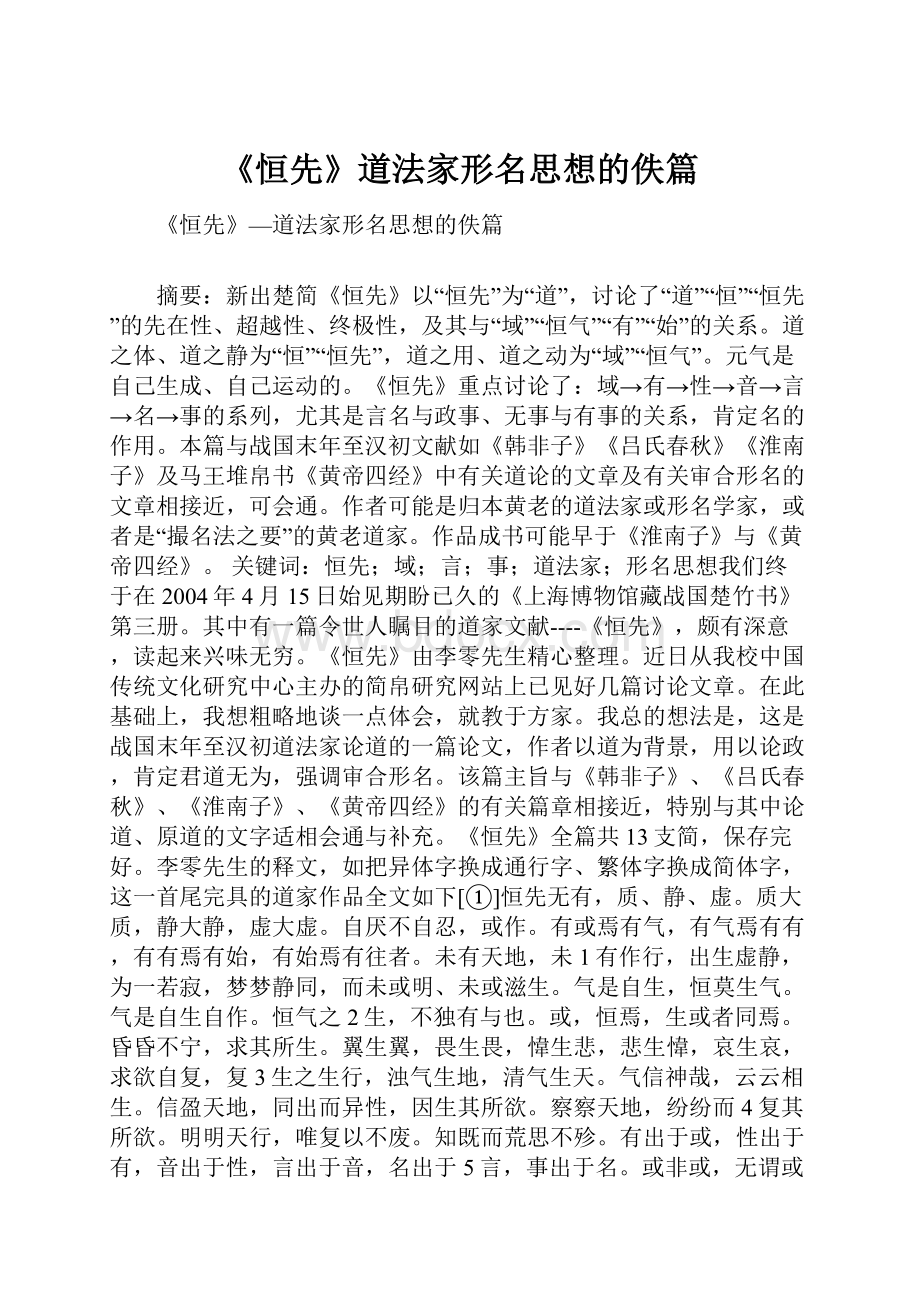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
摘要:
新出楚简《恒先》以“恒先”为“道”,讨论了“道”“恒”“恒先”的先在性、超越性、终极性,及其与“域”“恒气”“有”“始”的关系。
道之体、道之静为“恒”“恒先”,道之用、道之动为“域”“恒气”。
元气是自己生成、自己运动的。
《恒先》重点讨论了:
域→有→性→音→言→名→事的系列,尤其是言名与政事、无事与有事的关系,肯定名的作用。
本篇与战国末年至汉初文献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有关道论的文章及有关审合形名的文章相接近,可会通。
作者可能是归本黄老的道法家或形名学家,或者是“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
作品成书可能早于《淮南子》与《黄帝四经》。
关键词:
恒先;域;言;事;道法家;形名思想我们终于在2004年4月15日始见期盼已久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三册。
其中有一篇令世人瞩目的道家文献----《恒先》,颇有深意,读起来兴味无穷。
《恒先》由李零先生精心整理。
近日从我校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简帛研究网站上已见好几篇讨论文章。
在此基础上,我想粗略地谈一点体会,就教于方家。
我总的想法是,这是战国末年至汉初道法家论道的一篇论文,作者以道为背景,用以论政,肯定君道无为,强调审合形名。
该篇主旨与《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四经》的有关篇章相接近,特别与其中论道、原道的文字适相会通与补充。
《恒先》全篇共13支简,保存完好。
李零先生的释文,如把异体字换成通行字、繁体字换成简体字,这一首尾完具的道家作品全文如下[①]恒先无有,质、静、虚。
质大质,静大静,虚大虚。
自厌不自忍,或作。
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
未有天地,未1有作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梦梦静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
气是自生自作。
恒气之2生,不独有与也。
或,恒焉,生或者同焉。
昏昏不宁,求其所生。
翼生翼,畏生畏,愇生悲,悲生愇,哀生哀,求欲自复,复3生之生行,浊气生地,清气生天。
气信神哉,云云相生。
信盈天地,同出而异性,因生其所欲。
察察天地,纷纷而4复其所欲。
明明天行,唯复以不废。
知既而荒思不殄。
有出于或,性出于有,音出于性,言出于音,名出于5言,事出于名。
或非或,无谓或。
有非有,无谓有。
性非性,无谓性。
音非音,无谓音。
言非言,无谓言。
名非6名,无谓名。
事非事,无谓事。
详宜利主,采物出于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
天之事,自作为,事庸以不可更也。
凡7多采物先者有善,有治无乱。
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
先有中,焉有外。
先有小,焉有大。
先有柔,焉8有刚。
先有圆,焉有方。
先有晦,焉有明。
先有短,焉有长。
天道既载,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
恒气之生,因9言名先者有疑,巟言之后者校比焉。
举天下之名虚树,习以不可改也。
举天下之作强者,果天下10之大作,其尨不自若作,庸有果与不果?
两者不废,举天下之为也,无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
11举天下之性同也,其事无不复。
天下之作也,无许恒,无非其所。
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恒而果遂。
庸或12得之,庸或失之。
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与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
13一、“恒先”与“道”的形上、超越、绝对、无限性本竹书“恒先无有”之“先”字与“无”字字形上有明显差别。
马王堆《黄帝四经》的原整理者因其中《道原》篇首“恒先之初”的“先”字字形与“无”字相近,以“恒先”为“恒无”,见1980年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帛书》。
陈鼓应先生着《黄帝四经今注今译》亦用“恒无之初”。
李学勤先生据同一帛书图版前二行“柔节先定”句,定“恒无之初”为“恒先之初”,并在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之《马王堆汉墓帛书·道原》公布。
在此前后,余明光、魏启鹏先生等均释“恒无”为“恒先”。
李零在此次竹书《恒先》释文中,同意李学勤“恒先为道”说,并进而指出“恒先是终极的先”。
本竹书1至3简与帛书《道原》篇首数句有一定的理论联系。
《道原》篇首:
“恒先之初,迥同太虚。
虚同为一,恒一而止。
湿湿梦梦,未有明晦。
神微周盈,精静不熙。
故末有以,万物莫以。
故无有形,大迥无名。
天弗能覆,地弗能载。
”[②]关于“恒”字,黄老帛书中多见,如恒先、恒一、恒常、恒事、恒位等等。
《恒先》与帛书《道原》一开始都讲天地未形之前太虚的混混沌沌状态,“湿湿”即“混混”,两书均用“梦梦”,均有“虚”“静”的表述。
《道原》“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先》则谓“虚”“虚大虚”。
“迥同”是通同,无间隔的状态。
至于“静”,李零隶定为“寈”,释为“静”,李学勤释为“清”,直接讲清、虚、一、大[③]。
我以为还是依李零释“静”为好。
无论是《恒先》所说的未有天地之前的“静”“静大静”“虚静”“出生虚静,爲一若寂,梦梦静同”,还是《道原》“神微周盈,精静不熙”,都是讲天地万物未形之前的太虚的至静至寂状态,也是讲终极的“道”体在没有作用、动作之前的形态,讲“道”的根本特性即是静止、静谧。
此处“静”比“清”好。
参之通行本《老子》第16章“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与第26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等内容,可知“静”所反映的是超时空的“道”本体的绝待的与普遍的特性,圆满自足,无为无言。
而《老子》第39章“天得一以清”云云,是讲天、地、神、谷、万物离不开道,“清”只是道下的“天”得“道”之后的状况。
“清”又是“气”的一个特性。
所以,“静”与“朴”“虚”等价,是直接表述整一未分化的、末动作的、根源性的、超越性的“道”的。
这里还有关于“”的释读。
李零指出字形似“朴”,但有区别,不妨释为“质”。
李学勤、廖名春等释为“朴”[④],李学勤认为可以释为“全”,“大朴”即是“大全”。
方之《老子》第32章“道常无名。
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之”,第37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等,似以释“朴”为上。
首句三个“大”字,李学勤、廖名春释为“太”,其实不必。
此二字可互通,但《老子》凡言“大”字处亦不必改为“太”,如“大道”“大白”“大音”“大象”等,似仍如第25章“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云云。
故首句似应为“恒先无有,朴、静、虚。
朴,大朴;静,大静;虚,大虚。
”这句话并本体论与宇宙论一起说,是中国特有的“本体--宇宙论”的讲法,即现象世界的形而上的根据和根源、动力是“恒先”即“道”。
“道”是“恒常”“恒在”“永恒”的普遍的,是永远遍在的、与现象界同在的那种存在,同时在逻辑上与时间上都是先在的,故说“恒先”。
“恒先无有”句,“无”是动词。
这四个字讲“恒先”与“有”的区别。
即是说,“恒先”是“无”,无形无名,是超乎“有”的。
“恒先”是世界的本根、本体、本源、总动力,是在逻辑上独立于、超越于“有”的现象界之上,又在时间上早于有形天地万象之前的,是产生天地万象的母体。
这种独立不苟、浑朴、静谧、虚廓、无所不包的“道”,是朴、静、虚的极至。
与浑朴相对的是明晰与分化,与静谧相对的是活化与躁动,与无限虚空相对的则是有形有限的杂多、实有。
在一定意义上,“道”就是“大朴”、“大静”、“大虚”,即非分化、非运动、非实有、非有限性的整体。
“大朴”等既是道之特性又是道之名相。
《恒先》首句偏重于讲道的原始性、绝对性、无限性、先在性、超越性、终极性,是最高的哲学抽象,偏重于讲道之体。
以下第二三句则讲道之用。
当然体用并不能割裂。
二、“或”范畴及“域”与“恒气”之自生自作“或”字全篇有12个第1简两个:
“或作。
有或焉有气”;第2简两个:
“而未或明、未或滋生”;第3简两个:
“或,恒焉,生或者同焉”;第5简一个:
“有出于或”;第6简三个:
“或非或,无谓或”;第12至13简两个:
“庸或得之,庸或失之”。
李零先生指出:
“‘或’在简文中是重要术语。
它是从‘无’派生,先于‘气’‘有’的概念,从文义看,似是一种界于纯无和实有的‘有’,或潜在的分化趋势。
”[⑤]李零谨慎地表达了他的看法,又讲气从“或”生,“或”指将明未明、将生未生的混沌状态,又讲“或”属于“恒”,创造“或”的力量来自“恒”。
廖名春、李学勤、朱渊清、李锐等将“或”释为“域”。
[⑥]廖名春认为,“或”即“域”之本字,即四方上下之“宇”,即空间,即《老子》第25章之“域中有四大”,又说《淮南子天文》“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相当于《恒先》之“恒先无有”、“域作”、“有域,焉有气”。
关于第二简“而未或明、未或滋生”之两“未或”,我同意廖名春、李锐的看法,看作习语,视为“未有”,此处两“或”字不是哲学范畴的“域”。
至于第12至13简的两“或”者,整理者并未视为哲学范畴,亦仍作“或”。
现在看来,可以作为哲学名相“域”的,有第1、3、5、6简的八个“或”字。
我们依次来讨论。
第1简:
“自厌不自忍,域作。
有域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
”我认为,“域”是一个“场”或“场有”,不仅是空间,而且是时间。
这里说的意思是:
“道”自圆自足、不变不动,同时也可以发作、自己运动,“道”之发动即为“域”,亦是“域”之作兴。
“域”在这里是“不自忍”、初发动的“道”。
《老子》第25章讲“域中有四大”,作为宇宙的“域”包涵了道、天、地、人。
可见,“域”与“道”是可以互换互涵的,“域”是静止不动的“道”的发动状态。
道之体、道之静为“道”,道之用、道之动为“域”。
有了“域”就有了时间、空间,有了时空就有弥沦无涯的气充盈其间,有了作为物质与精神之一般的“气”,就有了作为现象世界的一般之“有”即总有、大有,这就标志着宇宙的开始,有了开始就有了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运动。
此即为道之用、动→域→气→有→始→……。
第2至3简: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
气是自生自作。
恒气之2生,不独有与也。
域,恒焉,生域者同焉……3”气是自己生成、自己运动,是本篇最重要的思想。
前面说“域作”,上文已解域之作即道之作,当然是道自己内在张力产生的运动,而不是超越上帝等外在力量之推动、使动。
这里说的是,气也是如此,自生自动。
气不是他生的,不是外在力量使然,甚至也不是道使它生使它动的。
“恒气”,李零说是终极原始之气,本原之气,可从。
“恒气”就是“元气”。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本篇前三支简所说恒先、恒、道、域、恒气、气,基本上是等质等价的概念,在一个层次上。
域、气、恒气,更好地表示出道的场域、场有、微粒、力量、能量、流动、化育的意涵,是这些意涵的抽象。
《恒先》其实也是一篇“道原”或“原道”,是对《老子》的阐发,必然涉及“道”的意涵及其表达,道与名的关系。
本篇后半段直接说及名与言,其实在一开始就把“道”之别名指示了出来。
从体而言,道是“独”,可称为“恒”、“恒先”,是静止的,寂然不动的;从用而言,道作兴、运动、实现之状况,感而遂通,则可称为“域”、“恒气”。
“域”、“恒气”、“气”等则不是“独”,“不独,有与也”。
它们相伴随而起,但它们也是“道”,是“道”内在的不同能量相感相动使然,故都是自生的,不是他者使生的。
域、元气是道的别名,是恒常恒在的,亦可称为恒。
故不能说是道、恒产生、化生出域、元气。
要之道--恒、恒先道--域、恒气、元气有关5至6简的四个“域”字,说见下。
三、《恒先》之重心在于审合言事第5至7简:
“有出于域,性出于有,音出于性,言出于音,名出于5言,事出于名。
域非域,无谓域。
有非有,无谓有。
性非性,无谓性。
音非音,无谓音。
言非言,无谓言。
名非6名,无谓名。
事非事,无谓事。
详宜利主,采物出于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7”上文说到道、恒、域、恒气、元始之气是同一层次的、同一等级的概念,是并列的非从属的,不存在道使之生的问题;域、恒气、元气只是道、恒的别号、别称。
这里讲的却是“某出于某”的系列域→有→性→音→言→名→事……域←有←性←音←言←名←事……域之后显然是另一层次,在这一层次内有从属、派生的系统,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有”源出于“域”。
“有”是万象大千世界的抽象一般,并非具体之物。
至于以下的性、音、言、名、事则是具体的个别的物事、事体、东西及其属性或特性、音乐或音声、言说或理论、名相或称谓、社会事务的相互关系等。
这当是先秦思想家名实关系讨论的发展,一方面强调名相、名言、概念的自身同一性,另一方面引伸到社会人事管理上,含有循名责实、各当其位、各守其份的意蕴。
这也是孔子以降正名思想之本旨。
《管子》的《九守》篇曰:
“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
名实相生,反相为情。
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
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与老子之“名者实之宾”与上引《九守》“按实而定名”的路数有一点不同,《恒先》在名实相生的基础上更强调名的规定性及名对实的反作用。
除《九守》与《恒先》一样有“某生于某”的论式外,郭店楚简诸篇,特别是《语丛》四篇,有不少“某生某”、“某生于某”的论断。
这里,我只想举《语丛一》之一例:
“有生乎名。
”关于“性出于有”,“性非性,无谓性”。
《恒先》在这里指物之性,也特指人的性情,道与人性的关系。
相类似并可用来参考的材料,见《淮南子》之《原道》:
“……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
是故达于道者,返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
以恬养性,以漠处神,则入于天门。
”又说:
“嗜欲者,性之累也。
”该篇提倡护持、反诸人的清净本性。
《俶真》:
“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而游心于虚也;达人之学也,欲以通性于辽廓,而觉于寂漠也。
”《泰族》则主张因人之性予以教化、引导,“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
”
关于“音出于性”,“音非音,无谓音”。
《吕氏春秋》提倡正位审名,并以正音为譬。
“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也。
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
”该篇进而论证治国立官,各处其职。
《淮南子》指出,丰富的乐音源于五音,五音又取决于处于中道之宫音。
“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天下为之圈,则名实同居。
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故音者,宫立而五音形矣……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
”足见道与性、音之关系的讨论与名实、名形关系的讨论,在当时都很常见,且可以引向政治论说。
战国末期、秦汉之际道法家习惯于这种方式。
帛书《经法》之《名理》篇讲执道者虚静公正,“见正道循理,能举曲直,能举终始。
故能循名究理。
形名出声,声实调合,祸灾废立,如影之随形,如响之随声……”帛书统说形名声号,依此而定位并贯彻始终。
关于“言出于音,名出于言,事出于名。
”“言非言,无谓言。
名非名,无谓名。
事非事,无谓事。
”言、名、事的关系,《韩非子》有一些讨论:
“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
”指言与不言都必承担责任。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形名;形名者,言与事也。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
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受申不害影响,韩非说:
“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又说: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
“名”字可以是名词,指名相,也可以是动名词,指言语所表达的,其内容指道理或名称。
“形”即表现。
在一定场合,“名”就是言,“形”就是事。
在另外场合,形名泛指言事。
“情”指真实状况,实情。
“参同”“参验”“参合”指验证、检验、证明,使所表现与所言说相符合,或者形名指导社会实践。
言自为名,事自为形,审合形名,结果是名至实归,名当其实,如此,君主才可能如“道”的品格,无为而治。
这是道法家形名思想的要点。
《恒先》篇显然是与这些思想可以相通的。
又《吕氏春秋》曰:
“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
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
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这都是一样的主张。
当然,在帛书《黄帝四经》中,关于“形名”,不再分开理解为“形”与“名”,而是笼统指事物的表徵,指言事、名号、政治法律制度,其所强调的是“形名”及其作用的重要性。
在韩非那里也已有了这种意涵。
关于第6简“详宜利主,采物出于作,焉有事不作无事举。
天之事,自作为,事庸以不可更也。
”有了以上关于形名思想的讨论,这句话就比较好理解了。
李零先生的解释,基本上是准确的。
“有事”与“无事”,见上引《韩非子》之《主道》的材料。
《恒先》此句意即:
详查审于事,得其所宜,利于主上。
“采物”即礼制、政务诸事等,都是有为,作为,乃有事,乃臣道,此与无事之君道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有事”即举名,以名举而责事。
帛书《经法》之《道法》有“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形名声号矣。
”又曰:
“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
逆顺死生,物自为名。
名形己定,物自为正。
”黄老帛书诸篇有物恒自正、形恒自定、名恒自命,事恒自定自施的思想,《道原》的“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尤为突出。
《恒先》第7简以下讲的天之事、人之事、治乱问题等等。
第7至8简说天之事是自作为的,自然而然的,意思是人主、明君亦应效法,不可直接挿手具体事务,反而搞乱了政事。
此关乎人世之治乱。
君道无为无事,臣道有为有事。
如《淮南子》的《主术》所说,人主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清静无为,清明不暗,虚心弱志:
“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
”关于第8至9简的“先有中,焉有外。
先有小,焉有大。
先有柔,焉有刚”等,可参《淮南子》:
“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恬然无虑,动不失时,与万物回周旋转……托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刚,用弱而强,转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
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废。
中能得之,则外能收之。
中之得则五脏宁,思虑平……”除《原道》《主术》外,《恒先》与《淮南子》的《精神》《齐俗》亦可相通。
第9简中“天道既载,唯一以犹一,唯复以犹复。
”与帛书《十六经》《成法》篇“循名复一”的思想相接近。
复一就是复道。
这里顺便指出,第10简“言名先者有疑,巟言之后者校比焉”,疑仍是讲的审合名形、言事的。
“校比”也有审合之意。
第10至13简,总体意思仍然是以虚御实,以静制动,以无为统有为,以无事统有事。
这里指出,举天下之事,之作,之为,不要用强力,不要多干预,不主动地改变习俗,不主动去兴起、参与什么或废止、舍弃什么,“无舍也,无与也,而能自为也”,使万事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各司其职,各守其份,自兴自舍,自主自为又不相妨碍。
第13简“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更加重名,即在道之下,以名统事,社会政务在名言制度下自然运转,反而不会紊乱。
如此,言名、事务均不可废,天子、诸侯、士君子各行其道而能相辅相成。
这些思想可与黄老帛书会通,但黄老帛书比《恒先》说得更明确,更丰富。
《恒先》与《太一生水》关系不大,《太一生水》主题是宇宙生成的图式,而《恒先》主要是论述道、名、言、事。
当然,《太一生水》后半也涉及道、天、地、名、事等,讲天道贵弱。
《恒先》全篇布局与黄老帛书《道原》相似,由恒先、道谈起,由道的超越、普遍性、无形无名、独立不偶,讲到其对社会人事的统帅,推崇圣人无欲宁静的品格,得道之本,抱道执度,握少知多,操正治奇,以一天下。
道是人间秩序、人的行为的形上根据。
当然,帛书《道原》没有详论名言形事等。
《恒先》与黄老帛书《经法》中的《名理》、《道法》篇更为接近。
帛书的形名思想强调天下事物在名物制度下,自己按本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恒先》并没有如《淮南子》与《文子》的《道原》那样铺陈,比较古朴;其形名思想也没有如《黄帝四经》那样展开,甚至没有提到“形”字。
我揣测,作者可能是归本黄老的道法家或形名学家,或者是“撮名法之要”的黄老道家,作品成书可能早于《淮南子》与《黄帝四经》。
近读简帛网站上庞朴先生的大文[⑦],很受启发。
庞先生在竹简编联上有改动,即把第8至9简排在第1至4简之后,5至7简之前。
全篇竹简排序改为1-4、8-9、5-7、10-13。
这种编排,颇费匠心,足资参考。
拙文粗疏,不当之处,敬请各位学者、专家批评指正。
注释[①]李零:
《恒先释文考释》,载马承源主编: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287—299页,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②]详见余明光等:
《黄帝四经今注今译》,第203页,长沙:
岳麓书社,1993年3月。
本文所引《黄帝四经》均据此书。
[③]李学勤:
《楚简〈恒先〉首章释义》,见简帛研究网站,2004年4月下旬。
[④]李学勤文见上注。
廖名春:
《上博藏楚竹书〈恒先〉简释》,见简帛研究网站,2004年4月下旬。
[⑤]详见注1,288—290页。
[⑥]李学勤、廖名春文见注3、4。
朱渊青:
《“域”的形上学意义》,李锐:
《〈恒先〉浅释》,两文均见简帛研究网站,2004年4月下旬。
[⑦]庞朴:
《〈恒先〉试读》,见简帛研究网站,2004年4月下旬。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恒先 道法 家形名 思想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Java程序设计》考试大纲及样题试行.docx
《Java程序设计》考试大纲及样题试行.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