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兰河传》教案.docx
《呼兰河传》教案.docx
- 文档编号:9051061
- 上传时间:2023-02-03
- 格式:DOCX
- 页数:19
- 大小:29KB
《呼兰河传》教案.docx
《《呼兰河传》教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呼兰河传》教案.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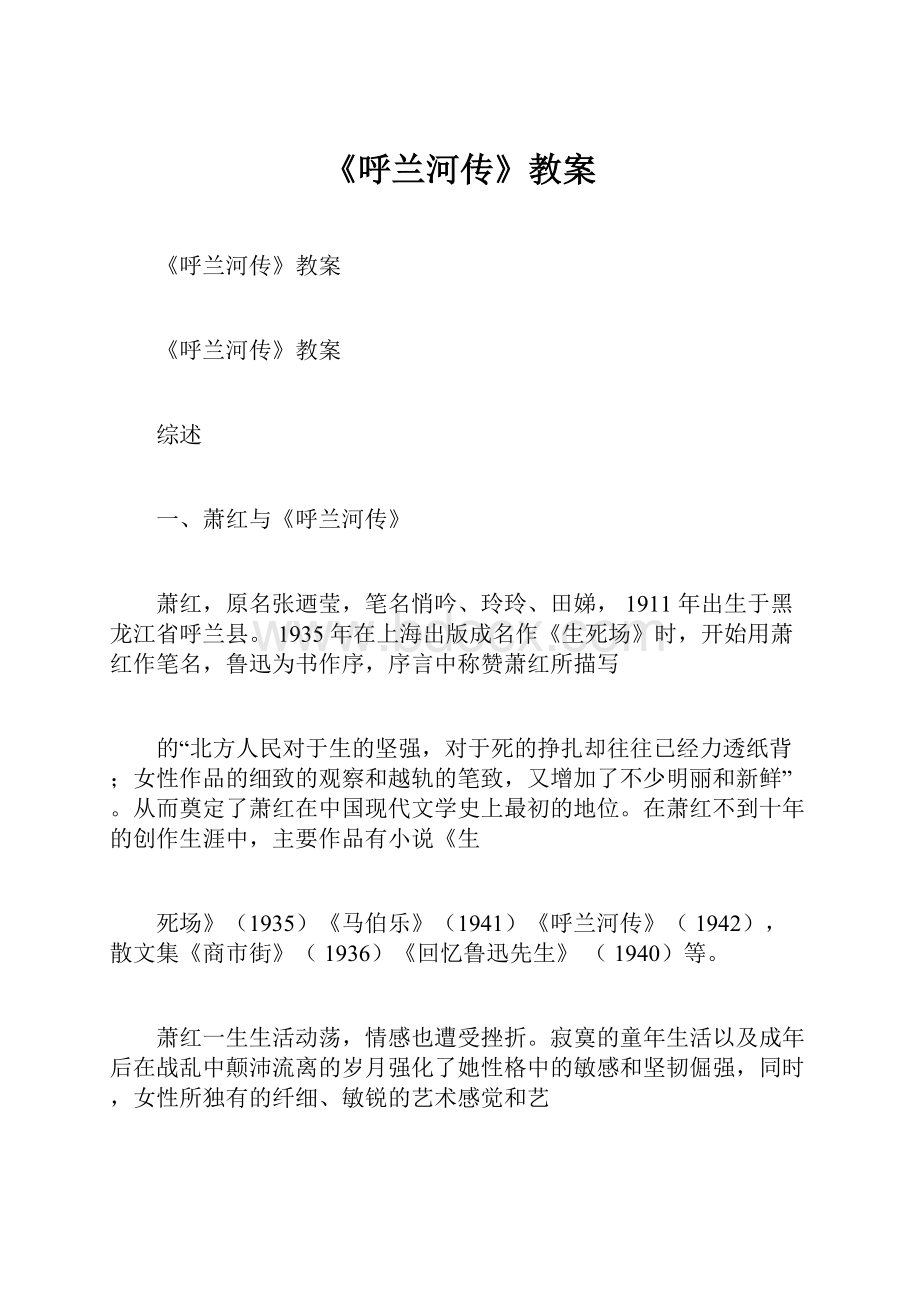
《呼兰河传》教案
《呼兰河传》教案
《呼兰河传》教案
综述
一、萧红与《呼兰河传》
萧红,原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
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开始用萧红作笔名,鲁迅为书作序,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
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从而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初的地位。
在萧红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主要作品有小说《生
死场》(1935)《马伯乐》(1941)《呼兰河传》(1942),散文集《商市街》(1936)《回忆鲁迅先生》(1940)等。
萧红一生生活动荡,情感也遭受挫折。
寂寞的童年生活以及成年后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岁月强化了她性格中的敏感和坚韧倔强,同时,女性所独有的纤细、敏锐的艺术感觉和艺
术感悟能力,使她成为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
在萧红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远离故土,索居香港,在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孤寂的心境中
度过。
1942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怀旧的心情中,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其艺术
上的颠峰之作。
《呼兰河传》融进了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绪记忆。
作品
不着力塑造“典型”的人物,也不刻意丰满故事的情节,而
从叙述的结构章法上突破传统、另辟蹊径,用一种率直的真
实、凄婉细腻的笔触,真实、感人地再现了呼兰河的乡土人
情、风俗习惯。
并通过作者年幼时代的生活和感受,反映出
呼兰河畔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
二、概要
1.小城故事
在《呼兰河传》这部作者晚期杰作中,她以散文化的笔调抒
写了以家乡为原型的“呼兰河”城的“传记”,这“传记”记录了呼兰河的四时风俗,“我”的美丽而寂寞的童年,以及小城里各式各样琐屑平凡的人世悲欢。
小说以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子”为起点,展开了关于呼兰河人日常生活的叙述。
那个当街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时常闹出乱子:
车马倒在污泥中了,救马的与喝彩的,一时热闹非凡,大人们挣扎许久终于过去了,小孩子掉下去又被救起来了,猪淹死了,,大泥坑上总是“盛事”不断,呼兰河人应付着、忍受着,然而,“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大泥坑”也许是一种象征,小城里的人们,也是挣扎在人间,被风霜雨雪吹打着,却又麻木因循地生活着:
卖豆芽菜的王寡妇死了独子,虽然疯了,但依然卖豆芽菜;扎
彩铺的伙计们扎出了富丽的阴宅,却依然在人间辛苦地生老病死;小胡同里一篮麻花,可以惹出一家小孩的追打;一块豆腐也能为人们的晚餐锦上添花,,事实上,呼兰河人对于死后的想像,要比生前的实际生活丰富得多,一年之中必有跳大神、放河灯、唱野台子戏、逛娘娘庙大会等各式各样的“精神盛举”。
对这些以鬼神的名义兴起的人间盛事,呼兰河人乐此不疲。
在自家的后花园内,是有祖父陪伴的多彩童年,后花园外却是荒凉的院落以及穷困租户的别样人生。
长蘑菇的草房子里住着几个漏粉的,旁边的小偏房里住着一家赶车的,他们的日子交织着微末的欢喜和沉默的不幸。
小团圆媳妇是赶车的老胡家为他们的二孙子娶的童养媳,是一个黑忽忽、笑呵呵的女孩子,然而照“规矩”经过婆婆的毒打与烙脚心的“调教”之后,日渐病倒,又经过跳大神、吃偏方、抽帖儿、用大缸洗澡种种奇特的“治疗”,终于死去。
有二伯是“我”家的一位古怪亲戚,他无家无业,居无定所,生活窘迫,甚至有些小偷小摸的劣习,但同时却又敏感而自尊。
他对砖头和云雀讲话,忌讳人家喊他乳名,他年过六旬却被年轻的主人打倒在地,他感到凌辱而想到死,但又缺乏自杀的勇气,最终他的“跳井”“上吊”成为人们的笑料。
临着“我”家后园的磨房里住着冯歪嘴子,他和邻家王大姐不声不响成了家,刚生下的孩子,在零下的温度里只能盖着面口袋取暖,
但这并不妨碍冯歪嘴子对生活的执著,他依然努力拉磨,卖年糕,最终王大姐在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中抑郁而亡,冯歪嘴子和他的儿子们却坚强地活着,,
茅盾在给《呼兰河传》作的序中这样描写呼兰河城的生活状态: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生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的。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到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
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现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
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2.内涵丰富的回忆的诗学
有一类作家几乎完全生活在回忆里,萧红可以说是这类作家的一个卓越代表,《呼兰河传》是一篇典型的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忆之作。
近来学界对《呼兰河传》的研究已充分地探讨了它对于“回忆的诗学”的独特贡献。
谢茂松即认为“回忆”对《呼兰河传》具有总体的统摄作用。
它是一种生命的和艺术的双重形式。
作为生命的形式,意味着回忆构成了萧红的灵魂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正如普鲁斯特在写作中回忆,在回忆中写作进而把回忆当成个体生命的现实形态一样。
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则意味着回忆在小说中承载着基本的结构的和美学的功能。
它生成着或者说决定着小说的技巧。
人的生理或心理性的回忆往往表现为一种非逻辑性的形态,当这种非逻辑性的形态落实在小说中,则体现为心境与情绪的弥漫,在这种弥漫中小说不断闪回既往岁月留给作者深刻印象的那些记忆
场景。
这便是人类本真的回忆在小说中的如实反映。
《呼兰河传》在这个意义上堪称是考察文本中的记忆形态的不可多
得的标本。
在《呼兰河传》中想捕捉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情节性的故事线索是不大可能的。
小说是一系列场景和印象的连缀,是童年镜头与画面的组接。
贯穿的线索不是情节,而是情绪。
而回忆的情绪自有其逻辑,在《呼兰河传》中表现为叙事者的心绪总是在悲凉和温暖两极之间循环。
这种情绪的循环昭示了在回忆性的叙述中,作者总是在过去和当下两个时空不断穿行。
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当下行为,即使是如《呼兰河传》这种童年追忆体小说,在写作时,当下仍然是被作者意识到的一种时空和处境,甚至是有力制约作者正在进行着的创作的现实因素。
我们在《呼兰河传》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回忆总是进出于童年和现实之间,一旦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叙述的调子就逐渐温暖;而每当回忆告一段落,现实处境便乘虚而入,悲凉的情调则氤氲起来,并最终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笼罩着叙事者灌注了全部生命和感情的倾诉。
读罢《呼兰河传》你可能会忘却小说中的全部细节,但那种弥漫的情绪却会长久地滞留在心中。
不妨说,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回忆本身固有的机制。
对回忆的模式的归纳并不意味着“回忆”已完全缝合了小说的全部叙述,相反,看看小说中的哪些部分无法被纳入“回忆”框架,是更有意味的诗学问题。
在《呼兰河传》中,我们发现小说的第五章很难被纳入“回忆的诗学”的范畴。
这一部分讲的是小团圆媳妇的故事,叙事者“我”渐渐隐去,而小说回溯性的限制叙述也渐渐有了全知的味道,小说的调子也开始充满反讽、调侃,甚至幽默。
与前面的叙述“我”与祖父的故事的个人性话语相对照,这一段叙述他者的故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沿用一种“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这
为《呼兰河传》带来了另一种声音。
它超出了“回忆”的叙
述框架,打破了小说自叙传式的自我生命拯救的命意,从而
为小说带来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忆的
模式就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结构框架之中。
《呼兰河传》由
此成为一个几种类型的声音并存的文本。
它容纳了民俗学、
人类学的话语,国民性改造的启蒙主义话语,以及关涉自我
生命拯救的个人性话语。
因此,它其实缝合了萧红的多重的
文化想像。
而多年来对《呼兰河传》各种角度研究之间的歧
异也正根源于此。
(选自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三、艺术风格
1.诗化小说
按照传统的小说观念,《呼兰河传》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
小说”。
它在艺术形式上比较独特,没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和
故事线索,没有波澜起伏的冲突,在叙述上打破成规,以散
文笔致和诗歌的抒情格调描写平凡人物、日常生活,于其中
显示卓越才华。
全书七章虽然可以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个
整体,从“街头巷尾”到“后花园”,从喜庆殡葬到种种“精
神的盛举”,从祖父祖母到我家院里各式各样的人,无不生
动形象、诗意盎然。
萧红以她娴熟的叙述技巧、抒情的散文
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颠峰之作。
我们可以看到,在小说中,呼兰河的社会状貌、风俗人情、平凡岁月均传达着一种情绪,酝酿着一种氛围,独特的情调将人们带到呼兰河的土地上,从中仿佛可以嗅到呼兰河畔的泥土芳香,仿佛可以看到一幅幅展开的北疆风情画面,进而便是对凝重历史的思考。
鲁迅曾称赞萧红的小说具有“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
的笔致”,这其中“越轨的笔致”可看做是对萧红小说别具
一格的行文方式和抒情基调的褒扬。
茅盾也曾评价《呼兰河
传》的文体风格:
“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诱人’些的东西: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对这方面的进一步理解,可以参考以下资料: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
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
萧红
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
“有各式各样
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
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
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
味的艺术世界。
,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
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
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
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
“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
感、失落感。
“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
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
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
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
”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选自徐晓红《论萧红的小
说创作》)
2.儿童视角
《呼兰河传》的艺术风格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儿童视角的运用,这种叙述视角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为呼兰小城的存在方式创造了宽阔的空间。
无论从作者的表达还是从读者的接受来看,它都将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绝佳效果。
我们阅读《呼兰河传》的第一个直观的感受或许是──这部
小说的语言独特,略显稚拙,却又饶有趣味;有点啰唆,却又句式单纯明晰,简洁干净,像一个儿童在絮絮地自言自语。
对
于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作者也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的心理视角来做出情感评价,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
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做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悖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
在课文节选的“小团圆媳妇之死”一节里,可以切肤地感受到这种艺术效果。
只有在还没被尘世干扰过的孩子们的心灵
上,还暂时保留着人际关系的纯正。
“我”和“小团圆媳妇”之间的对视、微笑等有声无声的交流,都是那么的纯净与可
贵,是成人世界所不能理解的真实。
儿童那未被污染的纯洁心灵缩短了他们与人人视为异端的人之间的距离,于是成人所无法体察的真实而残忍的细节落入孩子的视界之中:
只有“我”说小团圆媳妇“没有病”;只有“我”知道她不是掉了头发的妖怪,她的辫子是“剪刀剪掉的”;只有“我”毫
无顾忌地掀开她的棉被,和她玩玻璃球;也只有“我”关心她死去的原因和埋葬的情形,,
而同时,作品中的这种“儿童视角”却又不是一以贯之的,有时作者也会以成年面目插入叙事。
《呼兰河传》属于成年人回溯往事的童年回忆体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童年往事是在成年叙事者的追忆过程中呈示的,这就使文本中的儿童视角成为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
关于这一方面,有学者做了更深入的论述,节录如下,供参考。
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当成年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往事的缅想之中的时候,小说的儿童视角呈现给我们一种令人震惊的儿童所固有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
萧红笔下童年之“我”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所展示的儿童情趣几乎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浸染,从而使《呼兰河传》中的儿童世界表现出具有普泛的人类学意义的生命原初体验,并构成小说中最具有生命和美学认知价值的一部分。
,
回溯性叙事在叙述层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或隐或
显的成年叙事者的声音。
尽管这个成年叙事者并不一定在小
说中直接露面,但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
他必然要
控制和干预他所回忆的往事。
这意味着笼罩在回溯性的叙事
框架中的儿童视角其实是一种悖谬性的存在,就是说它不过
是成年叙事者所拟设的。
我们的困难在于无法确凿地判定究竟哪些是出自儿童本真的感受与观察,哪些更明显带有成年叙事者当下的干预的痕迹。
这涉及了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在诗学上的一个基本性难题。
毕竟是回忆者在回忆,这就是回溯叙事的当下性特征。
叙事者的回忆在叙事层面指向的
是过去的儿童天地,而在本质上则指向“此在”。
回溯性叙事中再纯粹的儿童视角也无法彻底摒弃成人经验与判断的
渗入。
回溯的姿态本身已经先在地预示了成年世界超越审视的存在。
尽管儿时的记忆在细部上可以是充满童趣的,真切的,原生的,但由于成年叙事者的存在以及叙述的当下性,决定了儿童视角是一种有限度的视角,它的自足性只能是相对的。
纯粹的儿童视角或许像保罗·瓦雷里界定“纯诗”那样,只是一个虚拟化的理想存在状态。
只要存在成人世界与儿童所象征的“蒙昧”世界之间的价值分裂,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合一。
,
,从《呼兰河传》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过去的生命境遇如何向此在生成,现时态的生存如何在战争年代依靠向往昔的回溯而获得一种真正的支撑,一个柔弱的女性如何借助童年的记忆在与生存的虚无抗争。
在这个意义上,童年往事不再是一个只滞留在过去的时空中不与当下发生关联的自足的世界,回忆本身照亮了过去,使个体生命的发
源地显得如此炫目,并进而使过去的生命融入“此在”而获得一种连续性。
所谓“生命的流程”的字眼儿从而超越了其比喻性内涵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具体性与生存的本体性。
《呼兰河传》由此讲述了一个生命本身的故事,它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以及人类集体性的大记忆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小说的儿童视角在呈示儿童世界的单纯的美感之外汇入了“回忆”这一更大的诗学范畴。
它讲述的是永恒的关于复乐园与失乐园的故事。
(选自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四、深层意蕴
1.女性的空间
萧红的一生在漂泊动荡中度过,生活的压迫、传统习俗的束
缚以及女性所独有的人生的苦痛始终伴随着她。
她曾经感
慨:
“我是个女性。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
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
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
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
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
觉得,,我会掉下来。
”(聂绀弩《在西安》)
萧红在发自内心的深沉喟叹中,以自觉的女性意识,以自身
“独特的处境和观察事物的角度”深刻地审视着自己以及身
边的女性,在其早期的作品里已非常关注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展示,而《呼兰河传》在这方面尤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本课所节选的章节,是表现“女性空间”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女性的声音尚显薄弱,但是它毕竟发掘出了《呼兰河传》所不同于以往的其他侧面──那就是对于导致女性悲剧根源的思索,并把这种思索与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化视野相融合。
小团圆媳妇刚到胡家来的时候单纯、活泼、健康,却因为“吃得多”“走得快”被认为“不知羞”“不像个团圆媳妇”,从而遭到婆婆的打骂。
婆婆及其帮众们为了帮助小团圆媳妇成
为一个符合传统标准的“小团圆媳妇”而狂热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最终导致小团圆媳妇的惨死。
然而更可悲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对此都不会产生道德和良心的压力,因为她们信守当时社会话语的合理性,她们不仅看不到自己对小团圆媳妇的伤害,反而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
面对小团圆媳妇的死,她们心安理得,甚至多了饭后的谈资。
萧红以敏感的灵魂和细腻的女性视角关注着女性的生与死,同时她更深刻地意识到,千百年来女性的悲剧命运不仅仅是男权文化统治的结果,更是女性对自己被奴役状态的历史性认同所造成的,是女性自己加速了对女性的异化。
这种心理成为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自觉地来规范约束自己和其他
女人,《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就是被女人异化的
典型。
萧红笔下的女性是旧中国社会最常见最普通的女性,不像一
个艺术形象,而就是生活中人。
这群浸没在男权思想里的女
人与封建意识一起构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吃人网,女人
同时既是被吃者又是吃人者,她们是男权传统樊篱中的牺牲
者、殉葬者和异化者。
2.悲悯情怀与国民性批判
呼兰河城似乎凝固在时间之外,呼兰河人平凡卑琐的日子,也是一天天,一年年,循环往复,亘古如斯:
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死了,不过在城边的地上埋了,活着的人哭过以后回家照旧过着日子──“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
老胡家的二孙子娶团圆媳妇了,儿子媳妇就成了婆婆,婆媳之间的折磨与反抗,代代相传;有二伯愤慨着“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居然看上了磨房的磨倌,有二伯不成功的“跳井”和“上吊”,又成为老厨子和小城人长久的谈资,不幸与不幸,也互相推波助澜。
小说呈现的是呼兰河人在历史与命运中因循反复的死水般
的生存状态,用茅盾的话说,《呼兰河传》里面“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
自艾的可怜虫”,虽然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极容易满足”,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生命力特别顽强”。
他们只是照
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生活着,不预约希望,也看不到光明,这种巨大的历史惰性,为呼兰河人原本就灰暗的日常生活笼
上了地久天长的悲凉气息。
萧红对呼兰河人的生存状态充满了悲悯的情怀,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小说中的这种基调,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
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
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作者深深地体验着而不单单是呈现着那浓厚的人生悲凉和空虚,并以她特有的沉郁和永恒的忧患意识发出了慨叹和责问: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
而《呼兰河传》更深层的悲剧意蕴在于揭示出一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下的相互同化和异化、扼杀人性。
这在前面“女性的空间”中已有所涉及,这里再作补充说明。
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
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
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
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
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
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
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
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
与《生死场》中受难后的凄呼厉号不同,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
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
(选自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呼兰城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生活惰性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小城在传统文化覆盖下的丑陋和保守,经由萧红的笔触得以生动而令人触目惊心地展现出来,并且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萧红有意识地在追随鲁迅,有着把深广的忧愤投射于人类愚昧和国民劣根性的创作取向。
鲁迅的影响,“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烛照,使得作家对自己生活过的故乡,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弱点,对桎梏妇女解放的封建礼教,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
于是,萧
红开始了痛苦的反思──探求中华民族如何走向新生,民族性格何以能够得到重塑。
她以睿智的目光洞察了理想和现实
的巨大反差,以决绝的态度揭示了封建道德、传统痼疾的无比
丑陋,由此自然铸成了鲁迅式的、幽默反讽的喜剧风格,《呼
兰河传》就是其贴近《阿Q正传》风格的代表作。
在她看来,这种风格,不只能使人们产生浓郁的沉重感,而且也能让人们获得战斗的愉悦感;对于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这种风格是
再合适不过的利器了,舍它其谁!
,
对于集闭塞、保守、愚昧之大成的呼兰城,萧红没有采取疾言厉色、匕首投枪般的正面批判,而是把穷形尽相的揭露和鄙视憎恨的态度,包藏在调侃反讽、苦涩悲凉的乡土叙述之中。
综观全书,大半以上的叙述,都是调侃反讽的语调,都有弦外之音、弦外之旨。
“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才”,呼兰河的人大概都有夜郎自大的恋乡情结,连街市捡粪的孩子也为“我们的呼兰河”而洋洋自得。
萧红调侃道:
“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他的。
”那给呼兰河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大泥坑,萧红总结了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呼兰河传 教案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城市规划基本知识》深刻复习要点.docx
《城市规划基本知识》深刻复习要点.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