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docx
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docx
- 文档编号:8164282
- 上传时间:2023-01-29
- 格式:DOCX
- 页数:7
- 大小:35.32KB
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docx
《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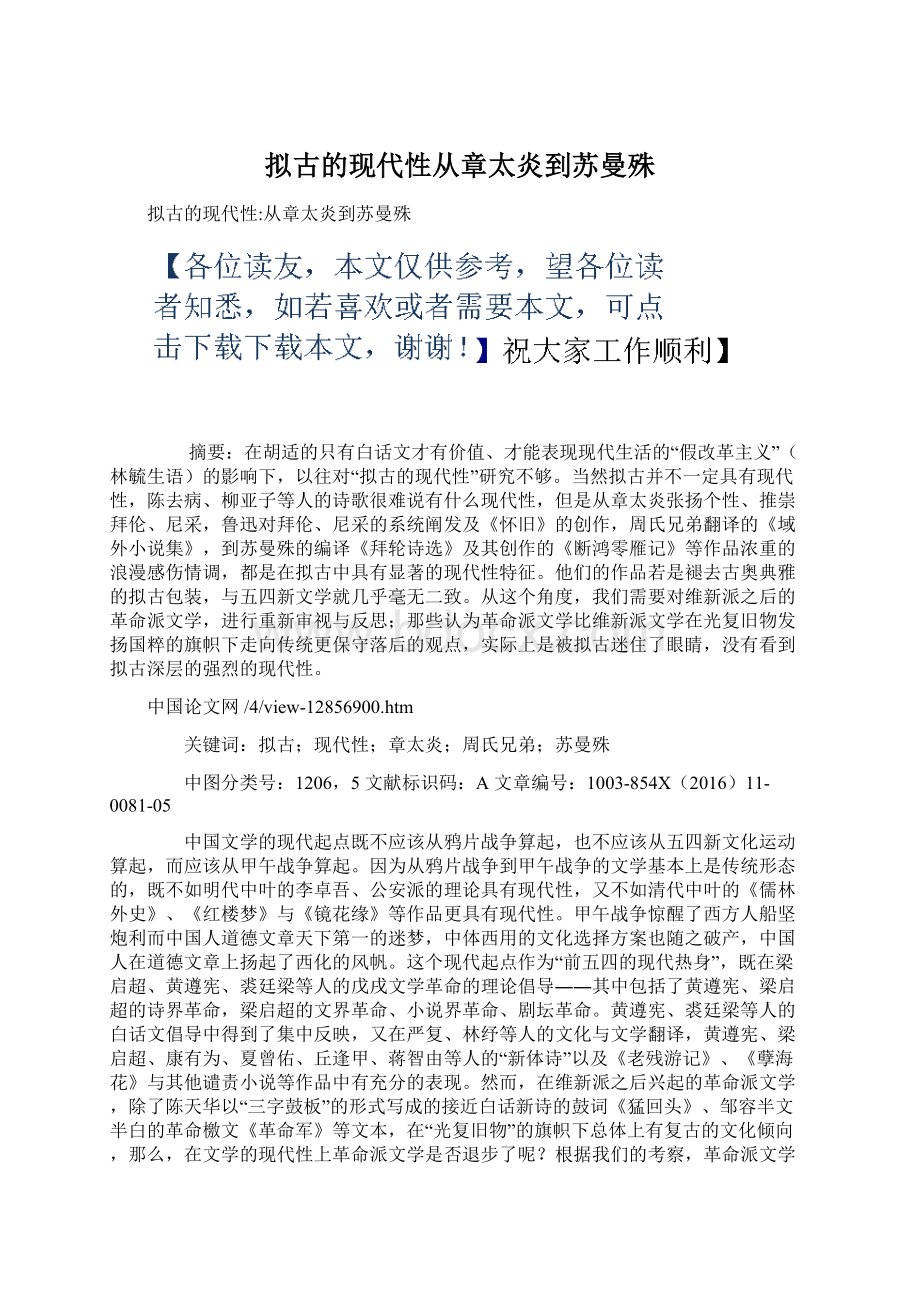
拟古的现代性从章太炎到苏曼殊
拟古的现代性:
从章太炎到苏曼殊
摘要:
在胡适的只有白话文才有价值、才能表现现代生活的“假改革主义”(林毓生语)的影响下,以往对“拟古的现代性”研究不够。
当然拟古并不一定具有现代性,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的诗歌很难说有什么现代性,但是从章太炎张扬个性、推崇拜伦、尼采,鲁迅对拜伦、尼采的系统阐发及《怀旧》的创作,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到苏曼殊的编译《拜轮诗选》及其创作的《断鸿零雁记》等作品浓重的浪漫感伤情调,都是在拟古中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征。
他们的作品若是褪去古奥典雅的拟古包装,与五四新文学就几乎毫无二致。
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对维新派之后的革命派文学,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那些认为革命派文学比维新派文学在光复旧物发扬国粹的旗帜下走向传统更保守落后的观点,实际上是被拟古迷住了眼睛,没有看到拟古深层的强烈的现代性。
中国论文网/4/view-12856900.htm
关键词:
拟古;现代性;章太炎;周氏兄弟;苏曼殊
中图分类号:
1206,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854X(2016)11-0081-05
中国文学的现代起点既不应该从鸦片战争算起,也不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而应该从甲午战争算起。
因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文学基本上是传统形态的,既不如明代中叶的李卓吾、公安派的理论具有现代性,又不如清代中叶的《儒林外史》、《红楼梦》与《镜花缘》等作品更具有现代性。
甲午战争惊醒了西方人船坚炮利而中国人道德文章天下第一的迷梦,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方案也随之破产,中国人在道德文章上扬起了西化的风帆。
这个现代起点作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既在梁启超、黄遵宪、裘廷梁等人的戊戌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其中包括了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剧坛革命。
黄遵宪、裘廷梁等人的白话文倡导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又在严复、林纾等人的文化与文学翻译,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等人的“新体诗”以及《老残游记》、《孽海花》与其他谴责小说等作品中有充分的表现。
然而,在维新派之后兴起的革命派文学,除了陈天华以“三字鼓板”的形式写成的接近白话新诗的鼓词《猛回头》、邹容半文半白的革命檄文《革命军》等文本,在“光复旧物”的旗帜下总体上有复古的文化倾向,那么,在文学的现代性上革命派文学是否退步了呢?
根据我们的考察,革命派文学在古色古香甚至佶屈聱牙的文字形式背后潜藏着比维新派文学更强的现代性意识,故名之为“拟古的现代性”。
我们先看古文家章太炎。
正是章太炎,拉开了文学上“拟古的现代性”的帷幕,显示了革命派在文化上与维新派的迥然不同。
章太炎在1903年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并撰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上海大同书局一起出版。
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再度来到日本时,已成为同盟会的一员大将,他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梁启超主张改良的《新民丛报》进行激烈论战。
他还主张以宗教发起信心,以国粹激动种姓,进行光复旧物的革命。
不过,尽管章太炎很赞成邹容反清排满的民主革命,但他并没有走邹容和陈天华等革命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进行启蒙的路线。
文言高雅是章太炎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而高雅的文言与反清排满的光复旧物与推崇国粹相联系,就找到了尊崇的理论依据。
换句话说,在古色古香与佶屈聱牙的中国古文字的字缝里,潜藏着政治文化上的驱逐鞑虏与光复旧物。
从这个意义上看,章太炎是以拟古的文学形式走向现代的先驱者。
章太炎文宗魏晋,“守己有度,伐人有序”,这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得以充分表现。
当然该文在章太炎文章中还是通俗易懂的,他的《�书》以及其它述学文章就更加晦涩难懂,连古文基础深厚的鲁迅也说看不懂。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胡适,在文学批评中一向以白话文为价值标准,却唯独对章太炎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做了很高的文学评价:
“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
人们注意的往往是章太炎的古色古香的拟古,关键在于他的拟古又是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往往令人忽视。
章太炎当时确实是让人用国粹激动种姓,但章太炎并没有像他的某些追随者那样以国粹排斥外来文明,相反,章太炎这一阶段的思想并不比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思想缺少现代性,而是具有卓然超群的浪漫品格。
“章太炎的反文明、反权威、反束缚,强调道德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甚至崇尚原始、返归自然等,都与卢梭如出一辙。
而章太炎对拜伦、尼采的推崇,正表现了他对始自卢梭,又被拜伦、尼采发扬光大的浪漫哲学的承担。
”章太炎说:
“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
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
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实有自性。
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因此,“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伪,惟人是真”。
人“亦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
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
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在当时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在陈去病、柳亚子等南社诗人那里,章太炎弘扬国粹的拟古表现为诗中大量地使用古代文化的典故,尤其是柳亚子的《孤愤》几乎是每一诗句都有典故:
题目典出《韩非子・孤愤》,第一句“孤愤真防决地维”典出《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怒触不周山;第三句“美新已�扬雄颂”典出扬雄吹捧王莽篡汉的《剧秦美新论》;第四句“劝进还传阮籍词”典出阮籍不得已在醉酒中给司马昭写的劝进文;第五句“岂有沐猴能作帝”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的“人言楚人沐猴而冠”;第六句“居然腐鼠亦乘时”典出《庄子・秋水》的“鸱得腐鼠”。
典故的大量使用在张扬国粹光复旧物方面是对章太炎的拟古的弘扬,但是章太炎的现代性在这些诗人的拟古中却不见了。
真正得章太炎“拟古的现代性”之神韵的,是章太炎的及门弟子周氏兄弟以及与章太炎是亦师亦友关系的苏曼殊。
可以说,章太炎影响了苏曼殊、周氏兄弟等文学家,他们在这一时期对拜伦的推崇与章太炎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文学形式上,他们也像章太炎一样讲求古雅,以文言写小说(苏曼殊)或者译小说(周氏兄弟),而且从《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破恶声论》,鲁迅的文章是越做越古奥难懂,生僻字也越来越多,这都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
事实上,章太炎推崇的拜伦不但是浪漫主义诗人。
而且用勃兰兑斯的话说,是走向现代的诗人。
拜伦的《海盗》等“东方叙事诗”那异域的情调,辽阔无垠的大海,无边无际的自由,荒蛮野性的冒险生活,真挚热烈的爱情,抗俗的意志品格,视道德与法律为无物的破坏性,以孤独的个人向社会群体复仇的精神,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相比之下,拜伦的《该隐》与《唐・璜》的浪漫主义特征就没有这么明显。
如果说《该隐》前面联结着古典主义,后面联结着现代主义;那么《唐・璜》前面联结着古典主义,后面联结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
可以说在英国诗坛上,拜伦将浪漫主义推向高峰,却又超越了浪漫主义。
如果说尼采是现代思想的开路人,那么拜伦对尼采的影响是巨大的。
拜伦深深认识到人生的悲剧性,在《曼弗雷德》中以“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等诗句震撼了尼采。
拜伦的诗自始至终贯穿着强力意志,尤其是表现强大意志力的《海盗》与《曼弗雷德》,使得尼采将强力意志本体化与哲学化。
拜伦在《该隐》中化做恶魔向上帝挑战。
而尼采则宣告了上帝的死亡。
拜伦被骚塞称之为恶魔诗人,在《该隐》等诗中也以恶魔自居,而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瞧!
这个人》中,则直接宣称喜欢恶不喜欢善,说查拉图斯特拉是恶人的朋友。
尼采也认为自己是拜伦塑造的,他说:
“人们一定会把我与拜伦的Manfred密切地关联在一起。
”而在中国,由于章太炎推崇拜伦,鲁迅很快就推出了张扬拜伦精神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而苏曼殊后来则以“中国的拜伦”自居,他编译的《拜轮诗选》不但所译《哀希腊》较全,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西方诗人的汉译诗集。
这部《拜轮诗选》的翻译显示了很深的国学与旧诗根底,这是郁达夫评价很高的原因。
但鲁迅却看出了其中另有奥秘。
因为他与苏曼殊当时都是章太炎的学生,1907年鲁迅筹办《新生》杂志,他为该刊准备的稿子就是介绍与推崇拜伦的《摩罗诗力说》,而这个时期开始译介并推崇拜伦诗歌的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
所以鲁迅怀疑,苏曼殊古奥的译文是经过章太炎修改的缘故。
鲁迅的怀疑方向是对的,章太炎确实参与了《拜轮诗选》的翻译。
根据黄侃的回忆,《赞大海》第五章就是章太炎翻译的,而且黄侃也参与了《哀希腊》与《赞大海》的翻译。
在朴学与国学方面,黄侃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弟子;他与章太炎的参与使得译文变得古奥,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但现在有人以为整个《拜轮诗选》都是黄侃翻译的则大错,因为黄侃说得明白,他与章太炎只参与《哀希腊》与《赞大海》的翻译,而《拜轮诗选》中还有《去国行》等拜伦的其它诗歌。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哀希腊》也有苏曼殊的参与,而其它诗黄侃与章太炎也进行了朝着古奥方向的修改,使之真正达到了“拟古的现代性”。
章太炎推崇魏晋之学,在其弟子苏曼殊与鲁迅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
如果说苏曼殊着重发扬了魏晋名士风流的放荡不羁与颓废感伤;那么,鲁迅则更多发扬了魏晋人物苏世独立的个性与“守己有度,伐人有序”的论辩艺术。
章太炎对鲁迅、周作人的影响都很深刻,包括其“拟古的现代性”的思想特色:
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革命的复古思想的影响”;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中,不但将章太炎推崇的拜伦与尼采分别加以推崇,而且将拟古真正推向了现代。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化层面的道德�r值革命与审美层面的文学革命,那么,鲁迅在章太炎的教示下在《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中已经完全达到了这两种革命的深度。
新文化运动是以个性解放反叛传统的礼教和家族制度。
那么,在新文化运动的十年之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早就发现了个人。
《文化偏至论》的文化策略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任个人”就是倡导个性解放,而个性从传统的合群中走出来,却不随波逐流,不为世俗所移而孤独地坚持着自己,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意志力,所以鲁迅又张扬主观的灵明,推崇“强大之意力”。
为此,鲁迅在哲学上向国人介绍了克尔凯戈尔、斯蒂纳、叔本华、尼采与易卜生等人。
尼采后来被表现主义与存在主义奉为先驱。
叔本华在意志本体论上是尼采的先驱,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神分析的先驱。
鲁迅写作《文化偏至论》时,克尔凯戈尔的名气还不大,后来存在主义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时才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家,因为存在主义将他奉为鼻祖。
《摩罗诗力说》从推崇个人的反传统视角,以拜伦等恶魔派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否定了宁静平和的“中国之诗”。
鲁迅激烈地批判传统的诗学:
既要言志,何必持之节之?
发乎情就可以了,何必要止乎礼义呢?
“强以无邪,即非人志”。
鲁迅在这里对个人自由的推崇,已经使他肯定了人性中邪恶成分的抒发。
鲁迅有感于恶魔性的否定与批判精神使西方迅猛发展,而中国善性的肯定精神使中国发展缓慢,所以,在《摩罗诗力说》中,他高举“恶魔派文学”的大旗,以颠覆中国传统文学平和的善性,就是为了使中国动起来,在列国争雄的时代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为此,鲁迅详细介绍了以拜伦为精神领袖的恶魔派诗人,包括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支奇、裴多菲,认为他们诗歌的恶魔精神“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
《摩罗诗力说》已蕴含了阿Q的影像,并且确立了鲁迅的启蒙范式:
精神界之战士应该是以反传统为特征的上抗天帝下启民众的恶魔,他对奴隶群众的姿态应该是像拜伦对希腊陋劣之民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然而,无论是《文化偏至论》对尼采的赞美还是《摩罗诗力说》对拜伦的推崇,都包裹在古色古香的文言叙述中,这种拟古的现代性,倒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迥然不同。
不过,不是没有人看出其中的现代性,冯雪峰就认为,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与“五四”的文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周氏兄弟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也是拟古的现代性的典范之作,一方面,选择的是比晚清包括林纾在内的所有其他译者的所译更为现代的作品,如现代派的开路人之一爱伦・坡的小说,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梭罗古勃等人的小说,而且译文迥然不同于此前的随意修改原文的“豪杰译”,成为现代直译的先驱;另一方面,在语言上却使用了比林纾的桐城古文更为典雅古奥的文言文来翻译。
周氏兄弟的论文也是如此,尤其是鲁迅的《破恶声论》。
可以用佶屈聱牙来加以形容,隔不几行就有难认的汉字出现。
正是在这种古奥典雅的行文中,潜藏着五四时代才得以张扬的个性精神。
鲁迅的小说《怀旧》差不多与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是同一时间的作品,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其现代性特征。
著名汉学家普实克认为,鲁迅的《怀旧》通过以念旧抒情的笔调淡化情节,瓦解了传统的叙事形式,小说整体风格上接近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然而,这篇具有现代的叙事技巧与表现风格的小说,却是以典雅古奥的文言文写成的,是真正的“拟古的现代性”。
如果说鲁迅由拜伦走向了尼采,那么,苏曼殊则始终钟情于拜伦,其《本事诗》第八首说: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他在《潮音跋》中是这样描绘自己与拜伦的合一:
“循陔之余。
惟好啸傲山林。
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轮《哀希腊》之篇。
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舟子惶然,疑其精神病作也。
”苏曼殊既写五绝、五律,也写七绝、七律,但他写得最多的是七绝。
他的生平就是一首充满各种传奇的令人感伤的诗,不过,他的诗不以用典彰显国粹,而是得传统诗歌之神韵,轻纱薄雾之中总透出忧郁与感伤。
苏曼殊的诗歌以爱情诗为主,他的小说几乎全都是爱情小说。
相比之下,他的小说比诗歌更具有浪漫色彩。
从1912年的《断鸿零雁记》开始,他发表了《绛纱记》(1915年)、《焚剑记》(1915年)、《碎簪记》(1916年)、《非梦记》(1917年)。
加上只写了两章的《天涯红泪记》(1914),共6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具有“拟古的现代性”特征。
我们以他的代表作《断鸿零雁记》来加以分析。
中国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言小说《世说新语》、《搜神记》和唐传奇,然而构成中国小说主潮的。
是从宋代勾栏瓦舍中成长起来的白话小说。
《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长篇名著使用的全都是白话文,文学价值比前述名著稍差的《三国演义》则是半文半白。
当然文言小说也没有消亡,但仅限于《聊斋志异》等短篇小说;而中长篇小说则都使用白话文,甚至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歧路灯》与把梁山起义军当强盗剿灭的《荡寇志》,使用的也是白话文。
在小说界革命影响下出现的谴责小说与《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中长篇小说,运用的也都是白话文。
从这个意义上看,苏曼殊以文言作中篇小说《断鸿零雁记》,而且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隔不几行就冒出一个难认的汉字,是真正的拟古。
然而,语言上古奥典雅的《断鸿零雁记》却比运用白话文的谴责小说更具有现代性。
在外在形式上,谴责小说中已经没有传统小说的诗词、四六和套语,这些诗词、四六与套语在说唱艺术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小说仅供阅读的现代就成为叙事的阑尾。
然而谴责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并不彻底,多数还保留了回目开始的“话说”与回目结束的“后事如何,下回分解”以及对仗工整的回目。
而在《断鸿零雁记》中,那些“话说”、“后事如何,下回分解”以及对仗工整的回目都不见了,以分章取代了传统的章回体,这与现代小说的叙事已经完全一致了。
传统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在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有一条鸿沟,叙述者经常与看官对话批评主人公及其他人物;谴责小说中已经出现了第一人称叙事,但是,小说主人公与叙述者几乎难以区分并成为作者的自叙传,却是从苏曼殊小说开始的,以至于很多人以《断鸿零雁记》来推断苏曼殊的成长经历,尽管二者不能划等号。
加上这部中篇小说浓重的主观抒情性、大量的心理描写以及感伤情调与悲剧氛围,使之成为“拟古的现代性”的代表作。
大雁向来成群结队而行,断鸿零雁则是孤独漂泊的象征。
唐人诗中即出现“断鸿”一词,如陈子昂《宿襄河驿浦》的“卧闻塞鸿断,坐听峡猿愁”,李咸用《登楼值雨》的“浪猛惊翘鹭,烟昏叫断鸿”,皎然《送严明府入关谒黎京兆》的“旅候闻嘶马,残阳望断鸿”。
不过,“断鸿”大量出现在诗词中是在宋代,尤其是陆游有十多首诗词都使用了“断鸿”一词。
然而,古诗中很少“断鸿”与“零雁”连用,这篇小说之所以连用,就是想特别强调去众离群的孤独漂泊,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
《断鸿零雁记》的第一章写身披袈裟的主人公“余”(三郎)倍感身世飘零:
“人皆谓我无母,我岂真无母耶?
”第二章到第六章是“余”下山化米迷路而至乳母家,乳母告诉“余”日本母亲的地址,于是在乳母家住下而与乳母之子潮儿为伴,并以卖花筹措去日本探母的资金,在卖花时得到未婚妻雪梅的资助(虽然雪梅父母见“余”家道中衰而悔婚,但雪梅誓死不从,这也是“余”出家的原因),就告别潮儿母子而东渡寻母。
第七章写“余”东渡大海,第八章至第十章��“余”与日本母亲涕泪相见,并与母亲去探望一直念着“余”的若姨及其女儿静子,却在若姨家病倒。
第十一至第十九章是“余”探母遇艳,写的是“余”与静子的交往与相恋的过程,“余”虽然已经出家,但对静子绝非无情,静子的惊艳之美丽,温柔之性格,博古通今之学识,能诗会画之才情,都令“余”激动不已,在“余”的视野里静子是一位完美的“玉人”,关键是静子已属意于“余”。
然而,当母亲告诉“余”她与若姨已将静子许配给“余”时,“余”却难以接受这份情,因为“余”已出家,而且“余”心里还有一个倾情于己宁可反抗父母并且资助自己东渡探母的雪梅。
但是“余”已出家以及雪梅的故事,又不能告诉母亲,拒绝母亲又会伤母亲的心。
“余”在尘俗与超凡之间、在家庭责任与个人抉择之间的艰难选择与心理挣扎,是小说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具现代性的描写。
最后“余”以书信的形式诀别静子,在西渡中将静子信物沉入大海,到上海后重披袈裟,又从麦家兄妹与潮儿那里得知,雪梅为抗婚“绝粒而天”,乳母已逝。
“余”先至乳母墓前,又去雪梅墓前,在“白杨萧萧,山鸟哀鸣”中悲悼不已。
然而,直到小说在悲剧中结束,“余”自身的内在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
“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
余此时泪尽矣!
自觉此心竟如木石,决归省吾师静室,复与法忍束装就道。
而不知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
”悲愁泪尽,岂会心如木石?
心如木石,岂会有无穷尽的弥天幽恨?
这篇小说是作者梦幻般的自叙传,“余”的很多经历与作者的经历是完全一致的,甚至“三郎”的名字都是一样的;但在现实中,作者却一直没有与他的日本母亲相见。
于是作者驰骋想象,使自己与母亲在小说中相见了。
纵然如此,感伤还是压倒了欢愉,泪水浸湿了整篇小说。
如果说五四文学以浪漫感伤为主导情调(从梁实秋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到李欧梵以浪漫感伤概括五四文学),那么,在苏曼殊小说的浪漫感伤为五四文学的情调拉开了帷幕。
具体地说,这种在感伤中表现自己的浪漫言说,成为郁达夫《沉沦》的先驱,甚至小说中“余”在东渡的大海上朗诵拜伦的《大海》,都与《沉沦》的主人公朗诵华兹华斯的诗歌,可以相互映衬。
很多人将苏曼殊的小说看成是鸳鸯蝴蝶派小说,连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也说苏曼殊“擅长鸳鸯蝴蝶派的文字”。
苏曼殊的小说确实可能影响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但将其小说看成鸳鸯蝴蝶派小说,却是一种误解。
正如《红楼梦》也影响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不能反过来说《红楼梦》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一样。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市场主要是市民阶层,并受到了文人的批判;苏曼殊小说的读者却是文人阶层,与市民阶层无关。
鸳鸯蝴蝶派小说很少自叙传式的主观抒情,而且很多运用的还是章回体。
鸳鸯蝴蝶派小说被看成是“相悦相恋,分拆不开”的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变种,不过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结尾一律大团圆不同,秦瘦鸥的《秋海棠》是悲剧,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及其《续集》是喜剧,但是,苏曼殊所有小说的结尾都是悲剧。
《绛纱记》中“余”与五姑、梦珠与秋云、霏玉与卢氏、玉鸾与“犯人”四对恋人无一不是以悲剧结尾:
《焚剑记》中的阿兰与孤独公子一个香消玉殒,一个焚剑而遁;《碎簪记》中的有情人不是自杀就是病逝;《非梦记》中的薇香与海琴一个抑郁而死,一个遁入空门。
苏曼殊小说在悲剧结尾与感伤情调上,具有明显的现代审美特征。
在胡适的只有白话文才有价值、才能表现现代生活及现代性等“假改革主义”(林毓生语)的影响下,以往对“拟古的现代性”研究不够,这也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完全排斥包括旧体诗在内的文言作品。
当然,拟古并不一定具有现代性,陈去病、柳亚子等人的诗歌很难说有什么现代性,但是从章太炎、周氏兄弟到苏曼殊的拟古,都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征。
他们的作品若是褪去古奥典雅的拟古包装,与五四新文学就毫无二致了。
周氏兄弟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大将,绝对不是偶然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需要对维新派之后的革命派文学,进行重新的审视与反思;那些认为革命派文学比维新派文学在光复旧物发扬国粹的旗帜下走向传统更保守落后的观点,实际上是被拟古迷住了眼睛。
没有看到拟古深层的强烈的现代性。
(责任编辑刘保昌)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拟古 现代性 章太炎 到苏曼殊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