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最新文档资料.docx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最新文档资料.docx
- 文档编号:535543
- 上传时间:2022-10-10
- 格式:DOCX
- 页数:5
- 大小:23.87KB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最新文档资料.docx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最新文档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最新文档资料.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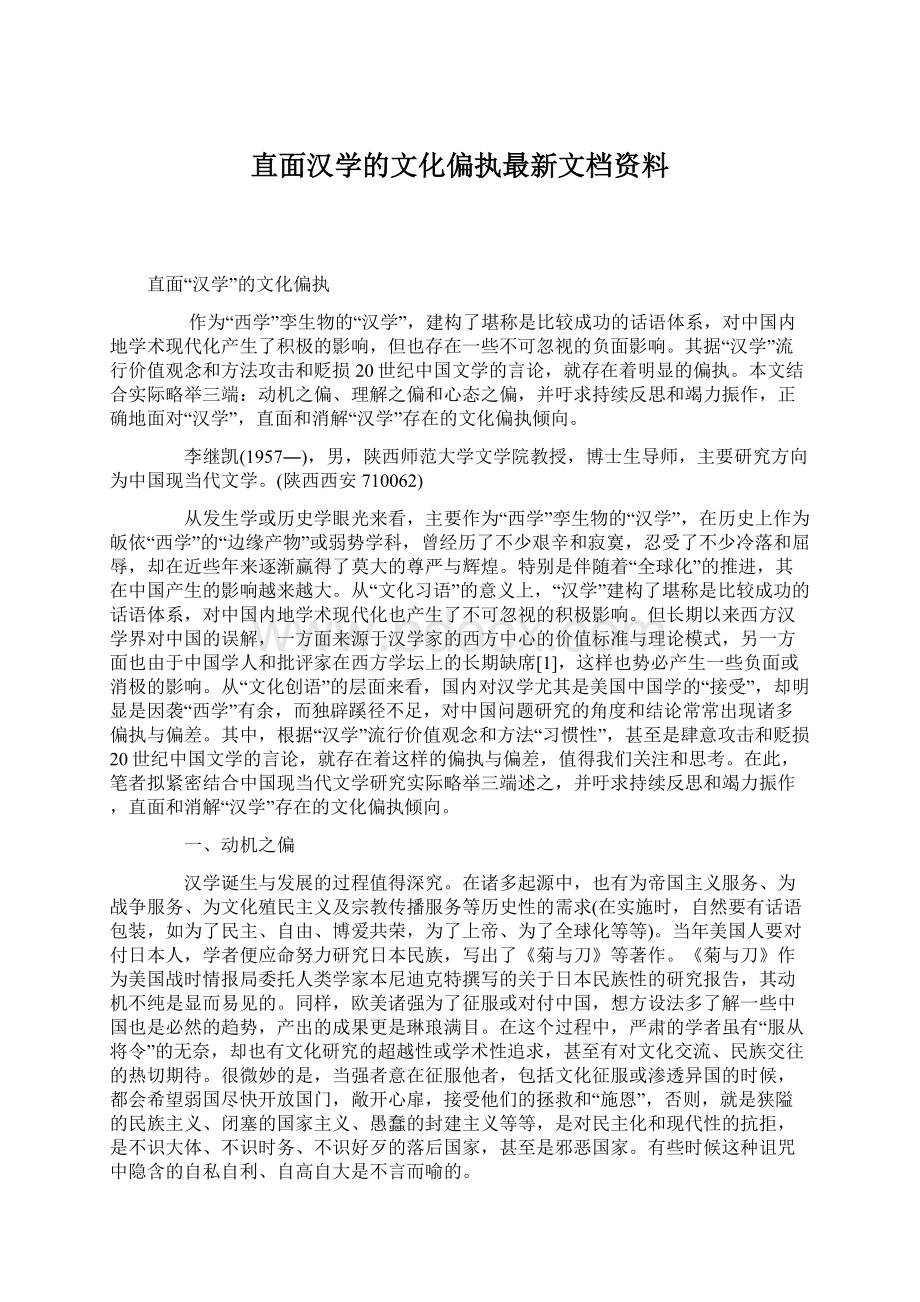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最新文档资料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
作为“西学”孪生物的“汉学”,建构了堪称是比较成功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内地学术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其据“汉学”流行价值观念和方法攻击和贬损20世纪中国文学的言论,就存在着明显的偏执。
本文结合实际略举三端:
动机之偏、理解之偏和心态之偏,并吁求持续反思和竭力振作,正确地面对“汉学”,直面和消解“汉学”存在的文化偏执倾向。
李继凯(1957―),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陕西西安710062)
从发生学或历史学眼光来看,主要作为“西学”孪生物的“汉学”,在历史上作为皈依“西学”的“边缘产物”或弱势学科,曾经历了不少艰辛和寂寞,忍受了不少冷落和屈辱,却在近些年来逐渐赢得了莫大的尊严与辉煌。
特别是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其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从“文化习语”的意义上,“汉学”建构了堪称是比较成功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内地学术现代化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但长期以来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的误解,一方面来源于汉学家的西方中心的价值标准与理论模式,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学人和批评家在西方学坛上的长期缺席[1],这样也势必产生一些负面或消极的影响。
从“文化创语”的层面来看,国内对汉学尤其是美国中国学的“接受”,却明显是因袭“西学”有余,而独辟蹊径不足,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角度和结论常常出现诸多偏执与偏差。
其中,根据“汉学”流行价值观念和方法“习惯性”,甚至是肆意攻击和贬损20世纪中国文学的言论,就存在着这样的偏执与偏差,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在此,笔者拟紧密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实际略举三端述之,并吁求持续反思和竭力振作,直面和消解“汉学”存在的文化偏执倾向。
一、动机之偏
汉学诞生与发展的过程值得深究。
在诸多起源中,也有为帝国主义服务、为战争服务、为文化殖民主义及宗教传播服务等历史性的需求(在实施时,自然要有话语包装,如为了民主、自由、博爱共荣,为了上帝、为了全球化等等)。
当年美国人要对付日本人,学者便应命努力研究日本民族,写出了《菊与刀》等著作。
《菊与刀》作为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撰写的关于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报告,其动机不纯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欧美诸强为了征服或对付中国,想方设法多了解一些中国也是必然的趋势,产出的成果更是琳琅满目。
在这个过程中,严肃的学者虽有“服从将令”的无奈,却也有文化研究的超越性或学术性追求,甚至有对文化交流、民族交往的热切期待。
很微妙的是,当强者意在征服他者,包括文化征服或渗透异国的时候,都会希望弱国尽快开放国门,敞开心扉,接受他们的拯救和“施恩”,否则,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闭塞的国家主义、愚蠢的封建主义等等,是对民主化和现代性的抗拒,是不识大体、不识时务、不识好歹的落后国家,甚至是邪恶国家。
有些时候这种诅咒中隐含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大是不言而喻的。
二、理解之偏
迄今为止,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是五花八门,似乎从各种角度或层面都可以切入现代性话题。
时空角度、古今比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审美接受、心理变迁、性际关系、个体集体、理性非理性、乃至反其道而求更加“现代”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等等,都可以与现代性话语联系起来言说。
但经典“汉学”中对现代性的强调是“圭臬”性的,突出的只是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尽管这现代性本身也带有矛盾与冲突)。
用之理解东方世界的“现代性”追求,特别是文化艺术的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就会暴露出自己的局限性,就会陷入“异元批评”的误区。
譬如对创造中国现代文化功绩卓著的“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运动,从主导方面看无疑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性理解。
但众所周知,在“汉学”中确有贬低“五四”的倾向,且采取了“前后夹击”的战术:
既从前面找“好东西”比“五四”,古代的乃至近代的,认为是“五四”抛弃了古代的好东西,只会学舌于西方,即使是现代性追求,“晚清”也有它的丰富性和精彩之处,反而是“五四”将丰富的现代性转化为文化激进主义,窄化或单一化了;又竭力从后面找坏东西比“五四”,很相似的东西,比如打倒孔家店之类,于是“文革”的源头居然就是“五四”,而伟大“五四”的历史作用便成了负面的,甚至被视为罪恶的渊薮。
某位汉学家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观点可以视为前者的代表,认为“五四”不是创生或彰显中国现代性,而是“压抑”或遮蔽了晚清原有丰富的现代性取向。
“‘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仓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
”[3](P56)其主张多从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学演化的内部来探询现代性的学术追求虽有其合理性,但似乎并不彻底。
因为现代性的多元和发生的“多源”使人们更可以发出这样的询问:
“没有红楼,何来晚清?
”“没有晚明,何来红楼?
”……甚至可以追溯到初民时代的某些“文化原型”。
但我们要强调的现代性,是在“大现代”时空中由“古今中外”融于一炉方才孕育生成的中国现代性,这样的现代性也孕育了特有的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延展到当前),不是外国任何一个国家文学的简单移植和翻版,但与很多国家文学又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与母语文学保持了创造性继承和发展的至密关系。
对此谁都无法否认。
这其实并非要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辩护,而是东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发展业已折射出多样现代性中的中国文化光辉。
人们从超越时空的中国先哲和文学大师身上似乎重新发现了“古代哲学的现代性”和“古代文学的现代性”。
既然现代性是多元多样的,古为今用也便具有现代性,如兵马俑,国人已经通过发掘和利用,将其“建构”成为现代旅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巡展也引起轰动。
那么,从接受美学角度看,也可以确认古典进入现代就成为被接受的“当代作品”。
因此,单纯的崇古薄今或崇今薄古都与现代性不兼容,仅仅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也是不够的。
没有中国,何来“五四”?
也正如说“没有外国,何来‘五四’”一样颠扑不破。
尽管“五四”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但那种试图从“五四”本身的症结分析入手,进行直接的解构的做法仍然存在问题:
认定“五四”本身浅薄、浮躁、幼稚、怪异等等,包括各种主义的纷沓而至及其浅尝辄止,似乎只是纷乱的一场闹剧而已。
其实,“五四”作为中国开启“大现代”的伟大开端当之无愧,很多无可争议的史实包括“五四”的积极影响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里还有必要特别提及“汉学”权威著作《剑桥中华民国史》。
这部著作无疑是中国内地学者“习语”或借鉴的主要对象之一。
其作者主要是美国中国学的一些代表性学者。
主编费正清是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执笔撰写上卷第9章及下卷第9章的则是时任芝加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李欧梵先生。
提起李先生,大家几乎一片赞扬声。
他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几乎被奉为权威中的权威论述。
其观点和思路在中国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
我们固然不能忽视或无视这些影响,更不能否认其曾经和依然会继续产生的积极影响。
但他在上卷第9章《文学的趋势I:
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中,却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一些“偏见”。
由于文学标准来自“西方”,话语间就难免有据此而来的相当简单化的理解与评判。
无形中就将中国现代作家基于古今中外传统融会而来的文学“创作”,看作是对国外作家的“模仿”而非独立的“创造”[4](P550),在整体上也必然会忽视“五四”时期中国作家的文化创造,将“五四”文学视为比之西方文学而不及的“亚形态”文学。
尽管他也肯定了标志性作家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并给予了较多介绍,但用西方标准的衡定结果却是:
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几乎是唯一‘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的人”,“在他的散文诗中,鲁迅好像已经超越了常见的他那一代人的感情,而到达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边缘。
”[4](P558-559)我们常常津津乐道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了与时俱进又提升为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近些年来还有人将鲁迅与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挂起了钩,仿佛鲁迅就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在中国的实践者和代表者――不过,因为只是学习者,模仿者所以充其量也只能达到这些时髦主义的“边缘”。
这样的学术取向和思路确实影响了太多的人,不仅年轻学者容易受到影响,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年学者也曾乐于进行类似的阐释。
还都以为是在弘扬鲁迅的伟大创造精神和先驱姿态呢。
然而,冷静思考一下,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几乎唯一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的人吗?
象征主义是解读鲁迅小说的最高最佳的理论范式吗?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纯粹用西方标准来看鲁迅,那么鲁迅千辛万苦的上下求索也只能“到达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边缘”而已。
然则,为何不说鲁迅抵达了从中国体验出发融合古今中外的独创性文学世界,而且还进入了中国特色(包括汉语书写)的文学世界之中心?
鲁迅要开辟“新文场”,要创作“新文学”,这个“新文学”显然不是空头支票,不仅对于中国读者是“新文学”,对外国读者来说也是“新文学”。
鲁迅在中国文学、在亚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都无疑是独特的一位作家,他的那些代表作不是模仿西方或任何外国作家的赝品,而是多所借鉴、融会再造的上品乃至极品。
在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中国学)影响下,不少人都不约而同地对鲁迅后期多所批评,其中“终结论”和“压倒论”成了主要的观点,影响甚大。
李欧梵先生虽然是相当严谨的学者,兼容并包意识颇强,也还是受到了此类观点的影响。
他说:
“1927年以后,鲁迅自己结束了他内心的苦闷,决定面对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拿起笔为‘左翼’事业而写杂文了。
从纯粹美学的观点来看,这一明显的转向意味着鲁迅作为一个创造性艺术家的事业的终结,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看,只不过是对政治的献身压倒了艺术的兴趣。
”[4](P560)这样的看法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9章中也得到了呼应:
“随着鲁迅在30年代早期变得更加政治化,他的杂文写作的内在个性,也逐渐淹没在公开的攻歼呼号的表层之下了。
”[5](P508)尽管李先生努力不把判断绝对化,但在相关评述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鲁迅创作衰落于“接受了青年激进派的基本信条”,确实耿耿于怀。
由这样的思维逻辑肯定会导致对“终结论”和“压倒论”的基本认同,并对审美、启蒙等给予赞肯而对政治、革命等给予贬斥。
由此也势必走上“告别革命论”的路途(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便与此相通)。
果然,李先生高度认同夏志清的有关论述,鲁迅等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局限于中国现实,因此不会置身于世界现代文学的主流。
而走在文学边缘的鲁迅一旦“走向左翼”,鲁迅的艺术生命也就政治化了。
西化思维是自洽的,用西方标准看,鲁迅的局限简直太明显了,中国文学局限性也太明显了。
“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中真正获得过胜利。
”而且在进入当代阶段以后,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主义文学的主要特点了”[4](P566)。
这就是李先生最想说的话语。
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理念本是西方的,内涵着合理之处,但某些“汉学”学者有时恰恰最容易忘记这一点。
他们认定中国本土不能产生现代性,开放融合实行必要的拿来主义也不能赢得现代性的真正胜利,中国共产主义文学的人民性和艺术性就更没有“现代性”可言了。
然而,果真如此吗?
这其实是个非常重大的文学命题,值得学术界开展广泛深入的探讨。
用力颠覆“五四”和左翼叙事的学术姿态,与没有真正“痛切”的历史记忆与人生体验相关,也与“第一世界”或“移民人生”密切相关。
三、心态之偏
王海龙曾指出:
“由于中国学人和批评家的长期缺席,西方汉学长期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纯粹的西方治学模式、理论观念和学术技巧去研究、批判中国文化,怀着倨傲的心态俯察中国,甚至把中国当成一个病态社会的案例来分析。
这就很难指望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另一种是钟爱汉学,怀着无限的同情来研究中国文化,赞美中华文明,甚至达到了不辞其咎的回护程度。
但是,过犹不及,酷评与溺爱都不是对中国文化和汉学研究应有的建设性态度。
”[1]这样的倨傲心态与过誉心态所导致的“酷评与溺爱”,都有一定的弊病,都会显示出弊多利少的“心态之偏”。
难怪当年鲁迅对大肆贬低或过分赞美中国人的老外言论有那样的抵触情绪甚至反唇相讥。
近些年来类似的心态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没有消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直面 汉学 文化 偏执 最新 文档 资料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12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实施细则_精品文档.doc
12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实施细则_精品文档.doc
 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_精品文档.xls
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_精品文档.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