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docx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docx
- 文档编号:5051373
- 上传时间:2022-12-12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32.10KB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docx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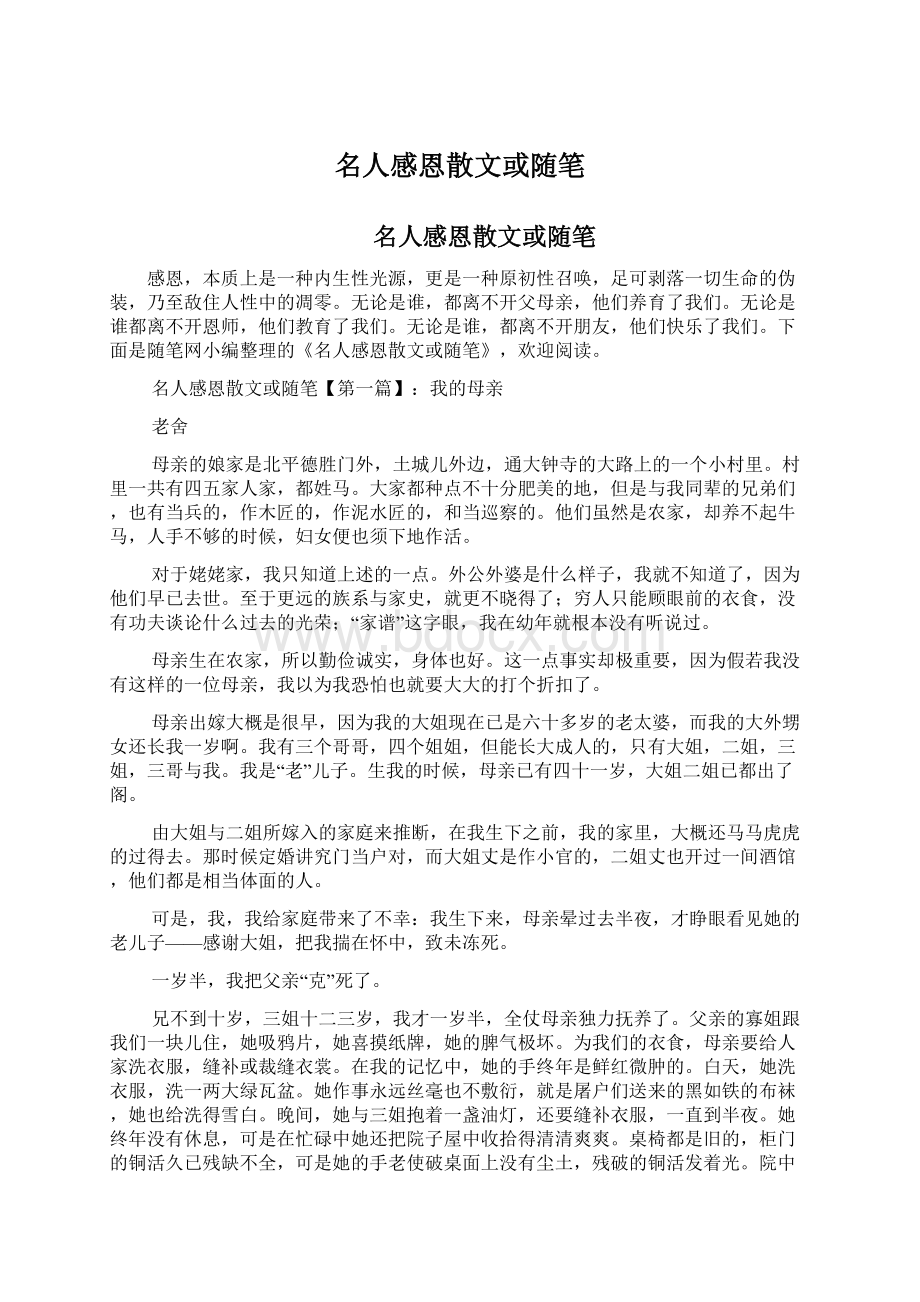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
感恩,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光源,更是一种原初性召唤,足可剥落一切生命的伪装,乃至敌住人性中的凋零。
无论是谁,都离不开父母亲,他们养育了我们。
无论是谁都离不开恩师,他们教育了我们。
无论是谁,都离不开朋友,他们快乐了我们。
下面是随笔网小编整理的《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欢迎阅读。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第一篇】:
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
还说什么呢?
心痛!
心痛!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第二篇】:
挥手——怀念我的父亲
赵丽宏
深夜,似睡似醒,耳畔得得有声,仿佛是一支手杖点地,由远而近……父亲,是你来了么?
骤然醒来,万簌俱寂,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打开台灯,父亲在温暖的灯光中向我微笑。
那是一张照片,是去年陪他去杭州时我为他拍的,他站在西湖边上,花影和湖光衬托着他平和的微笑。
照片上的父亲,怎么也看不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一个月前,父亲突然去世。
那天母亲来电话,说父亲气急,情况不好,让我快去。
这时,正有一个不速之客坐在我的书房里,是从西安来约稿的一个编辑。
我赶紧请他走,还是耽误了五六分钟。
送走那不速之客后,我便拼命骑车去父亲家,平时需要骑半个小时的路程,只用了十几分钟,也不知这十几里路是怎么骑的,然而我还是晚到了一步。
父亲在我回家前的十分钟停止了呼吸。
一口痰,堵住了他的气管,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两声:
“我透不过气来……”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救护车在我之前赶到,医生对垂危的父亲进行了抢救,终于无功而返。
我赶到父亲身边时,他平静地躺着,没有痛苦的表情,脸上似乎略带微笑,就像睡着了一样。
他再也不会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再也不会向我倾诉他的病痛,再也不会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创作,再也不会拄着拐杖跑到书店和邮局,去买我的书和发表有我文章的报纸和刊物,再也不会在电话中笑声朗朗地和孙子聊天……父亲!
因为父亲走得突然,子女们都没有能送他。
父亲停止呼吸后,我是第一个赶回到他身边的。
我把父亲的遗体抱回到他的床上,为他擦洗了身体,刮了胡子,换上了干净的衣裤。
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我很少为他做,他生病时,都是母亲一个人照顾他。
小时候,父亲常常带我到浴室里洗澡,他在热气蒸腾的浴池里为我洗脸擦背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得,想不到,我有机会为父亲做这些事情时,他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父亲,你能感觉我的拥抱和抚摸么?
父亲是一个善良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宽厚的微笑。
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一句,更没有打过一下,对其他孩子也是这样。
也从来没有见到他和什么人吵过架。
父亲生于1912年,是清王朝覆灭的第二年。
祖父为他取名鸿才,希望他能够改变家庭的窘境,光耀祖宗。
他的一生中,有过成功,更多的是失败。
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家乡的传奇人物:
一个贫穷的佃户的儿子,靠着自己的奋斗,竟然开起了好几家兴旺的商店,买了几十间房子,成了使很多人羡慕的成功者。
家乡的老人,至今说起父亲依旧肃然起敬。
年轻时他也曾冒过一点风险,抗日战争初期,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的封锁下,他摇着小船从外地把老百姓需要的货物运回家乡,既为父老乡亲做了好事,也因此发了一点小财。
抗战结束后,为了使他的店铺里的职员们能逃避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父亲放弃了家乡的店铺,力不从心地到上海开了一家小小的纺织厂。
他本想学那些叱咤风云的民族资本家,也来个“实业救国”,想不到这就是他在事业上衰败的开始。
在汪洋般的大上海,父亲的小厂是微乎其微的小虾米,再加上他没有多少搞实业和管理工厂的经验,这小虾米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大鱼和螃蟹们的美餐。
他的工厂从一开始就亏损,到解放的时候,这工厂其实已经倒闭,但父亲要面子,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靠借债勉强维持着企业。
到公私合营的时候,他那点资产正好够得上当一个资本家。
为了维持企业,他带头削减自己的工资,减到比一般的工人还低。
他还把自己到上海后造的一幢楼房捐献给了公私合营后的工厂,致使我们全家失去了存身之处,不得不借宿在亲戚家里,过了好久才租到几间石库门里弄中的房间。
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是一个名不符实的资本家,而这一顶帽子,也使我们全家消受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一直是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
记得我小时候身上穿的总是用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改做的旧衣服,上学后,每次开学前付学费时,都要申请分期付款。
对于贫穷,父亲淡然而又坦然,他说:
“穷不要紧,要紧的是做一个正派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们从未因贫穷而感到耻辱和窘困,这和父亲的态度有关。
父亲工厂里的“造反队”也到我们家里来抄家,可厂里的老工人知道我们的家底,除了看得见的家具摆设,家里不可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来抄家的人说:
“有什么金银财宝,自己交出来就可以了。
”记得父亲和母亲耳语了几句,母亲便打开五斗橱抽屉,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根失去光泽的细细的金项链,交到了“造反队员”的手中。
后来我才知道,这根项链,还是母亲当年的嫁妆。
这是我们家里惟一的“金银财宝”……
一天夜晚,“造反队”闯到我们家带走了父亲。
和我们告别时,父亲非常平静,毫无恐惧之色,他安慰我们说:
“我没有做过亏心事,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当时,我感到父亲很坚强,不是一个懦夫。
父亲作为“黑七类”,自然度日如年。
但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日子里,仍有厂里的老工人偷偷地跑来看父亲,还悄悄地塞钱接济我们家。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由此了解了父亲的为人,也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未必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
父亲一直说:
“我最骄傲的事业,就是我的子女,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想,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些作为,和父亲的为人,和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
记忆中,父亲的一双手老是在我的面前挥动……
我想起人生路上的三次远足,都是父亲去送我的。
他站在路上,远远地向我挥动着手,伫立在路边的人影由大而小,一直到我看不见……
第一次送别是我小学毕业,我考上了一所郊区的住宿中学,那是六十年代初。
那天去学校报到时,送我去的是父亲。
那时父亲还年轻,鼓鼓囊囊的铺盖卷提在他的手中并不显得沉重。
中学很远,坐了两路电车,又换上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
从窗外掠过很多陌生的风景,可我根本没有心思欣赏。
我才十四岁,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没有离开过父母,想到即将一个人在学校里过寄宿生活,不禁有些害怕,有些紧张。
一路上,父亲很少说话,只是面带微笑默默地看着我。
当公共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疾驰时,父亲望着窗外绿色的田野,表情变得很开朗。
我感觉到离家越来越远,便忐忑不安地问:
“我们是不是快要到了?
”父亲没有直接回答我,指着窗外翠绿的稻田和在风中飘动的林荫,答非所问地说:
“你看,这里的绿颜色多好。
”他看了我一眼,大概发现了我的惶惑和不安,便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胛,又说:
“你闻闻这风中的味道,和城市里的味道不一样,乡下有草和树叶的气味,城里没有。
这味道会使人健康的。
我小时候,就是在乡下长大的。
离开父母去学生意的时候,只有十二岁,比你还小两岁。
”父亲说话时,抚摸着我的肩胛的手始终没有移开,“离开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季节,比现在晚一些,树上开始落黄叶了。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我离家才没有几天,突然就发冷了,冷得冰天雪地,田里的庄稼全冻死了。
我没有棉袄,只有两件单衣裤,冷得瑟瑟发抖,差点没冻死。
”父亲用很轻松的语气,谈着他少年时代的往事,所有的艰辛和严峻,都融化在他温和的微笑中。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并不是一个深沉的人,但谈起遥远往事的时候,尽管他微笑着,我却感到了他的深沉。
那天到学校后,父亲陪我报到,又陪我找到自己的寝室,帮我铺好了床铺。
接下来,就是我送父亲了,我要把他送到校门口。
在校门口,父亲拍拍我肩膀,又摸摸我头,然后笑着说:
“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
开始不习惯,不要紧,慢慢就会习惯的。
”说完,他就大步走出了校门。
我站在校门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
校门外是一条大路,父亲慢慢地向前走着,并不回头。
我想,父亲一定会回过头来看看我的。
果然,走出十几米远时,父亲回过头来,见我还站着不动,父亲就转过身,使劲向我挥手,叫我回去。
我只觉得自己的视线模糊起来……在我少年的心中,我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对父亲是如此依恋。
父亲第二次送我,是“文化革命”中了。
那次,是出远门,我要去农村“插队落户”。
当时,父亲是“有问题”的人,不能随便走动,他只能送我到离家不远的车站。
那天,是我自己提着行李,父亲默默地走在我身边。
快分手时,他才呐呐地说:
“你自己当心了。
有空常写信回家。
”我上了车,父亲站在车站上看着我。
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别离的伤感,而是带着他常有的那种温和的微笑,只是有一点勉强。
我知道,父亲心里并不好受,他是怕我难过,所以尽量不流露出伤感的情绪。
车开动了,父亲一边随着车的方向往前走,一边向我挥着手。
这时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父亲第三次送我,是我考上大学去报到那一天。
这已经是1978年春天。
父亲早已退休,快七十岁了。
那天,父亲执意要送我去学校,我坚决不要他送。
父亲拗不过我,便让步说:
“那好,我送你到弄堂口。
”这次父亲送我的路程比前两次短得多,但还没有走出弄堂,我发现他的脚步慢下来。
回头一看,我有些吃惊,帮我提着一个小包的父亲竟已是泪流满面。
以前送我,他都没有这样动感情,和前几次相比,这次离家我的前景应该是最光明的一次,父亲为什么这样伤感?
我有些奇怪,便连忙问:
“我是去上大学,是好事情啊,你干嘛这样难过呢?
”父亲一边擦眼泪,一边回答: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我想为什么总是我送你离开家呢?
我想我还能送你几次呢?
”说着,泪水又从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这时,我突然发现,父亲花白的头发比前几年稀疏得多,他的额头也有了我先前未留意过的皱纹。
父亲是有点老了。
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儿女的长大,总是以父母青春的流逝乃至衰老为代价的,这过程,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进行,没有人能够阻挡这样的过程。
父亲中年时代身体很不好,严重的肺结核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
曾有算命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五十七是“骑马过竹桥”,凶多吉少,如果能过这一关,就能长寿。
五十七岁时,父亲果真大病一场,但他总算摇摇晃晃地走过了命运的竹桥。
过六十岁后,父亲的身体便越来越好,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二十岁,曾经有人误认为我们父子是兄弟。
八十岁之前,他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的人,说话,走路,都没有老态。
几年前,父亲常常一个人突然地就走到我家来,只要楼梯上响起他缓慢而沉稳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他来了,门还没开,门外就已经漾起他含笑的喊声……四年前,父亲摔断了胫股骨,在医院动了手术,换了一个金属的人工关节。
此后,他便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一下子老了许多,再也没有恢复以前那种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
他的手上多了一根拐杖,走路比以前慢得多,出门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
不过,只要遇到精神好的时候,他还会柱着拐杖来我家。
在我的所有读者中,对我的文章和书最在乎的人,是父亲。
从很多年前我刚发表作品开始,只要知道哪家报纸杂志刊登有我的文字,他总是不嫌其烦地跑到书店或者邮局里去寻找,这一家店里没有,他再跑下一家,直到买到为止。
为做这件事情,他不知走了多少路。
我很惭愧,觉得我的那些文字无论如何不值得父亲去走这么多路。
然而再和他说也没用。
他总是用欣赏的目光读我的文字,尽管不当我的面称赞,也很少提意见,但从他阅读时的表情,我知道他很为自己的儿子骄傲。
对我的成就,他总是比我自己还兴奋。
这种兴奋,有时我觉得过分,就笑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你的儿子很一般,你不要太得意。
”他也不反驳我,只是开心地一笑,像个顽皮的孩子。
在他晚年体弱时,这种兴奋竟然一如十数年前。
前几年,有一次我出版了新书,准备在南京路的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
父亲知道了,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去看看,因为这家大书店离我的老家不远。
我再三关照他,书店里人多,很挤,千万不要凑这个热闹。
那天早晨,书店里果然人山人海,卖书的柜台几乎被热情的读者挤塌。
我欣慰地想,好在父亲没有来,要不,他撑着拐杖在人群中可就麻烦了。
于是我心无旁鹜,很专注地埋头为读者签名。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我无意中抬头时,突然发现了父亲,他拄着拐杖,站在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人默默地在远处注视着我。
唉,父亲,他还是来了,他已经在一边站了很久。
我无法想像他是怎样拄着拐杖穿过拥挤的人群上楼来的。
见我抬头,他冲我微微一笑,然后向我挥了挥手。
我心里一热,笔下的字也写错了……
去年春天,我们全家陪着我的父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几天。
每天傍晚,我们一起湖畔散步,父亲的拐杖在白堤和苏堤上留下了轻轻的回声。
走得累了,我们便在湖畔的长椅上休息,父亲看着孙子不知疲倦地在他身边蹦跳,微笑着自言自语:
“唉,年轻一点多好……”
死亡是人生的必然归宿,雨果说它是“最伟大的平等,最伟大的自由”,这是对死者而言,对失去了亲人的生者们来说,这永远是难以接受的事实。
父亲逝世前的两个月,病魔一直折磨着他,但这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只是一种叫“带状疱疹”的奇怪的病,父亲天天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寝食不安。
因为看父亲走着去医院检查身体实在太累,我为父亲送去一辆轮椅,那晚在他身边坐了很久,他有些感冒,舌苔红肿,说话很吃力,很少开口,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话。
临走时,父亲用一种幽远怅惘的目光看着我,几乎是乞求似的对我说:
“你要走?
再坐一会儿吧。
”离开他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要多来看望父亲,多和他说说话。
我决没有想到再也不会有什么“以后”了,这天晚上竟是我们父子间的永别。
两天后,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父亲去世前一天的晚上,我曾和他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明天去看他,他说:
“你忙,不必来。
”其实,他希望我每天都在他身边,和他说话,这是我知道的,但我却没有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着他!
记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自己多保重。
”父亲,你自己病痛在身,却还想着要我保重。
你最后对我说的话,将无穷无尽回响在我的耳边,回响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生命永远沉浸在你的慈爱和关怀之中。
父亲!
现在,每当我一人静下心来,面前总会出现父亲的形象。
他像往常一样,对着我微笑。
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向我挥手,就像许多年前他送我时,在路上回过头来向我挥手一样,就像前几年在书店里站在人群外面向我挥手一样……有时候我想,短促的人生,其实就像匆忙的挥手一样,挥手之间,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成为过眼烟云。
然而父亲对我挥手的形象,我却无法忘记。
我觉得这是一种父爱的象征,父亲将他的爱,将他的期望,还有他的遗憾和痛苦,都流露渲泄在这轻轻一挥手之间了。
名人感恩散文或随笔【第三篇】:
背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
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
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父亲说:
“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
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因为丧事,一半因为父亲赋闲。
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
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
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
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
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
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
“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
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
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
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
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名人 感恩 散文 随笔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如何打造酒店企业文化2刘田江doc.docx
如何打造酒店企业文化2刘田江doc.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