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藏区支教.docx
在藏区支教.docx
- 文档编号:28899604
- 上传时间:2023-07-20
- 格式:DOCX
- 页数:25
- 大小:39.61KB
在藏区支教.docx
《在藏区支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在藏区支教.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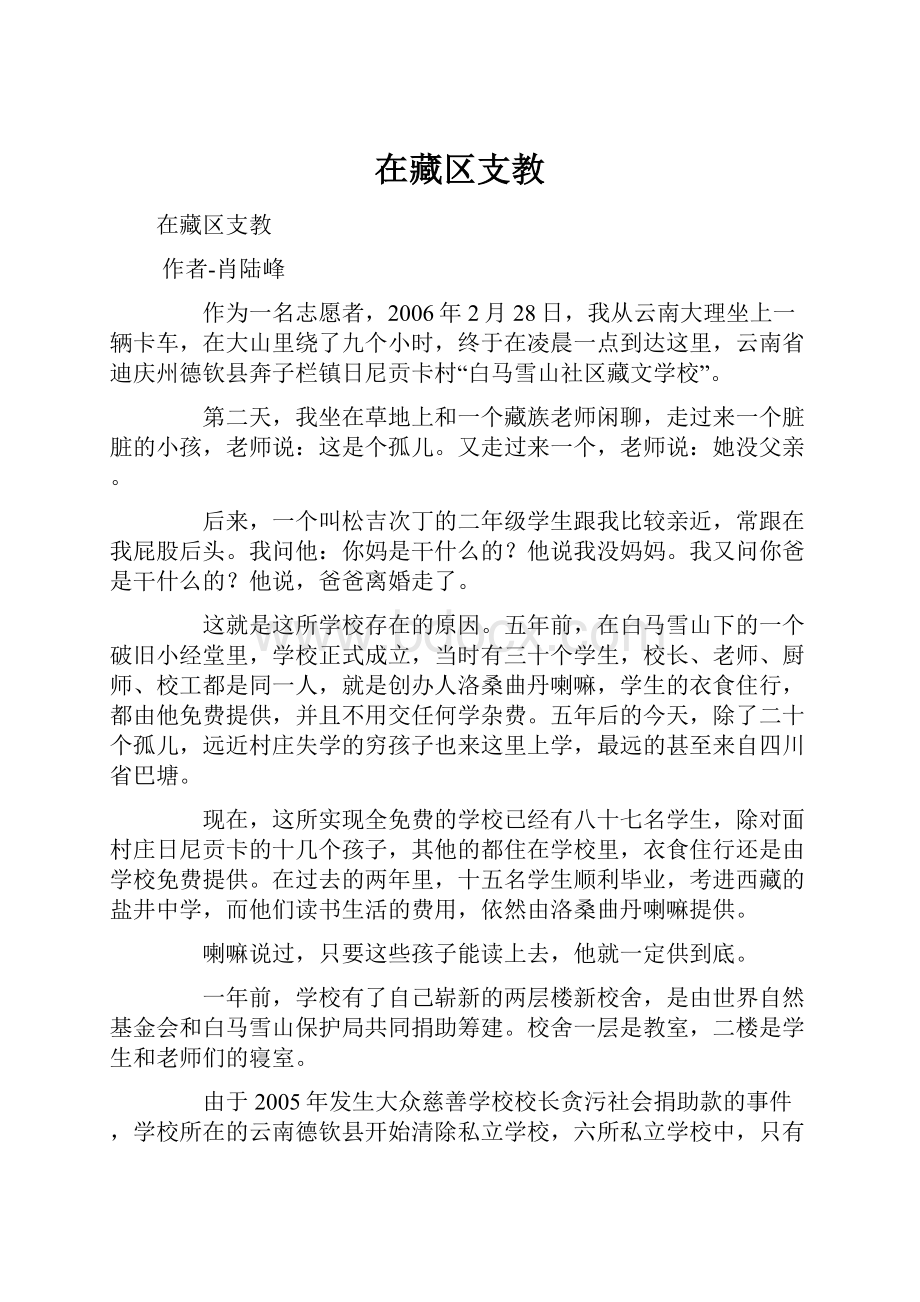
在藏区支教
在藏区支教
作者-肖陆峰
作为一名志愿者,2006年2月28日,我从云南大理坐上一辆卡车,在大山里绕了九个小时,终于在凌晨一点到达这里,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奔子栏镇日尼贡卡村“白马雪山社区藏文学校”。
第二天,我坐在草地上和一个藏族老师闲聊,走过来一个脏脏的小孩,老师说:
这是个孤儿。
又走过来一个,老师说:
她没父亲。
后来,一个叫松吉次丁的二年级学生跟我比较亲近,常跟在我屁股后头。
我问他:
你妈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没妈妈。
我又问你爸是干什么的?
他说,爸爸离婚走了。
这就是这所学校存在的原因。
五年前,在白马雪山下的一个破旧小经堂里,学校正式成立,当时有三十个学生,校长、老师、厨师、校工都是同一人,就是创办人洛桑曲丹喇嘛,学生的衣食住行,都由他免费提供,并且不用交任何学杂费。
五年后的今天,除了二十个孤儿,远近村庄失学的穷孩子也来这里上学,最远的甚至来自四川省巴塘。
现在,这所实现全免费的学校已经有八十七名学生,除对面村庄日尼贡卡的十几个孩子,其他的都住在学校里,衣食住行还是由学校免费提供。
在过去的两年里,十五名学生顺利毕业,考进西藏的盐井中学,而他们读书生活的费用,依然由洛桑曲丹喇嘛提供。
喇嘛说过,只要这些孩子能读上去,他就一定供到底。
一年前,学校有了自己崭新的两层楼新校舍,是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白马雪山保护局共同捐助筹建。
校舍一层是教室,二楼是学生和老师们的寝室。
由于2005年发生大众慈善学校校长贪污社会捐助款的事件,学校所在的云南德钦县开始清除私立学校,六所私立学校中,只有这所学校存活了下来,其它的都被关闭。
学校之所以被政府接纳,是因为在创立的五年来,学校的每一分收入和支出,都有详细的账目。
目前,学校共有七名老师,四名汉语老师,三名藏语老师。
由于教育局的接管,其中两名老师是由教育局支派来的。
一名藏语老师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委派,两名藏语老师由学校聘用,另外两位则是志愿者。
要说明的一点是,学校的一切开支,从衣食住行,到学习用品和书籍,还是和以前一样,由洛桑曲丹喇嘛负责解决。
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戏称喇嘛不是“校长”,而是“缘长”。
是的,学校的大部分经费都是由洛桑曲丹喇嘛利用他在佛教界的影响力从社会各界的善心人士处“化缘”得来。
另外一部分,则是由政府和基金会提供捐助。
云南省委副书记丹增已指示有关部门在2005、2006两年向学校提供10万元的资助。
世界援藏基金会从2001年起每年向学校捐助28200元,在2004年,由于学校的藏文考试在迪庆州名列前茅,作为奖励,那年的资助金增至68000元。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管洛桑曲丹喇嘛如何去努力,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做父母的都知道,将一个孩子抚养成人有多么不容易,而这里,有这么多的孩子,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即使只是简单的解决孩子们的吃喝问题,花费也是巨大,学校常常陷入资金危机,洛桑曲丹喇嘛不得不常年在外为资金奔走。
作为一个只会在这里短暂停留的志愿老师,看着这些脏兮兮、却和城市里孩子同样聪慧的孩子们,心里有时候会充满希望,有时候会无助悲哀:
他们还那么小,饿着肚子也会在大山里快乐地跑来跑去,但他们并不懂如果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未来。
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样,向洛桑曲丹喇嘛表示敬意,五年来,为了这个学校和这些孩子,他已经由一个富喇嘛变成一个穷喇嘛。
他曾是香格里拉“松赞林寺”的佛学教师,无论是学识和为人都德高望重。
现在,他把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作为一生的修行。
除了学生犯了大错会让他动怒外,平时他怎么看都像一个乐呵呵的弥勒佛。
而在笑容的背后,有你我想象不到艰辛和困难。
逃跑的张伦有同学
这个叫张伦有的家伙,今年十五岁,从头到尾,做了我十一天的学生。
2006年的2月28日,云南大理阳光灿烂,我在街头乱逛,等待校长喇嘛来接各地捐款为学校买的大米和菜籽油,顺便也把我这个预备役老师接走。
那个家伙,张伦有同学,据说他也在大理街头,但不像我这么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而是花5毛钱买了张红纸,在上面写了一堆歪歪扭扭的毛笔字,铺在地上,老老实实地找工作。
那张红纸我看过。
是在来学校颠簸的车上,他带着谦虚和惶恐的笑容,小心翼翼从裤兜里掏出来给我的,纸折得整整齐齐,保存完好。
上面写着自我介绍,他是贵州人,因父母离婚出走,家里没人要他,希望有好心人给他一份工作。
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写道:
我只求三餐一宿。
不要做小偷,不要跟坏人走。
这个几乎没怎么离开过家乡贵州偏僻山村的小孩,居然一个人跑到大理来,还想到这样的找工作方法,而不是像其他流浪儿一样跪地乞讨过活。
我很惊讶,问他,你怎么知道这里的。
他说,先坐汽车,再坐火车,再坐火车,就到这里喽。
我又问,你想找工作,怎么不去广州,那里赚钱容易。
他回答:
听人说广州有很多坏人,不敢去。
在大理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张伦有同学白天在大街上铺红纸找工作,晚上,睡5块钱一晚的旅馆廉价大通铺。
但谁会给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一份工作呢?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身上带的钱快花完了,于是他就睡在工地上的水泥管子里。
他用带着浓重贵州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
“水泥管子里不好睡,晚上冷得很咧,睡不着,只好把身子紧紧缩成一团。
”
就在身上带的钱快花完时,校长喇嘛在街头看到了他。
喇嘛看不懂汉语,他就请人把纸上的内容翻译成藏文。
后来喇嘛跟我说,当他通过翻译知道张伦有在纸上写的内容后,这里,痛,很痛,他指指自己的胸口。
等我找到校长喇嘛时,张伦有同学已经跟在喇嘛屁股后头了。
他准备去喇嘛的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继续上学。
当得知我是新来的老师,他露出兴奋的表情,说他在家上过小学三年级,数学不好学,语文好,最喜欢上语文课。
我们坐上喇嘛开的卡车,带着捐助款买的大米和菜籽油,在下午3点向学校进发。
一路上,我给他糖吃,一颗、两颗、三颗,吃到第四颗糖时,他开始告诉我更多的事了。
他爸爸是森林里的伐木工人,他们家穷,住茅草屋,因为没钱交学费他已经失学两年了。
爸爸妈妈离婚后,妈妈跟人走了,爸爸偷偷把家里养的猪卖了,没和他打个招呼,也消失了。
爷爷奶奶还在,但住在六盘水,他已经很多年没去过那里了。
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
于是他跑进林子里,把属于他们家的树砍了,带着卖掉树的钱,自己出来找工作,从家里出来已经十几天了。
他说他们老家原来有很多大树,大得好几个人都抱不过来,林子里还有很多动物。
现在大的树都砍完了,动物也很少了。
卡车在大山里绕了十个小时,越开越荒凉,起先还会路过县城,后来只能路过小镇,再后来只能远远的看见破破的小村落,再后来,连人影都看不到了。
张伦有在车上披着我姐姐给我的羽绒服,两眼一直盯着窗外看,嘴里时不时冒出一句:
这里真荒凉,比我们那里的村庄还差。
这个才十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那个收留他的人,穿着红黄长袍的是个藏族喇嘛。
那个白马雪山藏文学校,是他一手办起来的慈善学校,在那里读书的孩子,都是像他一样没人照顾的孤儿,或者是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的贫困儿童。
他也不知道,我们去的地方是云南和西藏的交界处,属于藏区,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住的全是生活习惯和我们汉族人相差巨大的藏民。
而他未来的同学,都是藏族小孩。
他会习惯那里吗?
我心里冒出一丝忧虑,即使是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车窗外的气温越来越低,我知道我们所处的海拔越来越高,看看表,已经将近夜晚8点,云南高原的夜幕终于拉开,开始笼罩连绵不尽的大山。
我和张伦有一起缩在我姐姐的羽绒服里,盯着车灯照耀下越来越险的公路,借着微弱的光,我们可以看到公路下的悬崖,不时有类似野兔的小动物一晃而过。
凌晨1点,我们终于到达学校。
那天是阴天,夜幕里没有一颗星星,学校只亮着几盏微弱的灯光。
我们看不清学校到底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地方,楼好像是新盖的。
几个人影出来迎接我们,说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藏语。
风很大,在耳边呼呼地响,很轻易地穿透身上的衣服,人忍不住地发抖。
我被安排进一楼的一个小房间,房间不干净,也不脏,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一张像木箱子的床,一盏同样昏暗的电灯,两条薄薄的被子。
电灯开关让人吓一跳,是两个裸露着铜丝的电线,简单地搭在一起。
我放下行李,顶风摸黑找到水池洗刷。
在混乱中,张伦有不知被带去哪里了。
那一天最后留下的印象,是我在西藏旅行时曾闻到过的那股难闻又让人难忘的奶腥味,在房间里,在被子里,在水杯里,无所不在。
人群的嘈杂渐渐散去,只留下窗外呼呼尖叫的风。
我钻进自己带的睡袋里,翻来覆去了很久也没睡着,我想张伦有同学应该也不会很快睡着。
睁开眼的第一天,是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清晨7点,这里的太阳还没起床,我拉开前面的窗帘,远处是一座雪山,打开后面的门,远处又是一座雪山。
裹着羽绒服出去转了转,风还是很大,似乎比昨晚更冷。
原来学校建在了两座山之间的垭口上,左边是白马雪山,右边是一座光秃秃几乎不见绿色的荒山,但据说是当地著名的日尼神山,在藏历吉日,远近的村民都会来转山和朝拜。
风从两山之间直灌而入,从不停息,毫不留情。
太冷喽太冷喽,这个地方太冷喽。
那贵州口音在耳边响起时,我才记起还有一个名叫张伦有的汉族小孩,昨晚和我一起来这里了。
他双手抱肩,裹着衣服,缩着身子走了过来,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身上不停地颤抖。
走近一看,一件短袖T恤加一件薄薄的蓝色单层外套,就是他身上全部的衣服。
我让他回去把全部带来的衣服都穿上,他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子,好像犯了错误似的,说,没有了,没衣服了。
我回到房间,从包里翻出自己的羊毛背心,陪他去寝室换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学生的寝室,在二楼。
里面的味道,让我想起城市里的垃圾堆,唯一的区别是,垃圾堆一般都死气沉沉,很少有人光顾。
而这里,却臭得生机勃勃,人头攒动,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藏族孩子聚在一起,那光景十分了得,让人难忘。
床分上下铺,孩子们有的正在穿衣服,有的还赖在被窝里,有的正打算出门,看到我这个陌生人,都伸长了脖子,像第一次在动物园看猩猩一样,看我。
床上的被子,脏得好像几百年没洗过,但那些还赖在被窝里的孩子,却像抱着亲人一样抱着被子,毫不在乎。
我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了,不能一到这里就露出厌烦和退缩的样子。
于是强忍着臭味和孩子们打招呼,孩子们嘻嘻哈哈笑成一片,接着有的用生疏的汉语跟我说你好,有的害羞地把头缩回被子里,有的睁着大眼睛,盯着我,一副茫然的样子。
离我最近的那个小男孩,带着一顶脏乎乎的帽子,鼻涕几乎要掉下来,正在你担心之际,说时迟,那时快,猛然吸了回去,声音响亮,干净利落。
但是没等我眨上一眼,那鼻涕又从鼻孔里滑了出来。
忍不住再告诉你一次,寝室里的那味道实在难闻。
张伦有的床在靠门的下铺,被子是学校新发给他的,所以干净得发亮,和寝室的环境极不协调。
他哆哆嗦嗦地穿上我的羊毛背心,太大了,松松垮垮的像马戏团的小丑。
我忍不住笑出来,其他孩子也笑起来,张伦有,也露出他那招牌式的惶恐卑谦的笑容。
这时,也许有了其他藏族孩子做比较,我第一次对张伦有的样子有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是个流浪儿,但毕竟只流浪了十几天,比起他未来的同学们,他的脸上身上干净得像个奇迹。
清晨的光芒越来越明亮,他的肤色在这灰色的房间里显得很白,一口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混杂在一片藏语声里,让人觉得有点孤单。
头发有点长了,盖住宽阔的前额,鼻子微微有点塌,嘴唇厚厚的很饱满,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眼神,一会看你,一会看地,一会又看窗外,很难让你抓住。
我们走出寝室,他偷偷地对我说,这里怎么这么脏,像垃圾堆一样。
从二楼走到一楼,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很多遍,像个?
嗦的小老头。
我明显感到,跟在我后头的那个汉族小孩,已经对这里开始失望了。
而我呢?
我两年前就去过西藏,对藏区的生活条件和习惯早已耳闻目睹,有所体验。
来这里之前,对这里的生活也幻想过很多次。
但现在,当真的身处这里时,我不敢说自己不失望,也不敢说自己失望。
那种感觉十分复杂。
我看着远处云雾缭绕的雪山,也看着近处光秃秃什么都不长的山坡,一种恍惚的感觉把我带离现实。
时间慢慢吞吞的,像个山间行走的驼背老妇,三天时间仿佛用了三个月才过完,天气开始好转,虽然风还很大,但一到晚上,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夜空里,星星密密麻麻,多得让人失去了去数它们的信心。
也许是山间路途遥远,也许是私立民办学校不受重视,总之开学时间已经过去两天,教科书还没运到学校。
这急坏了张伦有同学,他一次一次的追着我问,老师书到了没有?
老师,书还没到?
老师,明天书能到吗?
老师,那后天呢?
这三天还发生了一些事。
在送我们到学校的第二天,校长喇嘛又开着那辆二手破卡车,上了蜿蜒的山间公路走了。
这次载的不是大米和菜籽油,而是十五个学生和他们的铺盖。
这十五个学生是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首届毕业生,他们考进了西藏的盐井中学,而喇嘛继续负责他们上中学的生活费用,甚至包括开学放假期间的接送。
张伦有同学拒绝吃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饭菜,因为它们的味道实在太奇怪了,吃了就想吐。
我尝试着吃了那些饭菜,饭是先煮一会,然后再蒸出来的,似乎很软,又似乎很硬,如果是叫我妈妈来吃一口,她老人家一定会说这饭还没熟。
菜其实就是一碗汤,只是上面飘着些蔬菜,可能用的油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不管是闻起来,还是吃进去,味道都奇怪,难以下咽,像在吃药。
但还不至于吃完就吐,我就着菜汤,吃了满满两大碗的饭。
吃完后漱漱口,摸摸肚子,吃饱的感觉,和吃好菜好饭吃饱的感觉没什么两样。
我把这感觉和张伦有同学说,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作用,还是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总之,之后他每餐都乖乖地吃饭了。
又是另外一天,已经过了下午两点,我和张伦有同学都没吃饭,学校食堂已经关门。
我揣着鼓鼓的钱包,带着张伦有,沿着学校边上的104公路一路打听,走了将近二十分钟,终于在学校对面的村庄日尼贡卡找了个小卖部,花出去5块钱,几乎把整个小卖部掏空了,买来的食品上尽是灰尘,让我感觉自己简直是在非法购买出土文物。
小卖部老板,我一个学生的爸爸用生硬的汉语跟我说,末有开学,不敢进噢,末有开学,不敢进噢。
我下意识地看看手上那5毛钱一包的瓜子,上面根本没生产日期。
老师,你吃嘛,老师你吃嘛。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分给张伦有一袋饼干,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后,热情地非要分给我几块。
东西虽然是我给的他,吃在嘴里也没什么饼干应有的味道,但他这举动带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地受用。
大概这就是为人师长的感受,看到学生做出些懂事的举动,总是莫名其妙地开心。
这个小小的日尼贡卡,小得只有十一户人家,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小孩,还有一些牦牛,几头黑猪,几只母鸡。
村子沿着公路依山而建,公路旁,房子边都种着桃树、梨树、核桃树还有杏树。
桃树和梨树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像神话故事里的老树怪,没有树叶,却开满了花,粉红色嫩绿色的,一簇一丛,就在你路过的身旁。
三月的阳光温暖人心,我们一前一后沿着公路走着,一头离群的老牦牛,摇着驼铃,叮叮隆隆,不紧不慢的,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问张伦有,这地方漂亮不漂亮,张伦有说,漂亮的。
就在张伦有说这地方漂亮后的第二天,学校终于开学了。
书是运到了,但数量不够,只好两个同学用一本。
书上该写谁的名字,还要互相争论一番。
尽管这样,学生脏脏的脸上还是显露出无限欣喜,这感觉我们小时候都有,新书的油墨香总能刺激人的幸福神经。
张伦有如愿加入我做班主任的三年级。
那是他来学校后一直唠叨的。
他坐在第一排,上我的语文课,他汉族人的优势显露无遗。
上第一堂课我让学生们轮流上讲台介绍自己。
他在下面憋了很久,总算轮到他上台了,先给大家深深鞠了个超过90度的躬,然后操着贵州普通话说:
大家好,我叫张伦有,今年15岁,上小学三年级,来自贵州省兴义市晴隆县花贡镇竹塘村。
掌声一片。
上语文课,上数学课,上藏文课,上音乐课,上体育课,上劳动课,张伦有同学在白马雪山藏文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生活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几天。
这几天又发生了一些事。
我的手被刀子划伤,张伦有勤快地帮我洗衣服,勤快地去学校后山荆棘丛里晾衣服,又勤快地帮我收回来。
张伦有洗脚时借别人的拖鞋,忘了还,结果弄丢了一只。
主管生活的老师觉得这孩子比起这里的藏族孩子,过于娇气,缺乏受苦的经历,于是吓他,如果找不回来就要他赔。
这个只带了小背包出来,什么都没有的孩子吓坏了,哭了,让同学敲我的门,自己偷偷跟在后面,眼泪还没有擦干。
拖鞋当然没让他赔。
但经过这件事,我发现自己粗心了,这个和我一起来的孩子,没有任何生活用品,从毛巾到脸盆,从牙刷到吃饭的碗。
于是在一次为学校采购物品时,我帮他都买齐了。
上海捐赠过来的物品里,我帮他挑了几套能御寒又时髦的衣裤。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穿着新衣服的张伦有在校园里走动。
最后发生的那件事,出乎意料。
张伦有逃跑了。
穿着学校发给他的新衣服,带着我给他买的碗、调羹、拖鞋、牙刷、牙膏和一盒百灵鸟牌面霜。
我赶到他的寝室里时,被子乱糟糟的团在床上,人已经不见了。
他的同学说,昨天晚上看见他在整理东西,今天早上天没亮就走了。
我和学校的藏族老师达瓦雇了辆面包车,一路追赶,在离学校17公里之外的路上找到了他,达瓦老师惊讶地说,这小子太厉害了,真能走。
他低着头,我几乎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我们坐在公路边,下面就是深不可测哗哗流淌的金沙江。
吃早饭了吗?
我问他。
他摇摇头,嘴巴微微动了动,我听不到任何他发出的声音。
我从包里拿出饼干和水给他。
他吃得很小心翼翼,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
你想去哪里?
我问。
这次他的回答有声音了,他说,这里太脏了,同学又不讲卫生,我想爷爷奶奶了,我想回家,我想家乡的树林子。
你打算怎么回家?
我问。
走路回去,他说,先走到大理,然后爬运煤的火车回家。
以前我们家乡有人爬过。
我转头看看急流的金沙江,哭笑不得。
我耐心地告诉他这里离大理有多远,那天我们坐车都花了十个小时,如果走路,要几天几夜才能到,山里晚上这么冷,就这么走回去,不被冻死也会饿死的。
我忘了自己说了多久,说了多少大小道理,我只记得最后我说,老师答应你,你先在这里试着读一学期,如果等到放假了你还不适应这里,老师就亲自送你回家,顺便去看看你家乡的树林。
他还是低着头,嚼着嘴里的饼干,嚼了半天,终于点了点头,说,好的。
事情终于解决了。
这时早晨升起的太阳刚好照到峡谷里的村寨上,白色的房子,黄色的屋顶,绿色的麦子,白色的江水,牛羊已经出来吃草,炊烟已经袅袅升起。
江的这边,我们在云南地界,江的那边,则是四川。
我看看身边这个无助的孩子,看看一江之隔的云南和四川,想起刚才自己一本正经充当一个明白事理的师长,又想起以前在上海日日夜夜上班下班的忙碌生活。
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当一个老师,但责任已经到肩上了。
张伦有同学最后还是固执地走了,还算令人欣慰的是,这次他不是逃跑的,而是校长喇嘛亲自把他送到县城香格里拉,买了张去昆明的长途汽车票送他上车,最后让他从昆明自己坐火车回家。
临走时,我给了他300块钱,大半个已经快被风干的面包,一把几乎没牛奶味的牛奶糖,几个长得营养不良的苹果,还有一包新康泰克感冒药。
现在的教室里,张伦有同学坐的那个位子仍然空着,我常常想起他那飘忽不定、一会看天、一会看地、一会看你的眼神,也常常想起他最后跟我说的那些贵州口音普通话,他说他没办法不想爷爷奶奶,没办法不想家,一想家的时候,心里的那个感觉,很痛,一想起来就受不了。
对不起,老师,真的对不起,我真的想回家。
这大概算是我短暂教师生涯的第一个挫折。
我曾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会是受学生爱戴和崇拜的好老师。
但事实上,我甚至都不能说服一个流落他乡的孩子留下来读书。
张伦有临走的那天,天空阴云密布,山上下着雪,学校下着雨,很冷。
同学们都冒雨到校门口送他。
我一再对他说读书有用的道理,一再对他说回去不能干坏事,一再对他说路上注意安全,一再对他说那300块钱不要乱花,回去能上学的话就拿去交学费。
他都一一答应了我,但我不确定他真的会按我说的去做。
再说,回到家里一个人他该怎么生活呢?
一切都是个未知数,但我相信这个叫张伦有的家伙,他既然有胆子从家里跑到这么远的地方上,还有胆子走路爬火车回家,他一定会找到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也许是跑到六盘水找久未谋面的爷爷奶奶,也许是村里有好心邻居收养他,也许是跑进林子里,继续砍树卖树为生,也许还有我想不到的办法。
校长喇嘛对他说,不管什么时候,你想回来读书了,联系我们,我们派人接你回来。
他做了我十一天的学生,这期间,他对我说了很多次谢谢,最后那两次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在校门口临上车前,他低着头不停地说老师谢谢你,老师谢谢你。
还有一次是他已经到达贵州新义市时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老师,我只要再坐两次车就可以到家,谢谢你老师,谢谢你帮助我。
我想他说了这么多次谢谢,至少可以证明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我想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未来的路也许容易走些。
打人的坏老师
那个打人的坏老师,就是我。
现在我相信了,现实的破坏力无比巨大。
如果只是躺在家里想想,搭上一辈子时间,我也想不到自己原来是那种人,那种让自己厌恶并诅咒的老师。
抡起教鞭,划出一道丑陋的弧线,愤怒在心中爆炸,理智瞬间灰飞烟灭,这一棒下去,当初幻想为人师表的美妙感觉,粉身碎骨。
我之所以鼓起勇气,在这里揭发自己,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打学生了。
说白了,我还是缺乏承认错误的勇气和应有的态度,你知道,坦白从宽最好在第一时间,我已经错过了。
所以现在我发誓,即使有学生爬到我头上,顽皮地拉屎拉尿,我也不打他了。
事实上,不久前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上完课捧着语文课本,经过一楼的楼梯口,真的差一点被一泡从天而降的童子尿尿到。
有时候我推托责任地怀疑,我那打学生的暴力基因是不是来自遗传,我爷爷、我爸爸、我姐姐都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
按照逻辑推理,最大的嫌疑人应该是我爷爷,因为他是旧社会的私塾先生,你知道,那时候体罚学生是吾国的优良传统。
但他老人家在我4岁时就去世了,我已经记不起他到底是不是个威严四起,令人敬畏的老头。
而我的爸爸和姐姐都是性格温和的人,我很难想象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挥舞着棒子,凶神恶煞。
罪孽还是在于自己。
刚开学那几天,你知道,我信心百倍,以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好老师降临在白马雪山上。
我捧着我的笔记本电脑,拿着地球仪,还泡上一杯咖啡,神气十足地来到讲台前,兜售自己二十多年来所见所闻所想,指望着在一堂课时间里,就为这里的孩子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你知道,我雄心勃勃。
学生们张着嘴巴,用喜欢得恨不得一口把你吞掉的目光,欣赏着你。
后来你才知道,他们第一次面对你买来的新篮球,也是这种目光。
但当时你得意无比,你觉得你甚至都不用动嘴,就能把他们征服了。
你以为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就是他们的神,就算告诉他们1+1=100,他们也会相信你。
现实就像这里呼啸不停的山风一样,毫不留情。
时间有如转经,一天转过一天。
学生们已经和你混熟了,看见你已经不那么害羞了,甚至还会同你开开玩笑,弄个小恶作剧作弄作弄你。
但同时,学生们也摸透了你,吃定了你。
其实你只是一个会在讲台上胡说八道吹牛不打草稿的老师,高兴时他们会陪你拿着课本玩玩,不高兴时,哼,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坏小子们开始行动了,开始造反了。
不做作业的,上课睡觉的,上课吃东西的,上课溜出教室外面的,上课打架的,上课不带笔也不带课本还不带脑子的,一问三不知,三问九不知的……
你发现,你这个举世无双的好老师,居然到了快被活活气死的边缘。
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从沮丧和愤怒中缓了过来,跑去向其他老师请教。
得到的答案很简单。
打。
那几个坏小子在家时野惯喽,好好说根本不听,没别的办法,打几下就乖了。
老师苦笑着对我说,没别的办法。
回到课堂,再次面对这些小坏蛋的捣乱,你觉得无可奈何,还是入乡随俗吧。
先换一根结实点的教鞭,当凶器。
一开始,你还下不了手,你甚至连一次架都没打过,从小到大,最大的冒险,也就是小时候拿着棒子追着鸡鸭四处乱跑。
但你很无耻,居然想到请刽子手帮忙,在小说《尘埃落定》里,藏族人管刽子手叫行刑人。
你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支教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2机组现场施工用电布置措施.docx
#2机组现场施工用电布置措施.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