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docx
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docx
- 文档编号:28267109
- 上传时间:2023-07-10
- 格式:DOCX
- 页数:8
- 大小:23.08KB
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docx
《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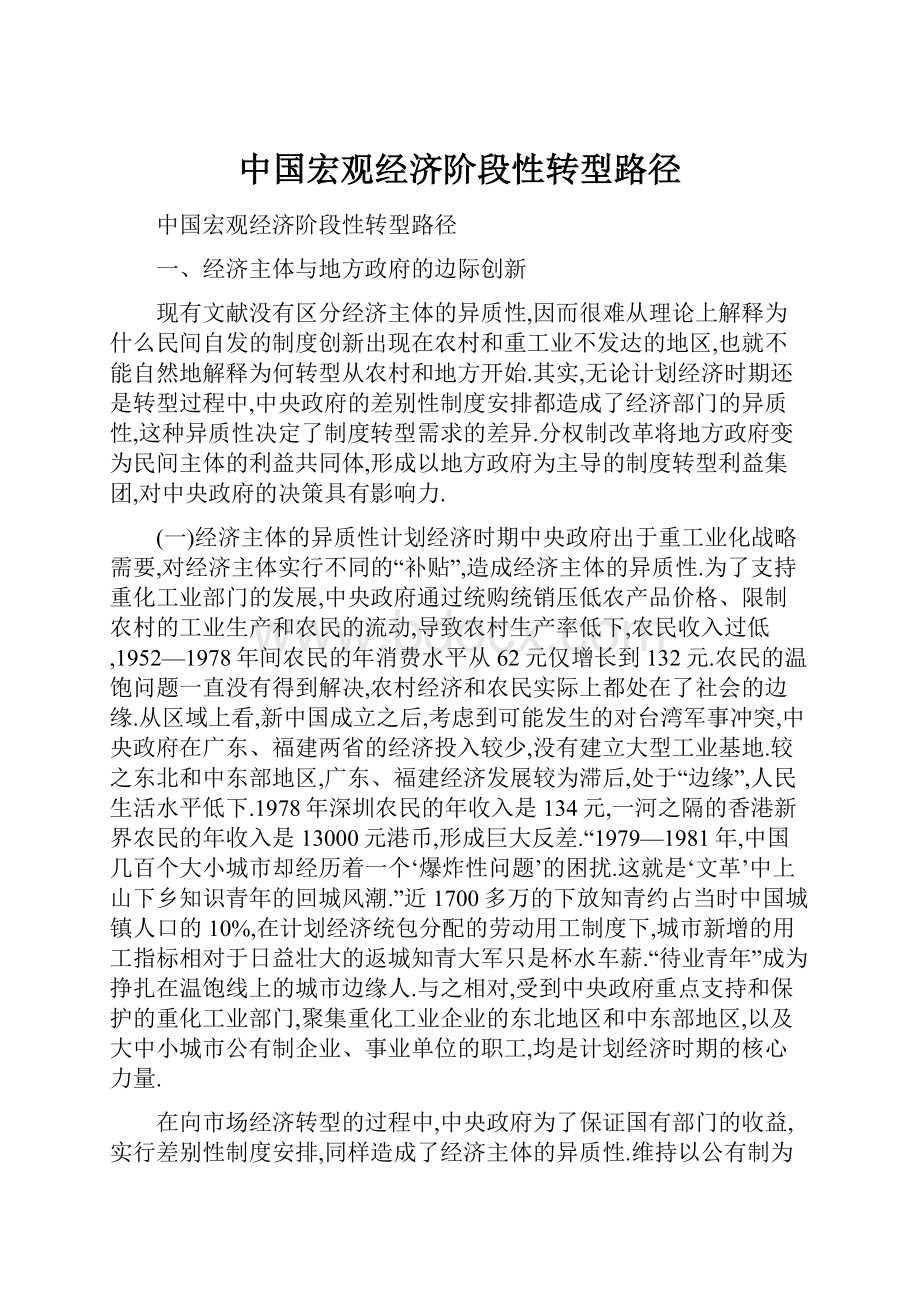
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
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转型路径
一、经济主体与地方政府的边际创新
现有文献没有区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因而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出现在农村和重工业不发达的地区,也就不能自然地解释为何转型从农村和地方开始.其实,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差别性制度安排都造成了经济部门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制度转型需求的差异.分权制改革将地方政府变为民间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制度转型利益集团,对中央政府的决策具有影响力.
(一)经济主体的异质性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出于重工业化战略需要,对经济主体实行不同的“补贴”,造成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为了支持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中央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压低农产品价格、限制农村的工业生产和农民的流动,导致农村生产率低下,农民收入过低,1952—1978年间农民的年消费水平从62元仅增长到132元.农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农村经济和农民实际上都处在了社会的边缘.从区域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对台湾军事冲突,中央政府在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投入较少,没有建立大型工业基地.较之东北和中东部地区,广东、福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处于“边缘”,人民生活水平低下.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是13000元港币,形成巨大反差.“1979—1981年,中国几百个大小城市却经历着一个‘爆炸性问题’的困扰.这就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回城风潮.”近1700多万的下放知青约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10%,在计划经济统包分配的劳动用工制度下,城市新增的用工指标相对于日益壮大的返城知青大军只是杯水车薪.“待业青年”成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城市边缘人.与之相对,受到中央政府重点支持和保护的重化工业部门,聚集重化工业企业的东北地区和中东部地区,以及大中小城市公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均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力量.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为了保证国有部门的收益,实行差别性制度安排,同样造成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维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体制、土地转让制度,倾斜于公有经济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市场准入条件等,都是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补贴”使非公有经济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的不对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异质性的表现.相对于“体制内”,“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实际上居于弱势地位,成为转型经济体的边缘力量.总之,中央政府实施的差别性“补贴”政策造成了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得到“补贴”过低的部门(边缘经济主体)总是有打破旧体制的激励.分权制下的地方政府作为民间经济主体的利益共同体,利用其组织优势对边缘主体的制度创新进行整合,请求中央政府承认,形成的是一种“边际创新”,因为这种创新对旧体制的革命性是边际意义上的.
(二)边缘革命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决定了制度需求的差异性.较之核心部门,边缘力量在旧体制下受剥夺最多.制度转型可以使它们摆脱中央政府的歧视性“补贴”,获取制度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收益.越边缘的部门,制度转型带来的净收益越大,因而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也越大.另一方面,边缘部门的边缘性、分散性及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边缘力量的制度创新需求难以形成集团行动,没有向中央政府表达制度需求的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长期压抑的制度需求一旦超过其承受极限,可能会引发“爆炸式革命”.1978年,面对大旱之下可能的饥荒,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户户主一致同意秘密“分田单干”,并立下“生死状”;在毗邻香港的广东边境,温饱线上的农民悄悄地尝试过境耕作、开展边境小额贸易等明令禁止的活动;城市里胆大的“待业青年”干起了修鞋、修自行车、补锅磨剪子、裱画、做衣服、开小饭馆等个体经营;以及80年代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涌现的私人钱庄和“抬会”等民间金融组织等都是被逼出来的与现行体制不相容的革命性制度创新.科斯谓之“边缘革命(marginalrevolution)”.边缘革命指的是边缘力量自发的革命性制度创新.
首先,这是边缘部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发性行为;其次,这种创新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且多为中央政府所明令禁止,所以称之为“革命”;最后,边缘革命是在旧体制的边缘、边界上的制度创新,并不触及核心体制的本质.边缘革命当然不会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当边缘革命与主流意识形态或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严重相悖时,必定遭到中央政府的批判或取缔.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民“包产到户”的努力历经三次,均遭批判;广东的边境商贸活动及城镇中的个体经营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遭到取缔;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刚开业即遭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攻击,在无证经营5年后宣布倒闭.“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问题是,为什么某些边缘革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而另一些边缘革命却被扼杀了呢?
也就是说,同样是边缘革命,却有迥然不同的结果.农村承包制、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个体经营最终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民间金融始终被抑制,存在着金融约束和金融摩擦.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革命的对象是边际制度创新,不会触动核心部门与体制,而后者革命的对象是核心部门与体制.
(三)分权制下的地方政府与边际创新地方政府在中国式转型及增长中的作用源自中国的分权财政体制.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一个分权过程.财政的分税制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边际留成率,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权.分权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实行锦标赛似的考核晋升机制.“德、智、勤、绩”四方面的考核内容中只有“绩”较为具体,体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稳定,当地经济发展和经济活力水平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样,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权、能被上级观察到的政绩最大化都与当地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因而地方政府具有捕捉潜在的制度收益搞活本地经济的动机,所以与地方经济主体在自发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合作会多于冲突.与分散、弱势的边缘力量相比,地方政府拥有组织优势和谈判优势,可以进行表达制度需求的集团行动.地方政府利用其信息、知识优势和组织优势对边缘部门的制度创新进行整合后向中央政府请求承认.整合的具体形式包括将民间主体分散的、差别化的制度创新整合为系统的框架式的制度设计,比如根据宝安县搞小额贸易和过境耕作的创新,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率领广东省委讨论设计出了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方案.或者“改头换面”、变通为易于为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形式支持、引导制度创新.如在1978年遭遇特大旱灾后,安徽省委决定实施“借地度荒”,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耕种.
这种规定并没有提出分产到户,看上去只是一种救急措施,实际上暗合了农户分产到户的需求.还有的地方实行先斩后奏,先暗中支持民间主体创新,待取得一定成效后再行整合向中央报告.地方政府的再创新只是对边缘革命的系统化和委婉化(变通为中央政府更以接受的形式),并不改变边缘革命的基本特征,不触及核心体制的本质,只是对旧体制的边缘(边缘制度、边缘部门、边缘区域)进行的局部创新.创新是边际意义上的,故而本文将地方政府对边缘革命的再创新称为“边际创新(marginalinnovation)”.比如家庭承包制首先出现在公有制性质最为薄弱的农村,并没有撼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基础,只是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权,而且刚开始只是出现于最贫穷的地区(安徽和四川).习仲勋“要权”建立经济特区也是在远离重工业中心的广东,而且只是广东的几个小区域.本文认为不是边缘革命、而是地方政府基于边缘革命的边际创新启动了中国式转型.边缘革命固然是中国式转型的萌芽与发动,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再创新并向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边缘革命可能像历史上多次自发的创新一样被取缔.
二、边际创新引致的“两阶段转型假说”边际创新
不触动中央政府的垄断租金,因而避开了“诺斯悖论”;边际创新还传达了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事实有效”的信号,降低了转型的思想成本;两方面的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转型的净收益,由此增加了中央政府提供制度供给的概率.于是,“边际创新”成为制度转型的根本动力.在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为保护核心主体而形成的非竞争性市场制度对已转型的民营经济和未转型的国有经济造成了差别性“补贴”,对非竞争性市场制度的边际创新成为第二阶段中国转型的核心特征.原创论文因此,中国宏观经济转型是以边际制度创新为特征的两阶段转型.
(一)边际创新引致的制度转型边际创新驱动中央政府制度供给的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边际创新降低了转型的思想摩擦成本,另一个是绕开了“诺斯悖论”.首先,边际创新传递了转型“事实有效”的信息,降低了中央政府制度供给的思想成本.当边缘革命受到主流意识和利益集团抵制时,邓小平的态度总是:
再等等,再看看.等的就是民间制度创新的效果.1979年,实行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卖给国家公粮约4450万公斤,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粮食的总和.如此大的反差足以证明包产到户“事实有效”.正是包产到户的“事实有效”,让反对者最终改变了认识:
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特殊政策,可以在贫困地区实施包产到户,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是,边缘革命并不能直接冲击旧思想旧体制,而地方政府的支持、宣传与游说传递了边缘革命“事实有效”的信息.较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改善地方经济绩效的制度安排上拥有信息和知识优势,对边缘革命“事实有效”还是无效的认识与判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地方政府拥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通过正式渠道(如会议、汇报、文件等)或非正式渠道(游说、找关系、私下沟通等)向权力中心传递反映本地利益的制度创新需求,而且是经过地方政府整合和协调、更易被主流意识形态接受的制度创新需求,因而增加了中央政府“放权”、提供制度供给的概率.第三,边缘部门的转型避开了“诺斯悖论”,使边缘力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均受益,实现了“帕累托效应”.中央政府的垄断租金只来源于受保护的核心经济主体,因而边缘部门的转型影响不到中央政府的垄断租金.这是中央政府愿意顺应民意而放权的重要原因.比如,中央政府在审批“经济特区”时,也曾考虑过同时在大连、青岛和上海等地建立.正是出于担心冲击社会主义的根基,最终只是把“特区”设立在远离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东南沿海.因为从重工业化发展道路来说,广东和福建省本属于边缘省份,其改革不会触及经济的主体力量;制度变迁只是在“特区”内,而且是试验田性质,即便出现问题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广东省和福建省,更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整体;而且,特区“特”办,基本不触及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制度和结构体系,所以推行起来也相对容易.习仲勋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宗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与中央政府经济改革的目标完全一致,又不触动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因而“经济特区”是一个民间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均合意的制度创新,所以就有了中央政府的放权.针对金融体系的边际创新则不同.作为核心部门的金融体制转型固然会大大提高经济效率,刺激总产出,但是却降低了中央政府的垄断租金.“诺斯悖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转型对中央政府是非“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承认创新的概率会降低.
(二)二元转型模式在边际创新的推动之下,边缘部门首先完成转型.因为边缘部门的转型绕过了“诺斯悖论”,所以中央政府放权的概率较大,转型由边缘部门逐步向较为核心的部门推进,形成中国式转型的主要路径.农村历经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股份制和乡镇企业大力发展,逐步进入到农村现代化,城市个体和私营经济也发展壮大.非公有经济逐步由以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领域为主,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由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主,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集团扩张.随着农村和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的认识逐渐清晰,对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抵触有所缓和,公有经济的改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深入.比如在农村改革的影响下,机制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地方国营企业以及所谓“大集体”企业开始试验承包制.1992年在继续完善和推进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开始逐步推进股份制改革试点.之后国企改革历经“抓大放小”,“三年脱困”阶段以及2001年之后的全面改革阶段,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步放弃了中小型企业的国有经营.
上述扩大企业自主权、承包制、股份制、“抓大放小”等“体制内”改革也是地方先自行试验,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形成共识后,再由中央政府主导推进的,因而也是边际创新引致的转型.中国式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上述边际创新引致的二元转型路径.这与中国宏观经济中体制内的公有经济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始终二元共存、非公有经济的规模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扩大的同时,公有经济的规模和工业总产值比重不断缩小、以及公有经济内部一直在改革的事实是相符的.上述二元转型路径大约在2004年左右出现停顿.一方面,从意识形态和舆论上看,2005年左右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04年,“郎顾之争”引发了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大争论,凸显了人们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和“国资进退”的重新思考.与此相关,针对中国式转型与增长暴露出的种种不平衡与不公平问题,围绕着市场化改革究竟是走过了还是未到位的问题,中国社会出现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争论,改革是否继续的问题自1992年之后再度摆到了大众面前.另一方面,从相关经济数据来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元共存的局面趋于均衡.国有经济把持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同时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民营经济在国有经济控制之外的领域趋于饱和,不再有继续扩大的空间.,民营经济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起加速上涨,外资企业的就业规模缓慢上升;公有经济的就业规模自1998年以来处于下降之势,但从2004年起基本保持不变.显示了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二元共存的均衡.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来看,国有经济的比重虽然不断下降,但占比始终维持着最高水平,从2005年起,比重基本不再下降,集体经济的比重也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显示了公有经济的稳定性.最后,从资源配置的机制上看,市场机制和政府控制双轨并存也逐渐趋于均衡.如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自由度在2004—2006年间渐趋稳定,显示出国内经营活动自由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较低,反映转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还是一个缺乏竞争性和自由度的市场经济.转型均衡意味着“改革红利”的消失,中国式增长的诸多问题日渐显现,并冲击着中国式转型的均衡.这表明,中国进入“深水区”的第二阶段转型已呈现显著特征.
(三)“两阶段转型假说”的机制在上述转型的第一阶段,只要转型带来的收益大于中央政府的“补贴”,经济主体都有转型的激励,如果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补贴小于转型带来的收益,则经济主体没有转型的动力.因而第一阶段的转型将在转型收益等于中央政府“补贴”的经济主体处实现均衡.在第一阶段转型中,低效率的公有经济与非竞争性市场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已转型的非公有制部门面临较大的制度摩擦成本(institutionalfrictioncosts),这是非公有部门的市场化运营与非竞争性市场制度不兼容造成的摩擦成本.制度摩擦成本实际上是未转型的核心部门对已转型部门的掠夺,已转型的非公有经济部门成为经济中新的边缘部门.作为边缘部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总是有制度创新的需求,比如温州地区多样化的民间金融组织就是新的边缘革命.此边缘革命与第一阶段的边缘革命不同.这时边缘革命针对的是核心部门及其体制,其转型创新是对核心体制的革命.这时的边际创新,即地方政府要求民间金融合法化的请求也就是针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金融体制的革命.偏向性制度安排造成的制度摩擦成本降低了非公有部门的利润,一旦出现外部冲击,非公有部门即陷于危机.
在转型经济体中,只有非公有经济才能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非公有经济陷入困境会使产出降低,从而危及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如果经济增长受损程度较大,危及到社会稳定时,中央政府不得不调低垄断租金预期.这时,“诺斯悖论”得到缓和,中央政府最优策略变为顺应民意,推进制度转型.第二阶段的转型依然是边际创新推动的,转型均衡将在中央政府的垄断租金降到最底线时出现.显然,边际革命引致的制度转型具有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经济中最边缘部门及其地方政府发起边际革命,“倒逼”中央政府推动转型由边缘部门逐渐向核心部门推进,在某一边界部门实现转型均衡;第二阶段,由于制度摩擦成本,已转型部门成为新的边缘部门,新的“边缘革命”及地方政府“要权”依然形成边际革命,“倒逼”中央政府从第一阶段的均衡点进一步向核心部门推动转型.这就是边际创新引致的两阶段转型理论.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型,正开启第二阶段的转型.在国有核心部门的外围,民营经济的危机与革命、地方政府的请求,继续成为驱动中国转型的动力.
三、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决定了转型需求的差别性,越边缘的部门转型的激励越大.边缘革命和边际创新是对非核心制度的革命与变革,不触动核心部门的公有制基础,因而不会引起“诺斯悖论”,所以中央政府可能放权.基于边际创新的转型是破解“诺斯悖论”之谜的关键机制,这一机制完成了中国的第一阶段的转型.而第二阶段转型,针对核心经济主体的边际创新即使会逐渐冲击中央政府的垄断租金,但由于对经济增长具有强推动作用兼具对社会稳定的保障,第二阶段的转型一旦成为边缘力量的“共同信念”,并成为某种“集体行动”,将会弱化“诺斯悖论”,再次成为转型的驱动力.“两阶段转型假说”不仅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式转型的“诺斯悖论”之谜,还可以诠释中国式转型的一系列特征.在中国转型早期出现的所谓的“增量改革”和“计划外”,是因为边际创新引致的转型是从计划体制核心之外的边缘开始的,因而转型后的边缘主体相对于核心体制是“增量”,也是“计划外”.21世纪头几年出现“国资进退”的争论和“国进民退”的逆流,是因为国退民进的转型进程到了第一阶段的均衡点,转型已经触及到了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出现停滞、反复等现象是必然的.
中国未来的改革与转型将依然从民间呼声最大、也即改革收益最大的部门入手,渐次市场化.而政府为了加速市场化,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可以做的努力包括:
对于初级行动团体已经形成的一些制度创新予以认可、支持、推广;舆论上做宣传,降低思想摩擦成本;弱化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降低改革的阻力;在旧体制力量过于强大的部门,“做出”增量,形成新的边缘力量,推动转型的进程.第一阶段的中国式转型决定了粗放式的中国增长模式.在这一阶段,市场化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国有经济的过度投资效应共同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因而,不难理解为何高效率的民营经济虽然不断扩张,但是在高投资驱动的中国式增长中始终没有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同样也可以理解2002—2006年中国结构变迁效应下降之谜,因为这一时期转型趋于停滞,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民营部门流动的转型红利也随之消失.另外,非竞争性的要素市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压低了出口成本与价格,造成了出口规模极度扩张.出口规模虽大,但是与中国产品竞争力和中国宏观经济主导产业结构极为不符,因而难以发挥“出口中学”效应,只是通过促进投资和新增劳动促进经济的扩张,于是强化了粗放的中国式增长模式.因而中国式增长的困局就在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中国式增长的困局将在第二阶段的转型中得到纾解,中国宏观经济将在体制转型中不断转变增长模式.随着民营资本不断进入核心部门,高效率的民营资本投入将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随着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加强,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激励市场主体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压低投入成本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将驱使中国宏观经济向更为集约的增长模式转型.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中国宏观经济 阶段性 转型 路径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贝的故事》教案4.docx
《贝的故事》教案4.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