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浅论伤痕文学.docx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浅论伤痕文学.docx
- 文档编号:27725466
- 上传时间:2023-07-04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31.40KB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浅论伤痕文学.docx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浅论伤痕文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浅论伤痕文学.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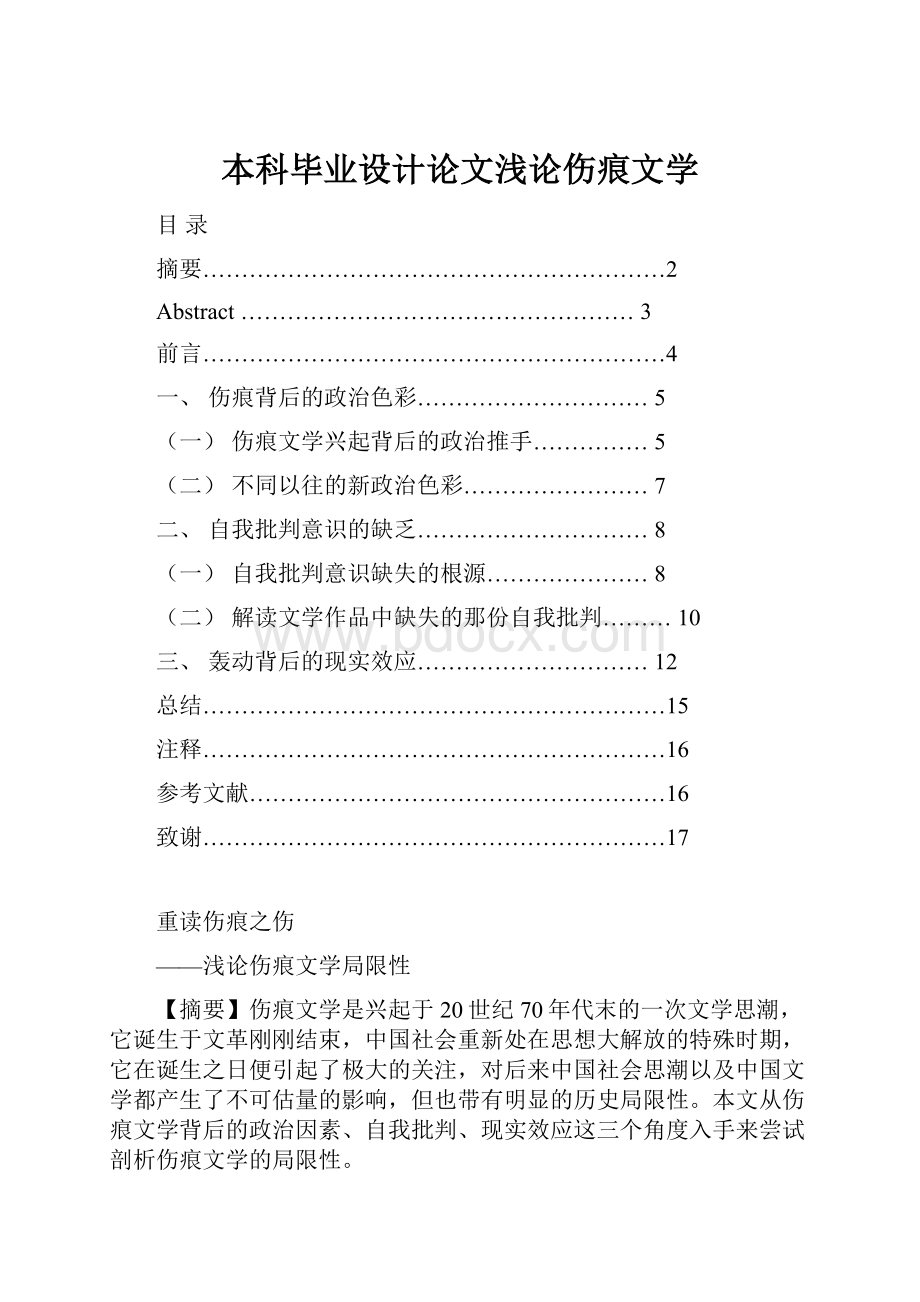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浅论伤痕文学
目录
摘要……………………………………………………2
Abstract……………………………………………3
前言……………………………………………………4
一、伤痕背后的政治色彩…………………………5
(一)伤痕文学兴起背后的政治推手……………5
(二)不同以往的新政治色彩……………………7
二、自我批判意识的缺乏…………………………8
(一)自我批判意识缺失的根源…………………8
(二)解读文学作品中缺失的那份自我批判………10
三、轰动背后的现实效应…………………………12
总结……………………………………………………15
注释……………………………………………………16
参考文献………………………………………………16
致谢……………………………………………………17
重读伤痕之伤
——浅论伤痕文学局限性
【摘要】伤痕文学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文学思潮,它诞生于文革刚刚结束,中国社会重新处在思想大解放的特殊时期,它在诞生之日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后来中国社会思潮以及中国文学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也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本文从伤痕文学背后的政治因素、自我批判、现实效应这三个角度入手来尝试剖析伤痕文学的局限性。
【关键字】伤痕文学政治因素自我批判现实效应
重读伤痕之伤
——浅论伤痕文学局限性
【Abstract】Thetraumaliteraturewasemergesinthelate-1970s'sliteratureideologicaltrend,itwasbornintheGreatCulturalRevolutionjustfinished,theChinesesocietyoccupiedthethoughtfullyemancipatedthespecialtime,ithasthenarousedtheenormousinterestindateofbirth,hashadtheinestimableinfluencetoafterwardtheChinesesocietyideologicaltrendaswellastheChineseliterature,butalsohadtheobvioushistoricallimitation.Originallyfromtraumaliterature'spoliticalfactorand,theself-criticism,realisticeffectthesethreeanglesobtainstoattempttheanalysistraumaliteraturethelimitation.
【keyword】TraumaliteraturePoliticalfactorSelf-criticismRealisticeffect
前言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多数国人都有一种从噩梦醒来的感觉,适应国人解放的情绪宣泄的政治批判的需要,伤痕文学应运而生。
一大批文学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
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结束了文革中那段“非人”的文学的历史。
[1]它率先以活生生甚至血淋淋的艺术形象,让人们重睹了十年浩劫给人民群众所带来的惨重灾难和心灵创伤,在改革开放的前夕,起到了类似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作用。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
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篇短篇小说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
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
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深刻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意义。
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并创作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真正的社会主义悲剧,塑造了悲剧人物、悲剧性格,从而复活了悲剧艺术和悲剧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生命。
“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描写生活”,这种写实的手法开启了80年代关注人性现实意义和价值的新的文学的道路。
[2]在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也是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了人性在遭受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的高压璀璨下的人生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先导。
伤痕文学的这种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因此说它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并不过分。
然而,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用一种现代的、理性的眼光和角度来重新解读伤痕文学时,伤痕文学的局限性就愈加明显。
伤痕文学的兴起、发展背后的政治色彩,伤痕文学自我批判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伤痕文学代表作品轰动背后的现实因素都是我们在解读伤痕文学时值得去深究探讨的一个有益的视角。
一、伤痕背后的政治色彩
(一)伤痕文学兴起背后的政治推手
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十年“红色经典”式的样板文学,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和政治体制的联系还是十分紧密的,当时对于文艺的理解可以形象地用一句口号来诠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在“十七年”文学中,“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曾经是当时文学的核心概念。
一篇文学作品是否“正确”,是否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能否“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概念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好坏的评判标准。
[3]伤痕文学作家群是在“十七年”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那种文学形式甚至是服务于政治的价值观念已经在无形之中潜移默化得深深扎根在其头脑中。
当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在中国大地上绽放开来时,虽然在反映的文学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伤痕文学和以前的“十七年”以及“样板文学”有了根本性的区别,不再是一味地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这个制度下的先进个人,而在于揭示文革中那个让人狂热地丧失理性的制度下对于普通人的摧残和迫害,在“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上都有了明显的调整,甚至是分道扬镳。
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这种巨大分歧的背后,从中可以理出一个明显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文学流派兴起都有着政治因素在其背后推波助澜。
“十七年”文学是在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刚刚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人民尚沉浸在新制度新生活的喜悦之中这样一个大背景,为了配合政治上翻天覆的巨大变革,以及出于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现实政治需要,文学主要的目的在于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为这个制度牺牲奋斗的英雄式的先进个人,体现一种重大深邃的“社会意义”以及“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责任”。
和政治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十七年”文学在其诞生之时就得到了政治权威的肯定和鼓励,进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主流文学潮流。
政治是它迅速的崛起、发展的有力推动器。
如果说把“十七年”文学当作是一部社会主义制度正面教材那么伤痕文学就是一部社会主义制度反面教材,人们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阴暗甚至是丑陋的一面,而且它是在顺应当时政治形式下的一种被扭曲了的“正义”。
伤痕文学诞生于文革刚刚结束的特殊时期,1976—1980,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处于破旧立新的激烈变化时期。
“文革”时期的政治思维方式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之伤和在这个制度下被压迫的人们的悲惨遭遇的伤痕文学无疑是和当时为政治制度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格格不入甚至是想抵触矛盾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引发频繁的争议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快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障碍。
其中尤以1979年《河北文艺》发表的一篇李剑的《歌德与“缺德”》评论具有代表性,文章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伤痕文学”的疑虑和婉转批评,转化为尖锐的政治批判。
该文提到:
让我们伟大祖国的春天在作品中展现出来,让人民从作品中看到绿于金色软于丝的万千细柳,闻到塞外原野的悠扬牧歌和战士打靶归来的阵阵欢笑。
这里,我们不搞一味地美化生活的歌舞升平,也不赞成一些人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
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全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让其跟着其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4]
结果《“歌德”与“缺德”》一经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
文艺界群起反驳,坚决捍卫来之不易的宽松和自由。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率先作出反应。
文章指出:
“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太过头了。
文章批评有些人“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5]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歌德”与“缺德”的大讨论大辩论迅速展开,对伤痕文学的“社会意义”肯定与否以及该如何来给伤痕文学定性、定位成为了当时争论的焦点,但是在当时对于文艺界争论最后的仲裁权是在中央手中的。
在那个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的时期,从文革中平稳过度,没有酿成流血冲突的“新政治”表面上波澜不惊,在这之下其实早已蕴藏着另外一种声音,需要马上及时地得到发言。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以前被“四人帮”迫害下放的老干部老同志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因为在某个方面讲他们本身就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心中对于这场引发十年动乱的文革无疑是抱着否定态度的,但是现实的政治环境和政治身份还不允许他们首先、直接地站出来对文革进行任何负面的评价,需要一个开路先行者,而这个重担无疑就落到了具有政治风向标功能的文艺界的肩上。
所以在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出现引发争议后,政治权威很快就直接介入到了这场争议。
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的直接授意下,伤痕话剧《于无声处》得意进京汇演并最终得以引起轰动;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歌德”与“缺德”的争论最终以伤痕文学的“胜利”而趋于平息,作者李剑也作了自我批评。
在政治因素的推动下,伤痕文学得以正身,并被推到了社会政治舞台的最前端,进而成为一种文学思潮流行全国。
很多伤痕文学作家也纷纷从幕后走到台前接受最广泛的关注和褒奖。
伤痕文学之所以能和“十七年”那样成为一段时期内的主流文学形式,离不开政治因素的支持和推动。
(二)不同于以往的新政治色彩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初期的伤痕文学作家群都是在“十七年”文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还在受“为政治服务”的流行文学观点的约束,更何况伤痕文学之所以能走到台前正是政治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纵然伤痕文学在一定程度确实是当时人们内心最急切最沉痛的呐喊。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伤痕文学作家群的思想虽然获得了很大的“解放”,在文学表现的“主题”、“题材”、“内容”和“思想立场”上都宽松了许多甚至是可以去触及以前创作的“禁区”了,如张贤亮的《灵与肉》通过许灵均这个因为家庭出身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物的坎坷人生经历,大胆而且深刻地涉及到了反右斗争中的血统论的问题;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钟雨和老干部始终默默地相爱而最后谁也没有向对方公开表白自己爱情直至老干部去世的爱情悲剧,提出了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的问题,这在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个主题和题材很少涉及的禁区,而且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雷区,但作为把伤痕文学推上舞台的政治决策层此时在文艺政策上也作了很大调整,具有了适应社会发展和文艺创作的更和蔼可亲的姿态。
所以,“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仅成为这些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潜在而有力的指导观念,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他们的取材、观察、体验和艺术风格,貌似自由、开放的文学局面其实并不是那么“自由”、“开放”。
“人们注意到,他们中的不少人在主题、题材的选择上,在表现的力度和深度上,悄悄地为自己设置了一条无形的“底线”;他们开始用辩证法的思维“干预生活”,塑造人物形象,并努力把这些形象暗暗扭转到与当时“形势”比较适应的角度上。
”[6]在《班主任》之后,刘心武又写了《我爱每一片绿叶》;高晓声写完《李顺大造屋》不久,接着创作了反映改革开放的《陈奂生上城》;张洁既有《爱是不能忘记的》这样振聋发聩的小说,又有《沉重的翅膀》这种热情讴歌改革开放的长篇巨制。
因为背后政治权威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以及关怀,伤痕文学整体上看似是与旧的非人的政治体制划清了界限,摆脱了政治束缚,敢写、敢说、敢揭露,可在这层层表象背后依然还是依附在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的。
“只不过它依附的是一个新的、具有西方人道主义色彩的新的政治,并在这个政治有力支持下演变成了一个有号召力、能唤起刚刚走过文革的人们精神共鸣的文学思潮,”[7]但是并没有跳出浓厚政治色彩的框架,在这一点上和以前的十七年文学,甚至是文革期间的样板文学有着共同点。
二、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一)自我批判意识缺失的根源
伤痕文学作品在内容以及所表现的形式上,给读者最直观最深刻的印象往往就是对“文革十年”的有力控诉,从伤痕文学诞生到后来伤痕文学在政治权威的直接介入下发扬光大,伤痕文学仿佛成了“文革十年”种种痛苦甚至是令人发指的非人遭遇的陈列馆,人们在这里寻找自己经历的文学形象代表的同时也再次寻求慰藉,急切地需要一个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的发言人,发泄不满肯定就需要一个标靶,把矛头指向整个体制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那肯定是不行也是不会被伤痕文学背后的政治权威所认可的,所以在这里控诉“四人帮”的罪恶成了人们自我解脱的一种精神寄托。
这里所说的“四人帮”已不再单单是指江青、姚文元之流,“四人帮”这个名词已经上升为了一个政治概念,那就是文化专制主义、思想专制主义和政治专制主义的高度统一。
在伤痕文学的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主人公所有不幸的遭遇都被认为是那个“四人帮”的迫害所致。
这里和“四人帮”想对应的就是那个新的、具有西方人道主义色彩的新的政治。
通过有力地控诉批判“四人帮”,伤痕文学其实在有意无意中其实已经和新的政治站到了一起,统一步伐一道完成了对旧政治的控诉。
文革的十年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阶层尤其是知识份子阶层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并产生“四人帮”?
难道真的只是毛主席对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就发生了这一切吗?
在我们站在理性、真实的角度来还原和反思历史的今天,“四人帮”产生并存在的土壤们值得深思的。
整个专制的文革政治就像一个金字塔,而“四人帮”就是站在了这个“专制金字塔”的顶端,可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一个庞大的基座,这个基座的构成正是当时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广泛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已经成为了那个专制体制下的一份子,一台专制机器下的零件。
没有下面这个庞大的基座,相信“四人帮”也掀不起让亿万人民不堪回首的十年文革的滔天巨浪。
泪声俱下地控诉了“四人帮”不见得就是对文革和专制体制否定的完成,不见得从此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再次出现“文革”,在这十年灾难背后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批判的最后是应该调整到对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层面。
通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来过滤我们文化和思想的糟粕在根源上避免历史的重蹈覆辙,这才是我们今天来回顾文革、反思文革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人文价值。
作为站在社会和人类思考最前沿,并第一个站出来痛批文革的伤痕文学作家群理应对此一个有更深更敏锐的理解和把握,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对国家、民族的不幸做出一个理性、深刻的独立思考,往往沉迷于揭露痛苦和丑陋的伤疤。
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班主任》、《伤痕》和其后大多数的作品,“四人帮”和传统文化成了伤痕作家群用最强音竭力控诉的标靶,甚至成了一些人在文革中残忍甚至是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的替罪羊和护身符,有了它,昔日里的屠夫也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自己是受害者了。
自我批判就在这样一种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的思维下被一笔带过甚至是略去。
作为伤痕文学的命名之作《伤痕》,今天我们为什么说它无论是在思维的深度还是艺术的表现上都远远不及巴金写在文革后敢于坦率地自我暴露、自我反思的《随想录》,这当然也是作家本身主观因素差异的必然结果。
伤痕文学作家群习惯于寻找外在事物来给人们文革中所受创伤和灾难负责,批判的对象永远是“四人帮”和这个社会,而从来不会是指向自己用以启蒙的知识本身和自己本身。
没有把自己看成是那个“专制金字塔”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批判“四人帮”把自己放到了这个“专制金字塔”之外,仿佛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新视角,可这当中又缺乏现代超越功利性的理性意识,所以对“四人帮”的批判注定是肤浅的,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注定是缺乏理性精神的,不能从根本上去窥视一系列悲剧背后的本质,只能停留于表面,这类现象在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中常常出现。
(二)解读文学作品中缺失的那份自我批判
“伤痕文学”得名于卢新华创作的《伤痕》,《伤痕》这部作品向我们展示了文革千千万万个悲剧中一个比较典型的片段和记忆。
在小说中,虽然就王晓华的伤痕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言行举止发现:
王晓华心中的伤痕是母亲被迫害了,不是叛徒却被“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硬说成是叛徒,蒙受了多年的不白之冤,而且还连累了王晓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甚至连自己和苏小林的爱情也险些夭折。
等到她接到公函得知母亲确实不是叛徒的时候,时间已经不在,母亲已经不在了,想和母亲解释误会的机会都没有了,想见母亲最后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这就是王晓华所认为的伤痕。
这一伤痕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因为她在认定这个伤痕的时候说了一句“亲爱的妈妈,您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
显然这一切悲剧和伤痕在王晓华看来都是“四人帮”戳下的。
可事实并非王晓华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单纯。
在母亲在遭受政治迫害而身心疲惫最需要家的温暖的时候,是王晓华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母亲,离开这个抚养她长大成人的家,就因为害怕自己那“叛徒”母亲连累了自己,让母亲在蒙受不白之冤而陷入悲哀、绝望时又进一步增加了母亲的负疚感和孤独感。
在王晓华把阶级斗争带进家的那刻也是母亲生活真正绝望的开始,因为自己守望、痛爱了十几年的女儿却不能和自己共患难,那怕是一丁点的抚慰。
王晓华的伤痕不仅是文革时代造成的,也是自己造成的。
因为并没有人危及她的生命迫使其离开母亲,而且一走就是好几年,至死不相认。
王晓华母亲的伤痕也不仅是文革时代造成的,同样是王晓华造成的,是她充当了刽子手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扮演了一个伤害母亲心灵的角色,对亲情的背离刺痛了母亲心中最脆弱的神经,那里有着母亲对女儿无限的疼爱和关怀,存放着母亲对女儿的日思夜想和对女儿回归的渴望。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王晓华成了一个让她母亲的不幸更加不幸的加害者,她的决裂和离家出走使她母亲的人生更显悲剧色彩,但是这一些她并不了解,也没有对自身做过任何反思,因为在她看来自己并没有任何过错,自己只是根据党的指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革命牺牲,而万恶的“四人帮”已经为这一切的不幸和伤痕买了单。
作者的控诉和王晓华的悲痛、激愤之情相融合,血泪交加,悲从中来,在最后誓死紧跟华主席,大干党的事业,一种与旧世界势不两立的政治高姿态便是作者对于文革反思后最终得出的有益收获,并没有对自我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反思。
在看到别人手上斑斑血迹而加以控诉的同时并没有回望自己双手也沾了血腥味,这类形象在伤痕文学作品并不少见。
如果说王晓华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不自觉地伤害了自己的母亲,那么在伤痕文学作品中还有另外一类人物形象,他们在自己受到了文革和“四人帮”的伤害后沉沦并最终有意识甚至是理直气壮地去危害其他人。
李克威的《女贼》,通过女主人公黄毛(黄绫)在“四人帮“的摧残和迫害下沦为女贼的过程,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寻求青少年犯罪的根源,说明了作者李克威勇于探索,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动机也是积极向上的。
黄毛作为著名戏曲艺术家黄韵秋的女儿,在母亲受迫害自己也无家可归的时候,选择了自我沉沦,做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庞妈、白天英、孟逵等人组成了专门的偷盗集团,大肆偷盗国家和群众财产,公开享乐挥霍。
虽然我们知道黄毛受迫害做小偷这是在生计无以维持的窘境下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如何这种行为在社会道德层面都是错误和不被允许的,不能因为自己受害就可以去加害别人。
黄毛在公安局长陈一潭以及后来碰到的“恋人”韩蒙蒙的帮助下最终改邪归正,但这些种种背后,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黄毛也就是黄凌对之前自己做女贼时所犯的错误有过任何的反省,甚至在作品后来陈述黄毛改邪归正的过程根本就没提到,只有最后一句“黄毛的眼神里充满了感激,韩蒙蒙在一边笑着向她挥手”便草草地结尾了,对自己做贼的历史没有一个深刻地反省和自我批判。
一个女贼就因为她是受“四人帮”迫害,作者李克威就不再追究她的女贼身份,之前做女贼所犯的错误就因为曾受“四人帮”迫害就被一笔购销了。
自我批判意识在黄毛身上,在作品里消失地无影无踪。
对于做女贼的黄毛,作者甚至采用的是一种崇敬的心态将女贼黄毛塑造成一个侠盗似的人物,不但会骑马、会扒车、会飞檐走壁,而且还有高超偷技。
作者这种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在人物塑造上无疑是有缺陷甚至是有问题的,社会影响也是消极的,没有把黄毛经历的这种家庭苦难放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思考,对于黄毛做女贼是同情甚至是纵容的,认为黄毛做女贼是理所当然的。
这种对人和社会道德之间关系认识的偏差本身是不可取的,作者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在这部具体作品中的主人公黄毛身上体现着淋漓尽致。
整体而言,以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作家群只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做了必要的发言,在文学领域配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关于“政治思想解放”的呼声一道完成了对“文革”政治的代名词“四人帮”的批判,在狭隘的视角下,我们看不到现代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性的思考,看不到自我的反思和批判。
三、轰动背后的现实效应
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表现方式,根据文艺理论我们知道,文学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产物,其本身要有一个文学创作过程。
伤痕文学引起巨大轰动的作品往往是没有区别于现实世界,而是依附于现实经验,是现实世界的一个典型的摹本和反映,而不是文学创作。
[8]
伤痕文学的初期引起极大反响的卢新华的作品《伤痕》,在作品中很多经历都是来源了作者卢新华在文革期间,自己认定母亲是坏人,直至母亲去世都不理他的真实回忆,并最终以这个灵感素材写成了小说。
在这里卢新华把自己个人的现实经验和经历当作了创作本身,所以作品的文学性就显得贫弱,更而像一个现实故事的稍加文学处理后再现。
作品本身缺乏足够的文学内涵,缺少我们可以去深挖的内在美,读者在文中看到的只是王晓华和她母亲在文革中是如何遭到迫害而“伤痕”累累,在控诉“四人帮”的同时又不忘讴歌一番新时代,它不像陈忠实的《白鹿原》那样能给读者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极具个性的精神世界,《白鹿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白鹿原世界”,我们在这里能去深入的窥视生活其中的白嘉轩和鹿子林这两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并得出读者自己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悟。
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在现实材料的基础,把生活艺术化了,再造出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陈忠实显然没有在自己作品描绘的年代生活过,但是他用自己独特的想象力为我们编织了一个“白鹿原”,当然也是在一些现实材料的基础上,传达了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所以我们说它是优秀的作品,而《伤痕》不是。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伤痕》的历史会发现它在中国社会和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本科 毕业设计 论文 伤痕文学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2机组现场施工用电布置措施.docx
#2机组现场施工用电布置措施.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