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娘家与婆家书评.docx
娘家与婆家书评.docx
- 文档编号:26135565
- 上传时间:2023-06-17
- 格式:DOCX
- 页数:21
- 大小:51.52KB
娘家与婆家书评.docx
《娘家与婆家书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娘家与婆家书评.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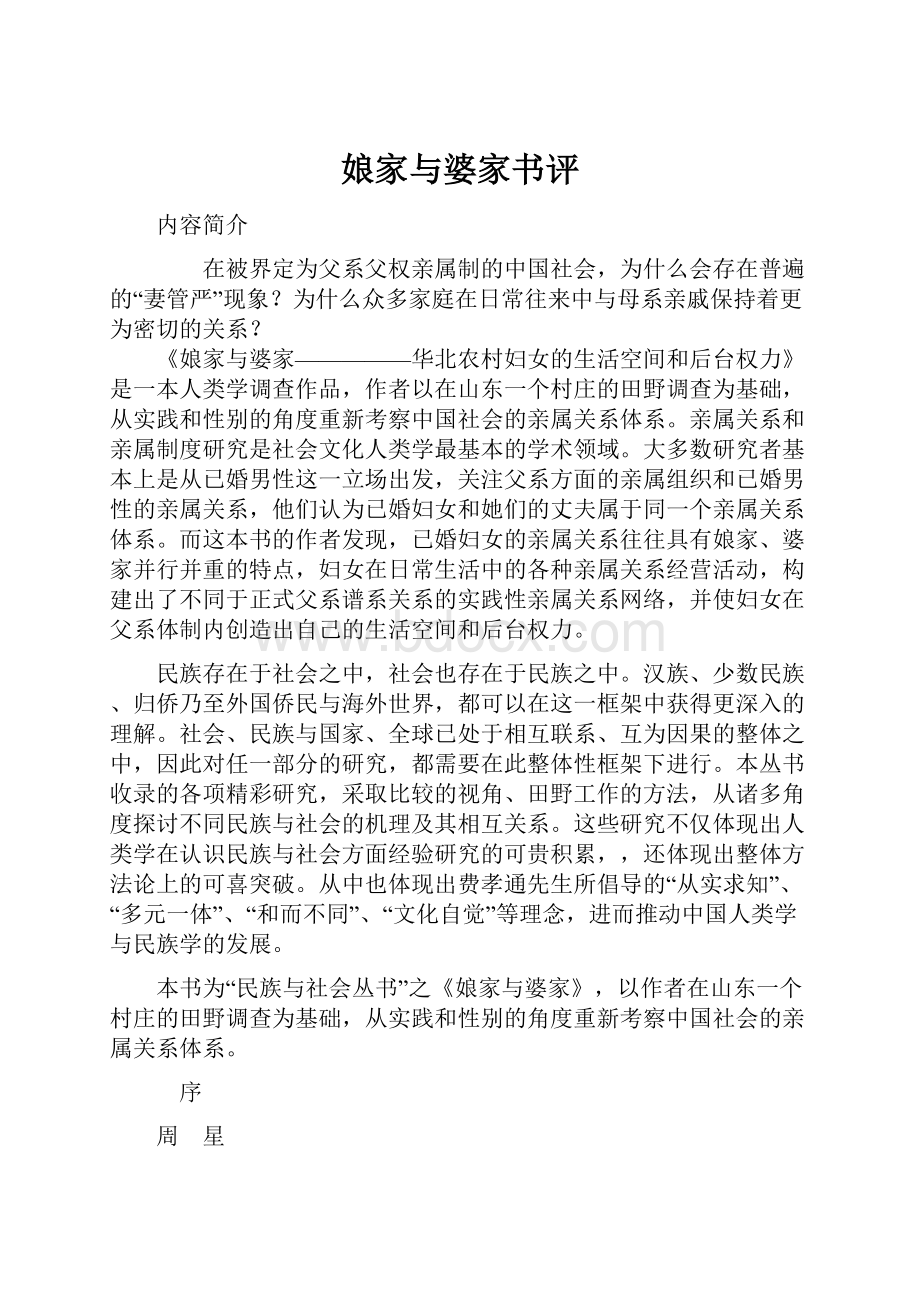
娘家与婆家书评
内容简介
在被界定为父系父权亲属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存在普遍的“妻管严”现象?
为什么众多家庭在日常往来中与母系亲戚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是一本人类学调查作品,作者以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
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学术领域。
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是从已婚男性这一立场出发,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
而这本书的作者发现,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往往具有娘家、婆家并行并重的特点,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
民族存在于社会之中,社会也存在于民族之中。
汉族、少数民族、归侨乃至外国侨民与海外世界,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中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社会、民族与国家、全球已处于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整体之中,因此对任一部分的研究,都需要在此整体性框架下进行。
本丛书收录的各项精彩研究,采取比较的视角、田野工作的方法,从诸多角度探讨不同民族与社会的机理及其相互关系。
这些研究不仅体现出人类学在认识民族与社会方面经验研究的可贵积累,,还体现出整体方法论上的可喜突破。
从中也体现出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从实求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文化自觉”等理念,进而推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
本书为“民族与社会丛书”之《娘家与婆家》,以作者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和性别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体系。
序
周 星
我非常高兴地为这部专著写序。
李霞博士通过在当代中国华北一个汉人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该村落妇女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学术思考,运用“娘家—婆家”这一分析框架,深入和细腻地论述了农村妇女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
本书突出地强调了女性的视角、实践的观点和情感的线索,无论是在生活细节的描述上,还是在理论层面的分析上,都充溢着人类学的智慧、创意和真知灼见。
我以为,这部人类学专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作为一部“女性民族志”作品,本书对有关汉人社会的女性人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众所周知,有关中国汉人社会及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大都是由男性人类学者,主要以男性为调查和访谈对象,集中围绕各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例如,宗族)等而展开。
此类研究所产生的民族志作品自然反映了男性的视角,在它们所描述的对象社区的社会生活里,往往也是“理所当然”地忽视了妇女的存在或没有给她们以应有的份额与位置,很难避免所谓的“男性意识偏见”。
鉴于截至目前有关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有深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依然非常稀少,李霞这部具备了规范的田野工作之科学基础的“女性民族志”作品,也就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女性人类学者在她们的田野工作中经常可能由于不同的视角和体验而有与“主流”的男性人类学者不同的课题意识、调查心得、生活感受和田野发现。
例如,美国人类学者玛格瑞·沃尔夫根据她在台湾的田野调查,把妇女视为能动的个体来考察,正确地指出了汉族妇女是在父系宗族制度的框架之下致力于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汉人已婚妇女和“她的家庭”,乃是基于安全感和情感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子宫家庭”(或译“女人家庭”)。
另一位美国人类学者朱爱岚,非常关注已婚女性和娘家之间的关系,她对“娘家”的论述,较多地是从正式制度与具体实践之间的所谓“惯习”的层面去分析,指出妇女自身在她和娘家的关系中具有积极的能动性。
日本人类学者植野弘子对汉人社会里的姻亲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她批评以往的宗族研究和姻亲研究,均是以“单向性”和男性中心为前提;基于对台湾南部汉人姻亲关系的实地调查,她指出在娘家(所谓“生家”)与婆家(所谓“婚家”)的关系中,其实还包括了女婿和岳父的关系、甥舅关系、“母舅”的作用、娘家作为“后头厝”的意义等。
现在,读者眼前这部由中国人类学者撰写的女性民族志,其中对汉人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对农村妇女喜怒哀乐的人生有许多独到的观察和描述。
在我看来,李霞的著述不仅在上述女性人类学者之汉人社会研究的脉络或其“延长线”上取得了更具综合性的进展与收获,它还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此前对于汉人乡村社会的认知,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也将有助于纠正以往人类学的汉人社区研究中所隐含着的男性中心偏差,照亮这些偏差所遮蔽的误区。
其次,作者在她深入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娘家—婆家”这一妇女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从而对有关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
在我看来,这一“发现”确实具有某种颠覆性,它对于截至目前的汉人社会之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的研究具有某种革命性的意义,并为我们提供了涉及婚姻、家庭、宗族、分家等在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颇具重要性的那些基本社会事实的许多全新的知识。
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始终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最为基本的学术领域。
有关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及亲属制度研究,长期以来虽然已有不少的积累,但无论是对汉人亲属称谓体系的研究,还是对宗族组织这种父系继嗣群或是对宗亲关系的研究,甚至包括不少姻亲关系研究,绝大多数研究中设定的“己身”(ego)均是已婚男性。
研究者基本上均是从这一立场出发,主要关注父系方面的亲属组织和已婚男性的亲属关系,他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已婚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属于同一个亲属关系体系。
中国人类学者冯汉骥曾经指出:
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网络通常是宗亲在观念上比非宗亲(外亲)更为重要;和宗亲相比较,姻亲称谓及其亲属关系也较为简略、单纯;与妻子到丈夫家需要适应的夫族亲属称谓相比较,丈夫需要了解的妻族亲属称谓则比较少。
虽然在汉语的民间称谓里有比较系统的“夫系亲属称谓”和“妻系亲属称谓”,夫妇双方原则上应该分别对对方的亲属关系予以接纳,但在汉人社会的男娶女嫁、婚后从夫居的婚姻制度和父系继嗣的宗族制度之下,此种相互接纳并不对等。
在父系制度的安排下,妇女在整个社会的亲属称谓体系和亲属制度中具有从属性的身份地位。
以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宗族范式”的汉人社会研究,重视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世系群(宗族)及其作为社会组织的机制、功能、结构及仪式的研究,很自然地认为妇女处于父系亲属关系的边缘,其身份具有两重性,而且最终也要被同化进父系亲属制度之内。
在上述两类研究中,妇女均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关注对象,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妇女独特的亲属关系网络和亲属关系实践等,往往不是被屏蔽,就是被视而不见,其中或明或暗地总是存在着某些对妇女的轻视。
现在,我们看到,李霞在她的著作中以全新的视野和思路,富有创新性地把女性人类学的性别研究视角引入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研究,颠覆性地把当事人或“己身”替换为女性来重新审视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及亲属制度,并因此有了新的发现:
以女性为中心的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以及妇女自身积极进取的亲属关系实践。
李霞发现的妇女亲属关系,可以用“娘家—婆家”这一对范畴来概括,也就是说,已婚妇女所处的或她所建构的妇女亲属关系,往往具有娘家、婆家并行并重的特点。
“娘家—婆家”及其背后的两类亲属关系范畴,主要是以已婚妇女的主位立场为依据的。
她婚前完全生活在“娘家”的亲属关系(通常,也是一个父系亲属体系)体系之内并享有亲情,以结婚为转折,她又必须逐渐适应另一个不同的亦即以丈夫为核心的“婆家”的父系亲属关系体系。
于是,身为当事人的已婚妇女,其妇女亲属关系基本上就是以“娘家—婆家”为框架,左右逢源,进而拓展出使她自己得以经营核心小家庭的生活空间。
从妇女生活的立场看,她们体验的亲属关系并不完全是父系的,其中她们和娘家的关系以及她们从娘家获得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李霞的研究表明,在汉人社会里,妇女潜心经营的小家庭固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宗族、父系家族或其世系谱牒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是在丈夫的祖先和子孙之间形成继嗣连锁(传宗接代)的环节之一。
就此而论,它正是父系宗族继嗣和父系亲属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的机制。
但在已婚妇女自身看来,她和丈夫一起经营的小家庭却不是宗族或大家族的简单复制,而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属性。
第三,李霞进一步通过在她的研究中引进“实践”的视角,从而对中国汉人社会里妇女的亲属关系实践及与之相关的亲属关系建构活动做出了精彩的说明。
汉人社会里妇女的亲属关系实践是以女性自身为主体,以女性自身的人生为主轴,在其所有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展开,并且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的。
正如李霞指出的那样,妇女亲属关系的实践目标及其人生历程,并不是以父系继嗣意义的家族或家族集团(宗族)为指向,而是以她自己的小家庭为指向。
根据李霞发现的“娘家—婆家”这一妇女亲属关系的结构框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妇女在制度性的父系亲属关系结构里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在其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建构出了她自身的妇女亲属关系。
较早时期的人类学,经常忽视个人在文化或社群团体生活中也是具有能动性的,有意无意地总是把人们理解为只是单方面地被“社会化”、“文化化”,或只能遵从民俗、传统惯例或刚性的制度而生活着。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发生了转向,亦即在文化体系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作为实践者与行为者的重要性逐渐引起了关注。
法国人类学者皮埃尔·布迪厄针对结构主义人类学过于强调规则和结构而多少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倾向,提出了“实践”理论,从而为人类学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受此种全新的人类学取向的启发,李霞也是从实践的视角出发,将乡村社区里的已婚妇女视为是她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具有能动性的实践者与行为者,视她们为实践着的个人,从而把以往总是被理解为铁板一块的父系亲属制度,重新解释为其中实际上是在持续不断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实践,尤其是妇女的亲属关系实践。
李霞的此项研究较好地说明了文化体系与个人、社会结构与不断从事着实践活动的当事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她的描述中,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并不是一个铁定、僵硬不变和自古而然的传统,而是由当事人在其中时常创新、反复不断地进行着“解构”与“建构”之类实践活动的体系。
已婚女性究竟是如何在“娘家—婆家”的关系结构中构筑起自己的核心家庭,经营自己的亲属网络、社会关系,乃至实现人生意义的?
阅读李霞博士的论述,就会对这些问题有豁然开窍的感触。
概括说来,已婚妇女在其旨在经营核心小家庭的亲属关系实践中经常可能采取的“策略”,就是借助娘家的“外势”,在“娘家—婆家”之间游刃有余。
此类实践的目标,基本上是以“分家”和经营核心小家庭为指向,逐渐脱离由公婆权威所代表的大家族。
这样,她很自然就会刻意地(往往也是一时地)抵制、躲避、淡化婆家亦即大家族的亲属关系,诸如通过分家尽力促使丈夫和他的“近门子”疏远等;与此同时,妇女的亲属关系实践还有更加进取的方面,亦即对娘家方面的关系积极地予以利用,极力把丈夫卷入和娘家的密切互动之中,或自行和“街坊”交往以搭建和维护自己的社交环境等。
外来媳妇试图在丈夫的家族或宗族之内逐渐建构以自己为核心的独立小家庭,此类实践活动构成了中国农村已婚妇女的人生目标。
如此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不少人类学者曾经指出,外来媳妇对于宗族或家族来说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李霞揭示了已婚妇女是如何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亲属制度的体系内部,以建构核心小家庭为奋斗目标而实践性地发展出了女性自己的亲属关系空间的。
可以说,“分家”的机制主要就是来自媳妇的利益诉求和压力,那种把婆媳矛盾或妯娌冲突只看做兄弟之间冲突的“媒介”,认为男人之间的冲突才更具实质性的意见,似乎低估了妇女通过可控的冲突达致分家的主观能动性。
虽然分家有可能带来某些后遗症,但这些后遗症随后大都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弭。
分家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媳妇可以完全脱离丈夫家族的亲属关系,而是说她为自己建构了一个空间,从而可以在其生活实践中对丈夫家族的亲属关系根据各种具体的场景予以筛选、取舍、妥协和利用。
事实上,妇女营建自身的亲属关系和她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实践,并不绝对排斥丈夫家族及其“近门子”,通常她是会理性地将其也纳入经过自己选择的亲属关系之内。
但妇女的生活实践还有另一层面,亦即着意在“近门子”之外发展出一些具有个人人际关系之属性的“街坊”。
总之,以自我为中心,“娘家—婆家”两边都认,才在现实生活里最为实惠。
如此这般,妇女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个看起来颇为严格的父系亲属制度的框架内,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和策略,最终建构起自己的亲属关系来。
中国乡土社会里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属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因人而异的,已婚妇女的亲属关系实践,也基本上是个人层面的努力。
妇女个人的奋斗需要娘家做后盾,把丈夫发展为同盟,把子女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在“娘家—婆家”的关系结构中成功地搭建起令她自身感到惬意和舒展的妇女亲属关系。
李霞通过对村妇们此种亲属关系及其实践的细腻描述,说明了妇女具有和其丈夫不尽相同的家庭观和亲属观。
丈夫可以拥有独立的小家,却不能完全脱离宗族的连带关系,也不能完全摆脱对大家族的责任(宗族、家族的共同祭祀和赡养父母等);对于妻子而言,分家使得她“自己的家”从“老婆婆的家”独立出来,她可以更加方便地通过走亲戚、年节互访、大事互助及经济协作等方式,依托娘家的支持来提高或巩固自己在小家庭内的主导地位。
丈夫和妻子各自对亲属关系、对“家”人的理解并不完全重合,这意味着以男性为中心的亲属体系并不能够完全为丈夫和妻子所共享,即便在形式(礼制和仪式)上有此可能,但在彼此的厚薄、亲疏、远近和用情的深浅等方面却有着太多的差别。
在李霞研究的这个同姓宗族(大家族)的村落社区里,人们把亲属关系明确地区分为“家族”(五服之内)和“亲戚”(主要通过联姻确立)。
家族成员彼此总会有一些超越各家户的较为正式的仪式(拜年磕头、婚丧礼仪的互助等),亲戚则主要靠“走动”来维系。
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走亲戚”非常频繁,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社区和家族的那些仪式。
家族仪式和颇有一些儒教意味的社区规范,主要涉及辈分(孝敬)、继嗣、家族或宗族成员的亲疏远近(五服和差序格局)以及社会性别等,而日常生活的实际运行、“过日子”,更多的则是走亲戚和“为”亲戚,“走”和“为”都是非常具体的实践活动。
对丈夫而言,家族或社区的仪式及规范往往是家族重于亲戚的,但对媳妇的实际生活而言则未必如此。
媳妇根据需求建构自己的关系网络,也因此而另有一套远近亲疏的亲属关系序列。
父系亲属制度的结构依然有效,但妇女的生活实践所指向的妇女亲属关系其实更具有现实性。
由于妇女的积极实践有可能导致产生一种比起父系偏重来稍微对等一些的亲属关系结构,因此,我们说她们并非父系制度的依附者,而是自身生活空间及亲属关系的建构者。
第四,李霞的村落妇女研究,其对基于情感、以情感为导向和归宿的女性亲属关系实践——包括妇女对“子宫家庭”的追求、对娘家的眷恋等——的重视和描述,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状态的理解,这一点也堪称本书的重要特征和贡献。
妇女的亲属关系实践,并不单纯地只是基于理性的判断或功利性的利害而展开,它同时也是基于人类情感的颇为自然的需求。
以往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较多地专注于制度层面,而不大关注情感问题。
事实上很多学术著述均有轻视人类情感的倾向,大多倾向于把当事人描述为一切行为都是基于理性、权利和义务等的“经济人”或“法权人”。
李霞这部著作从时间的基轴考察了妇女亲属关系的感情层面,并对此有生动的概括。
嫁娶婚和从夫居使得汉人社会的妇女一般都以结婚为契机而必须经历生活空间、身体、劳动以及集团归属的转移或转换。
妇女经营小家庭和建构个人亲属关系的实践活动,往往伴随着女性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而不断地有所调整,她们总是尽力去维系、追求、发展和巩固自己经营的个人亲属关系网络,并尤其重视和娘家的情感。
情感是家庭和妇女亲属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及动力之一,妇女也是家庭及亲属情感最主要的维系者。
但妇女的人生及情感归宿,通常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一个由亲近“娘家”逐渐转向于认同“本宗”(夫家、婆家)的“移情”过程。
在她的“子宫家庭”建立的初期,娘家亲戚就是最天然的关系资源与情感依托;而“子为母之党”,妇女经常携孩子回娘家(对于孩子而言,则是“外家”),并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影响子女一个较长时段的情感取向;不过,伴随着子女的成长,他们自然会有情感的“转向”,逐渐会对“本宗”和“外家”形成新的认知和认同,母亲对子女的此类本宗情感终归是必须予以承认的。
与此同时,伴随着子女的出生和成长,往往就是通过“从儿称”的方式,她在夫家亲属体系,进而在宗社之内和村邻之间均可获得稳固的身份;当她因为儿子结婚而熬成为“婆婆”或因为闺女出嫁成为女儿牵挂的“娘家妈”时,已婚妇女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就会逐渐而又明确地发生转变。
她的身份除了“婆婆”、“娘家妈”之外,还有“岳母”甚至“祖母”和“外婆”等,她的情感也会逐渐地“归”宿于自己以前多少有所忌避的“婆家”。
但此时,公婆多半已经过世,她因为母亲和祖母的身份而不会再有多少困扰。
促使她逐渐淡化对“娘家”的情感和归属感以及缓慢地“移情”夫家本宗的原因,经常还有来自“娘家”也必然发生的各种变化,诸如娘家父母的过世、娘家兄弟的结婚和分家、娘家兄弟媳妇的“他人化”态度等。
但终其一生,妇女大都保持着有关娘家深厚的情感记忆。
妇女和娘家之间的情感纽带,不仅表现为出嫁女子对娘家的眷顾,更有娘家对出嫁女子的牵挂。
中国各地民俗里有很多涉及出嫁女儿“回娘家”的乡土传统,诸如在婚礼过后的“回门”,春节大年初二的回娘家拜年,每逢年节岁时接出嫁女儿回娘家的习俗等,可知各地的乡俗普遍地均有此类顾及女性情感的设计。
女子出嫁前在娘家生活所培养的感情,自然会延续到婚后很多年。
由于不能马上适应婆家的生活,出嫁女儿往往需要时不时地回娘家休养,或频繁地在婆家和娘家之间来回走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形成双栖轮住的生活方式。
老北京旧时的农历“二月二”,各种民俗活动中有一项就是接出嫁的“姑奶奶”回娘家。
民谣俗语云:
“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说的就是娘家亲人对出嫁女子的牵挂。
与在宗法礼制及仪式等层面多少被婆家有所束缚形成对照的是,乡间民俗却同时安排了让已婚妇女回娘家的各种惯例,从而使出嫁女子的情感得以舒展,以帮助她们平衡或缓解来自婆家及父系亲属制度的压抑。
此外,像大年初二,携丈夫、孩子给娘家父母拜年;清明节,女儿给娘家祖先送纸祭祖;中秋节,女儿给娘家送月饼等乡土社会的走亲戚和礼物馈赠活动,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儿女亲家”之间。
所有这些馈赠和相互走动,均深切体现了娘家和出嫁女儿之间的互相牵挂与惦念;而且,也正是为了使“儿女亲家”之间的此类互动得以随时进行及持久存续,中国各地农村的“通婚圈”基本上都以当日可以往返的距离为半径,这可以说是乡土地域社会得以成立的基础之一。
最后,我觉得还有必要特别指出,“娘家—婆家”这一对范畴有着非常丰富的妇女亲属关系之实践的内涵,不应该被简单地归结为“男方”和“女方”或嫁女的一方(Wifegivers)和娶妻的一方(Wifetakers)。
严格说来,它应该是在新娘子—小媳妇成为亲属关系中的当事人(ego)之后才得以成立。
这一组在民众日常生活中颇有涵盖力的“民俗用语”,经过本书这样的“发现”和阐释,完全有可能脱颖而出地成为能够被用来说明或揭示中国民众社会生活某些重要侧面的学术性概念。
中国南北各地民间有不少对“娘家”和“婆家”的方言称谓,诸如西南官话里的“娘屋人”(成都)、“娘屋头”(成都)、“娘屋里”(武汉),福建方言里的“娘老厝”(福建光泽)、“后头厝”(台湾南部),河南方言里的“婆子家”等。
如果说这些都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俗语汇,那么,李霞所提示的“娘家—婆家”这一对完全可以超越地域性的范畴,就应该和“人情”、“关系”、“面子”、“生熟”、“阴阳”等概念一样,而能够成为今后我们理解汉人社会时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学术用语。
“娘家—婆家”这一对范畴,在几乎所有中国妇女看来,均是理所当然和心领神会的;同时对于她们而言,这也是最普遍、最根本、最有概括性和最富有内涵的妇女亲属关系的称谓及分类。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它熟视无睹的局面,只是在女性视角被李霞导入她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之后才被突破,这确乎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李霞对“娘家—婆家”的研究,或者说她通过运用“娘家—婆家”这一分析框架对妇女亲属关系及其实践活动之人生意义的探讨,乃是很重要的学术贡献。
在看似平淡琐事描述的背后,李霞实际上成功地揭示了汉人社会生活里最具有常识性的一部分结构与事实,并由此解释了很多与之相关,虽然寻常可见却也不乏重要性的社会文化事象,例如,为什么在中国各地的民俗语汇中往往会有大量强调母方亲属(或外家)之重要性的熟语、谣谚?
为何在中国各类民间口承文学中,经常会表现出婆媳矛盾、姑嫂矛盾、分家纠纷之类的题材?
等等。
虽然中国现已延续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导致城市里出现了大面积的独生子女家庭,进而也使男性中心的娶嫁婚及从夫居的生活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妇女感受到来自婆媳纠葛的压力小多了,但即便如此,“娘家—婆家”的基本生活图式依然没有失效,独生子女夫妻之所以年复一年地会有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过年、吃团圆饭的困扰,似乎正好可以说明“娘家—婆家”的妇女亲属关系逻辑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我认识李霞,是在1998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俗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后来,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社会人类学专业的博士课程。
李霞的博士学位论文,从讨论题目到确定研究思路,再到田野调查和具体的写作,我都有机会和她经常地讨论、切磋,真可谓教学相长,这同时促使我也逐渐地开始思考一些和她的这一研究课题有关的学术问题。
李霞对学术研究非常认真、严谨和执著,她的博士论文在2002年6月1日答辩时获得了人类学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自那以来,她把博士论文改了又改,一晃八年过去了。
今天,这部专著终于得以出版,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相信,这部读来令人感到亲切、温暖而又聪慧的著作,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及广大读者的认可和欣赏。
1.摘要:
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的重要话题,但是要进行研究却非易事。
由李霞博士撰写的《娘家与婆家:
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以女性人类学家独特的细腻视角,通过长期、扎实的田野调查,以详实、丰富的民族志资料,挖掘出中国家庭关系中典型的“娘家—婆家”模式。
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的重要话题,但是要进行研究却非易事。
由李霞博士撰写的《娘家与婆家:
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以女性人类学家独特的细腻视角,通过长期、扎实的田野调查,以详实、丰富的民族志资料,挖掘出中国家庭关系中典型的“娘家—婆家”模式。
这种娘家与婆家的文化现象,在人类学上称之为“从夫居”PatrilocalResi-dence制度,指的是女性结婚之后多数时间与丈夫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由于从夫居的父权机制,导致了女性婚前婚后的角色变化,以及她们和娘家与婆家的远近亲疏,这才有了娘家与婆家之别。
人类学家已经通过民族志调查证实了在全球69%的文化中存在这种现象。
从夫居文化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中国,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独有的“伦理之道”,使“娘家与婆家”的分野成为中国本土“从夫居”文化的典型特征。
李霞博士的这本著作,正是从这一典型特征切入了中国“人伦”文化的精要之处。
关于中国家庭关系的研究汗牛充栋,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对这一领域有深入探讨。
以人类学为例,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农村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马格丽·伍尔夫的《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和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等都是研究中国农村的妇女、婚姻和家庭的民族志经典。
对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角色,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阎云翔强调的是随着“集体制解体”的社会变革,农民家庭及亲密关系的改变;伍尔夫则着重于亲子关系的深描,其“子宫家庭”的概念,深刻揭示了父权制家庭中,母亲通过对子嗣的情感控制,集合各方资源,争取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朱爱岚重点考察的是女性在家户与国家双重领域中的角色及其性别权力关系。
这些研究,往往将女性角色置于“婆家”的社会空间范畴之内进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娘家 婆家 书评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爱和自由》读书心得15篇.docx
《爱和自由》读书心得15篇.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