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文化论文看山看水有感.docx
语言文化论文看山看水有感.docx
- 文档编号:23033001
- 上传时间:2023-04-30
- 格式:DOCX
- 页数:8
- 大小:24.16KB
语言文化论文看山看水有感.docx
《语言文化论文看山看水有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语言文化论文看山看水有感.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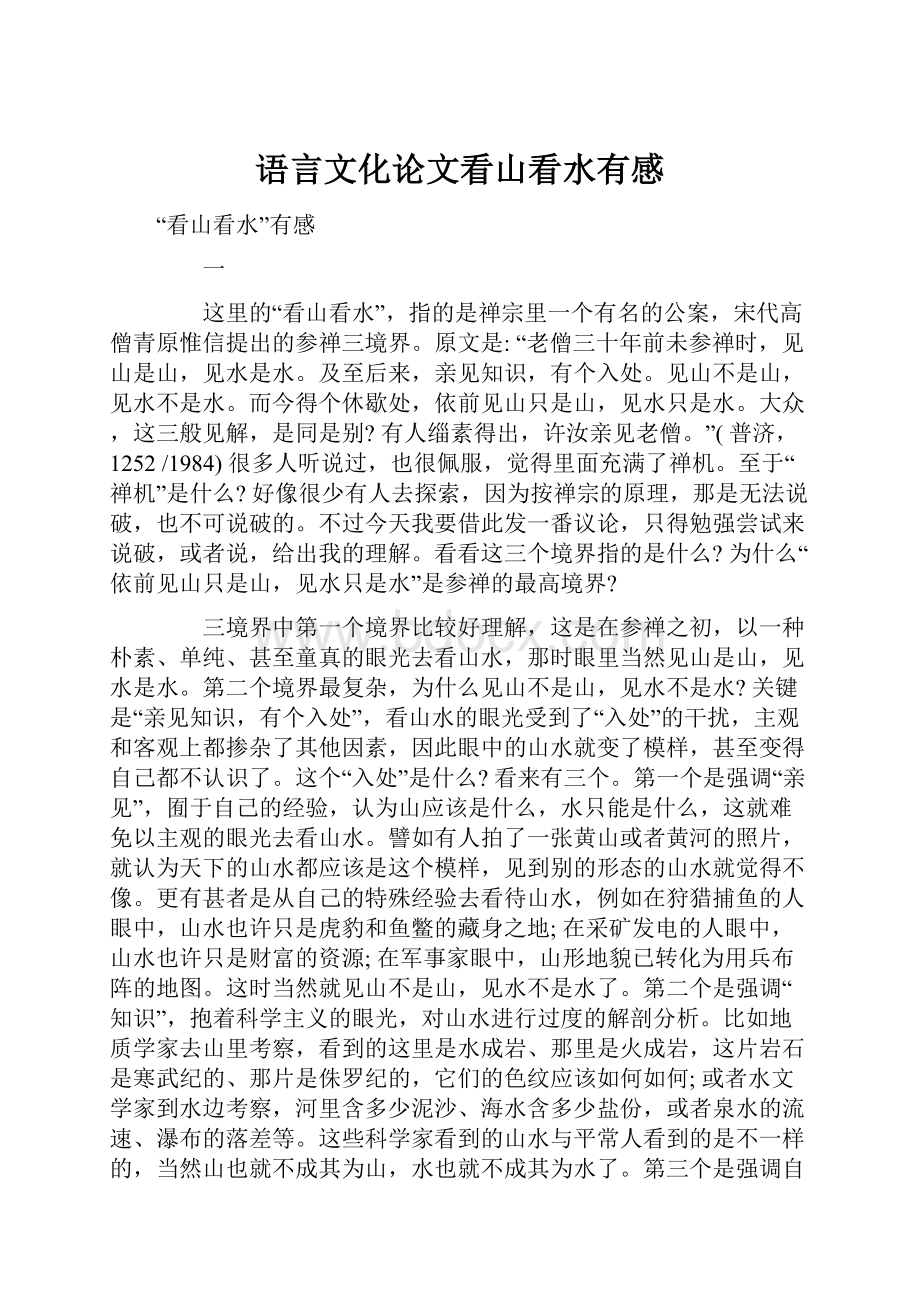
语言文化论文看山看水有感
“看山看水”有感
一
这里的“看山看水”,指的是禅宗里一个有名的公案,宋代高僧青原惟信提出的参禅三境界。
原文是: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
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
”(普济,1252/1984)很多人听说过,也很佩服,觉得里面充满了禅机。
至于“禅机”是什么?
好像很少有人去探索,因为按禅宗的原理,那是无法说破,也不可说破的。
不过今天我要借此发一番议论,只得勉强尝试来说破,或者说,给出我的理解。
看看这三个境界指的是什么?
为什么“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是参禅的最高境界?
三境界中第一个境界比较好理解,这是在参禅之初,以一种朴素、单纯、甚至童真的眼光去看山水,那时眼里当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第二个境界最复杂,为什么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关键是“亲见知识,有个入处”,看山水的眼光受到了“入处”的干扰,主观和客观上都掺杂了其他因素,因此眼中的山水就变了模样,甚至变得自己都不认识了。
这个“入处”是什么?
看来有三个。
第一个是强调“亲见”,囿于自己的经验,认为山应该是什么,水只能是什么,这就难免以主观的眼光去看山水。
譬如有人拍了一张黄山或者黄河的照片,就认为天下的山水都应该是这个模样,见到别的形态的山水就觉得不像。
更有甚者是从自己的特殊经验去看待山水,例如在狩猎捕鱼的人眼中,山水也许只是虎豹和鱼鳖的藏身之地;在采矿发电的人眼中,山水也许只是财富的资源;在军事家眼中,山形地貌已转化为用兵布阵的地图。
这时当然就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了。
第二个是强调“知识”,抱着科学主义的眼光,对山水进行过度的解剖分析。
比如地质学家去山里考察,看到的这里是水成岩、那里是火成岩,这片岩石是寒武纪的、那片是侏罗纪的,它们的色纹应该如何如何;或者水文学家到水边考察,河里含多少泥沙、海水含多少盐份,或者泉水的流速、瀑布的落差等。
这些科学家看到的山水与平常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当然山也就不成其为山,水也就不成其为水了。
第三个是强调自己的“亲见、知识”,因而只有自己的“入处”才是正确的,一条道走到底。
就如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有人强调是“岭”,有人强调是“峰”,这就反而看不清山水的真面目了。
这三种情况,比起第一个境界时完全没有“入处”,也就是没有进行观察当然是一个进步,因此可说是有了初步的“悟道”,但是,一个囿于主观上的经验,一个囿于客观上的过度理性,一个囿于方法上的片面固执,反而造成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后果。
从禅宗来看,造成这些窒碍的“入处”既是进步,又是束缚,只有把它们彻底“放下”,才可以进入第三个境界,回到“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自然境界。
然而,这时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已不是第一境界的简单重复,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只”字,说明经过了第二境界的历练,“山、水”的本貌比第一境界要丰富得多了,因而心也“得个休歇处”了。
因此这三个境界如果要用现代的话语加以表述的话,我认为不妨称之为“经验性”、“理性”和“智慧性”,进入到智慧性,也就“悟禅”或者“得道”了。
这里讲的是参禅,其实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规律,其他哲学家也有过类似的表述。
例如黑格尔讲的“正-反-合”的辩证思维过程就与此有些相似。
但黑格尔强调第二阶段“反”是对第一阶段“正”的否定,而第三阶段“合”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观察就有点绝对化的味道。
因为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禅家第二阶段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只是第一阶段认识的深化,未必是对其的否定。
毛泽东的“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论规律与之更接近,他强调第三阶段的“实践”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实践,而不是第一阶段的简单重复。
但毛认为“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是个无穷的过程。
因此我们这里还是采用禅宗的说法。
既然“看山看水”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根本规律,我们就可用它来观察其他事物和现象,例如翻译。
在翻译问题上,我们是否也会经历“看翻译是翻译-看翻译不是翻译-看翻译还是翻译”这样三种境界呢?
我认为是的。
二
中外的翻译都有了两千年的实践,也都有了几百年的理论探索,最近这三四十年对理论的探索尤其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深入,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到了对翻译认识的第三个境界。
如果说翻译产生初期,我们有过“看翻译是翻译”的朦胧童稚阶段,那么由于上面分析“亲见知识,有个入处”的同样的三个原因,直至今天,我们可能还停留在“看翻译不是翻译”的第二阶段。
下面试加以讨论。
(一)囿于亲见主观认定
翻译的发生是因官方或民间出自政治或经济交流的需要,《史记》记载汉武帝时开拓丝绸之路的功臣张骞,在提到西方的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康居等大国的时候说:
“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徳遍于四海。
”(司马迁,1982:
3166)可见当时人们看重的是对翻译的实际需要和能否完成任务。
哪怕要经过“重九译”,但只要达到“致殊俗,威徳遍于四海”的效果就可以了,翻译就是翻译,没有人关注“什么是翻译”这样的理论问题。
这是“见翻译是翻译”的第一境界。
但一旦开始对翻译进行理论研究,主观性就难以避免地出现,因而也就不可阻挡地进入了第二境界。
很久以来,我们有着一个几乎一致的认识,即认为中外翻译史上都有着一个以“忠实”为核心内容的传统,认为这既是翻译研究的客观性,也是翻译研究的共性。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事实并非如此。
对翻译的理性探讨,不论中西,都是从宗教翻译开始的,这时,不同宗教的语言观和翻译观就会产生和形成不同的翻译研究传统。
在西方,这确实是一个以“信”也就是“忠实”为核心的传统,而在中国却不是,而是一个以“达”乃至“达旨”为核心的传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
因为西方的宗教翻译以基督教传播为主要任务。
基督教传播有三个特点,一是《圣经》有确定的文本,开始是希伯莱文本,后来是希腊文文本和拉丁文文本,二是基督教传播大抵是从文明高的民族传向文明相对落后的民族。
三是《圣经》的翻译者大多兼通两种甚至多种语言。
《圣经》传达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当然不容许有任何篡改,这就形成了西方翻译研究原文至高无上的传统,以及“信”或“忠实”是翻译最基本的原则。
而中国的翻译研究起始于佛经翻译,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有三个特点。
一是佛教没有确定的文本,由于原始佛教采取除不许用梵文外,“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这样放任的语言政策(季羡林,1957:
69),因而到中国来传教的僧人可以各用其自身家乡语言讲经。
二是佛经传到中国时,中国已是一个文明早已开化的国家,有成熟的思想文化如儒道及诸子百家等,佛教的传播不能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如入无人之境”。
三是佛经的翻译者双语不熟练,西域僧人精通西域语而中文不足,中国助手多数不通西域语。
由此而形成佛经翻译研究以“达”为主要宗旨。
“文质之争”本质上是个如何更好地“达”的问题。
中西译论重“信”重“达”的不同传统与各自的文化传统互为表里(说“互为表里”,因为很难说清是翻译造成了中西不同的文化还是中西不同的文化影响了其翻译观)。
西方重“信”的翻译传统造成了西方aggressive的文化传统,也许可叫做“征服文化”。
《圣经》翻译走的语言路线图是希伯莱文-希腊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徳文等-世界各国语言。
在这条路线图中处于中游的语言文化对排在其前面的都有一种莫名的尊崇,而对排在其后面的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极度自负的优越感。
以英语为例,在历史上,英语对拉丁语乃至法语总有点自惭形秽,包括连英语语法都是拉丁文文法的翻版。
而在英语通过翻译走向世界时,英语和英语文化在世界其他民族前就有一种咄咄逼人的优越感,不仅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甚至包括语言本身。
其势甚至逼得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抬不起头来。
中国二十世纪初白话文运动的动因之一就是因为觉得文言文不能用来“忠实地”翻译现代也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文明。
有人觉得翻译以“忠实”为第一义是天经地义的,其实这只是西方的翻译传统。
我们循着上面的路线图一看就明白,顺着看是行得通的,例如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其他文字等,我们都会觉得“忠实”是天经地义的。
但如果逆向呢?
恐怕就行不通了:
从中文译成英文有多少人会强调“忠实”?
即使中国自己的翻译家,有强调中译英时必须不折不扣地忠于原文的吗?
中式英文Chinglish是要被嘲弄的,而英式中文、所谓的翻译腔,从傅斯年教人“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傅斯年,1918:
223)起,就一直不乏有鼓吹之人。
可见,以“信”为主题的西方译学传统,其实已经不是翻译策略,而是一种文化战略了。
那么中国以“达”为核心的译学传统呢?
看来也同样不仅仅是翻译策略,而与文化息息相关。
从策略上说,“达”是只问结果,不重过程,更不重原文的,为达目的,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因此中国历史上,“翻译”一词的含义比西方要广得多,翻译和“翻译家”的范围也要大得多,包括许许多多根本不懂原文的人。
而以“达”为宗旨的翻译,其结果是造成了中国在引进外来思想时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格义”方法,即借用中国既有的思想和术语去比附引进的思想和术语,原因就在上面说的佛经翻译是将一种外来思想引入已有强大文化传统的民族。
而这在西方译学传统中根本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格义”方法有利也有弊。
其弊在于对于翻译来说,这绝对是一种不忠实的翻译(因此我们说这也是“看翻译不是翻译”)。
而其利在于,有利于文化的融合。
事实上,正是格义式的佛经翻译,推动产生了中国新的文化,自从佛教引进之后,最早从道家中演化出了道教,后来儒学也演变成了新儒学或者理学,甚至佛教本身在中国也蜕变成了与印度佛教全然不同的禅宗。
相对于重“信”的翻译造成了西方的“征服文化”,重“达”的翻译可说造成了中国的“融合文化”,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这一百余年来,我们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概念、新理论,其中许多是采取“格义”方法的,如“形而上学”“封建社会”等。
这就是一种融合文化,或者“格义”文化,这是西方所不具备的。
造成“征服文化”或“融合文化”的当然都不是真正的“翻译”。
(二)过度理性—见木失林
第二种“看翻译不是翻译”源自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其表现为对于翻译现象的过度解读。
科学主义迷信于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成就,一意想用自然科学方法解释社会人文学科。
其方法论上的特点一是标榜客观性,二是强调体系建构,三是主张定性定量的研究,四是主张形式化,其绝端者则根据reductionism(约化论或还原论),主张大量采用公式、数字和符号来进行描写。
在翻译研究上的表现主要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所谓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这是“忠实”派译论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
“忠实”本可以有忠实于原意和忠实于原文两种理解,但到被强化解释为忠于原文、特别是原文的语言形式之后,翻译就成了对原文词句形式的死板服从和模仿,词、句、语序、音律等都要求丝丝入扣的“对等”或“等值”。
而二十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的发展又为这种这种条分缕析的过度分析提供了方法和可能。
中国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很多翻译理论和技巧著作就充满了这一类的技术“指导”:
名词怎么翻?
动词怎么翻?
名词、动词怎么转换?
介词、副词又怎么处理?
长句怎么拆分?
被动句怎么调整?
等等。
表面上看来,这种理论堆满了语言学术语,有时还使用转换公式和符号,有的更细到了一个一个词的处理(如定冠词the和不定冠词a的翻译),但因为太繁琐了,犹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将下来,不成片断,实际上应付不了复杂的翻译实践。
这样的研究,看上去是翻译,其实并不是翻译。
(三)是我所是—偏执一隅
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对科学主义的语言学派的反拨。
从翻译研究来看,也从原文指向转到了译文和译语社会的指向。
但是其存在的问题也走到了另一面。
由于只强调赞助人意图及社会影响,轻视原文(甚至鼓吹“原文死了”)、忽视翻译过程,结果变成了纯粹的文化研究,对翻译实践毫无具体的指导意义可言,成为人们批评的“什么都是,可就是不是翻译”。
而从文化研究出发的某些策略和主张运用到翻译中还会引起误导。
譬如“异化”论。
提出异化论,本来是希望成为弱势文化用来抵抗强势文化的武器,也就是主张逆前面提到的“征服文化”的路线图而行。
但到了中国,却变成了顺因这个路线图,为中文中的“翻译腔”辩护的主张。
但“文化转向”带来的问题还不仅在此,而在于“开创”了理论研究的另一个传统:
即理论研究的走马灯似的转换。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甚至根本不需要三十年,种种理论不断地在升降起伏。
每一种都以否定前人为起点,而以被人否定告结束。
近三、四十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瞭乱,这里不可能一一评述。
但有一个总的发展趋向:
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派强调原文和作者,七、八十年代的文化学派强调读者和译入语社会,九十年代以降的译者主体性强调译者,本世纪以来则强调翻译的过程研究。
这样,翻译全部过程述及到的四个方面(如果原语和作者分开,译入语和读者分开,则是六个方面)都已经涉及到了。
这四个方面,如果只是片面强调其中某一方面,都只可能是片面的、局部的研究,没有翻译的全局观。
结果也只能是“见翻译不是翻译”。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种情况。
三
从“参禅”的三境界来看,第一境界是认识的初期,一般不会太长,第三境界很难达到,而第二境界的时间最长。
从第二境界到第三境界是个顿悟的过程,也许有人一下子就突然明白了,多数人一辈子就总在第二境界里,迷于其中不能自拔。
讨论看山看水三境界说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怎样让更多人实现从第二境界到第三境界的转变。
这就需要了解,第一境界为什么能“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第二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迷失究竟在哪里?
原因是什么?
这才能为第三境界的“悟道”作好准备。
我认为第一境界之所以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其原因是因为纯出于天然,没有功利之心,没有好胜之心,甚至也没有探究之心。
而第二境界的迷失,一迷于主观,局限于“亲见”即自身之见。
二迷于“知识”,特别是今天所谓“科学”“客观”的知识,在琐细中迷失了自己。
三迷于自我的“入处”,相信自己“亲见”及“知识”得出的结论,偏执于一得之见。
这三“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想刻意求得什么,这就是道家或禅宗说的“机心”。
而一旦有了“机心”,就反而什么也得不到了。
关于“机心”,最有名的故事出自《列子·黄帝》篇: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
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其父曰:
‘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
”(列子,1986:
200)这个人没有机心时,鸥鸟都跟他玩,一旦有了机心,鸥鸟看出来了,就不跟他玩了。
翻译也是如此。
这些年我们谈了那么多的理论,好的翻译反而更难见了,翻译理论里反来复去举的,都是前人的例子。
语言学派细至毫厘的条分缕析,好像没能教会人怎么做翻译,更做不出好的翻译。
文化学派谈翻译对译入语社会起的作用,洋洋洒洒,也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是对既有事实的观察和分析,却无法指导人具体怎么做翻译,因为翻译作品能否起影响、起什么样的影响,并不是当下做翻译的人能够事先确定的。
其他种种理论似乎也是如此,说得再天花乱坠,对翻译实践起的作用却十分有限。
这个现象说得透彻一点,就是“翻译学热闹了,翻译却不见了”。
翻译理论研究成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圈子里的人说得开心,但对翻译的影响却越来越小,真正在做翻译的人基本不把你当回事。
曾几何时,人们突然发现,所谓研究翻译就是炒作翻译理论,于是只见到各种理论在国外轮番上场,然而又引到国内,很多人在根本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跟着起舞。
所谓“创新”就是引一个国外的理论,然后把国内的例子往里面套,以证明该理论的有效。
或者把几个外国理论捏在一起,推导出一个新奇的说法(最多的是把“翻译学”与“某某学”相粘合,就马上形成一个“某某翻译学”的“新学科”,从而填补了“空白”)。
这样的为理论而产生的“理论”,怎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呢?
这样看来,陷于第二境界“看翻译不是翻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有了“机心”而忘了翻译的本来面目,在“理论研究”的幌子下,反而忽视了丰富的翻译实践。
云遮雾罩的“理论”掩盖了缺少翻译实践的苍白。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要达到第三境界的落脚点,或者说,“休歇处”,也就有了。
那就是回归自然,回到翻译实践,让翻译“只是翻译”,也就是进入看翻译的第三境界。
而这时的“见翻译只是翻译”,不是第一境界的简单重复,而应包含更丰富的内容。
我想,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回到翻译的最自然状态,首先就要强调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基本功。
说一千,道一万,翻译离开两种语言的基本能力那就什么都不是。
既做不了翻译,也没有辨别翻译作品对错、好坏、美丑的能力。
因此强调研究翻译的人的翻译实践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理论应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对的,但是第一,这句话的适用度对不同学科是不同的,对纯理性学科如数学、物理等也许如此,但对翻译这样的应用性学科、实践性学科并不适用。
第二,理论应与实践保持一定距离不等于研究理论不需要考虑实践,更不能成为不顾实践,甚至掩盖自己实践能力差的借口。
在翻译研究人才的培养上尤其要注重打下实践能力的基础,翻译硕、博士的培养如果不从注重实践能力着手,就会误人子弟。
第三,所谓理论,只有来自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有意义的。
翻译实践有对错、好坏、美丑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这三个方面应该一层高于一层。
一个真正为实践服务的翻译理论应该是能兼观这三个方面、帮助实现这三个方面要求并能对之进行检验的理论。
实践有不同层面是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而理论却要能适应不同层次的需要而不能只顾一个方面(例如语言学派译论其实关心的只是一个“对错”),才能真正为实践服务。
第四,理论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认为可以在理论基础上推导出新的理论而不接受实践检验是靠不住的。
外来理论要不要引进及如何引进应作如是观。
认为西方理论天然正确,搬用几句西方理论观点、术语、概念,就是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西方理论是否正确、应否引进,只有在实践、特别是自身实践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断。
而最成功的引进应该是潜移默化,把别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或见解融合进自己的主张或理论里,而不是装腔作势,乱堆概念和术语以吓人。
这样看来,回到“见翻译只是翻译”的第三境界,就是重新强调实践的至高无上性。
以此来纠正第二境界之偏,让理论的研究回归到“来自实践、指导实践、提高实践、受实践检验”的本原。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语言 文化 论文 看山看水 有感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全自动电容电感测试仪.docx
#全自动电容电感测试仪.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