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讲 亚士多德的《诗学》文档格式.docx
第五讲 亚士多德的《诗学》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22233129
- 上传时间:2023-02-03
- 格式:DOCX
- 页数:16
- 大小:32.73KB
第五讲 亚士多德的《诗学》文档格式.docx
《第五讲 亚士多德的《诗学》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五讲 亚士多德的《诗学》文档格式.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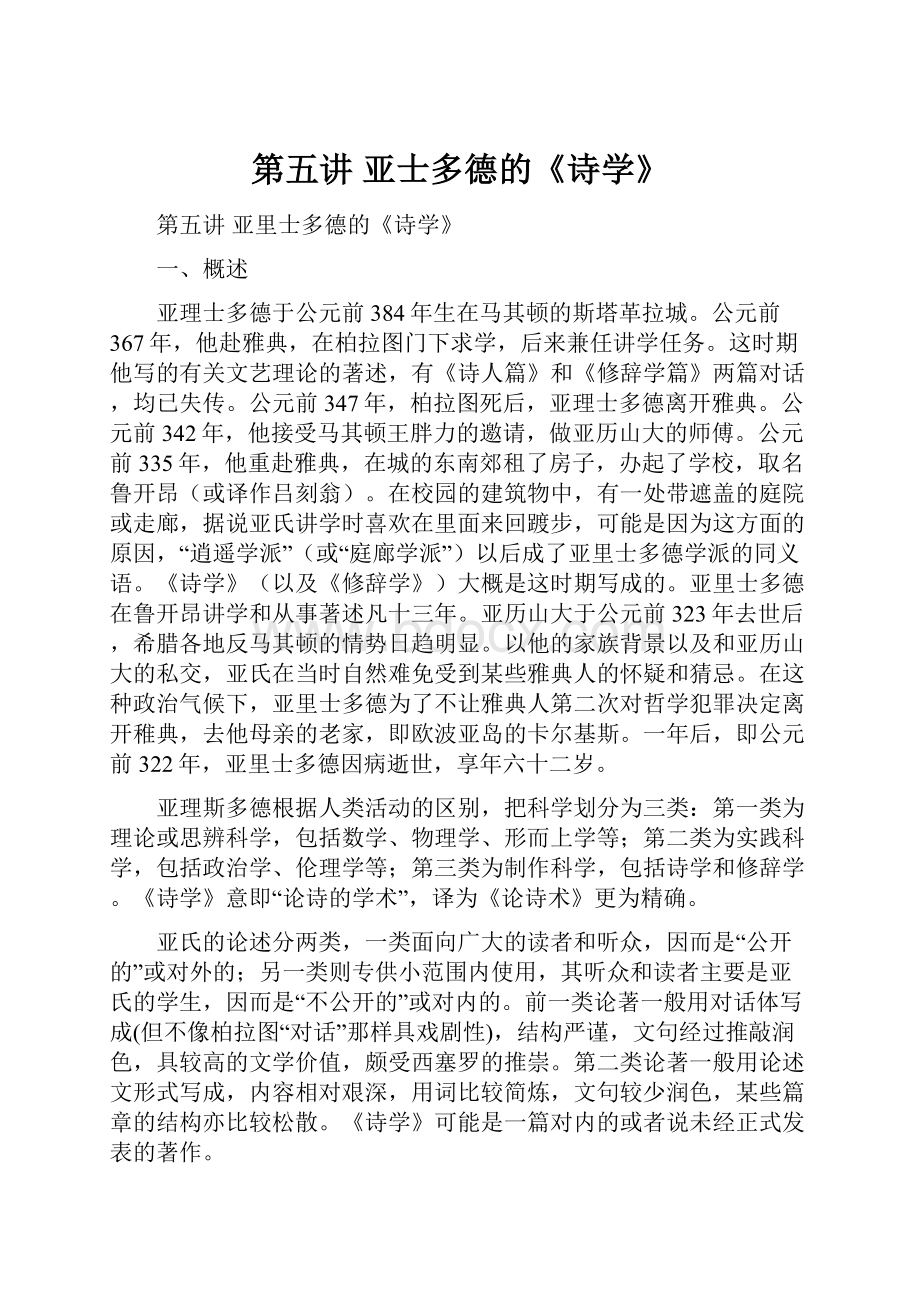
亚氏就柏拉图对“摹仿性的诗”的批判,提出了异议。
他通过强调诗源自人的模仿本能,诗和历史的比较(诗具有逻各斯)为诗的真实性和价值作了有力辩护。
我们大致可以把《诗学》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序论,包括第一到五章。
亚氏先分析各种艺术所摹仿的对象(在行动中的人)、摹仿所采用的媒介和方式;
由于对象不同(好人或坏人),媒介不同(颜色、声音、节奏、语言或音调),方一式不同(叙述方式或表演方式),各种艺术之间就有了差别。
亚理斯多德进而指出诗的起源。
他随即追溯悲剧与喜剧的历史发展。
第二部分包括第六到二十二章。
这部分讨论悲剧,亚理斯多德先给悲剧下个定义,然后分析它的成分,特别讨论情节和“性格”,最后讨论悲剧的写作,特别讨论词汇和风格。
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三到二十四章。
这部分讨论史诗。
第四部分,即第二十五章,讨论批评家对诗人的指责,并提出反驳这些指责的原则与方法。
第五部分,即第二十六章,比较史诗与悲剧的高低,结论是:
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艺术的效果,达到摹仿的目的,因此比史诗高。
《诗学》不是一篇完整的、经过作者认真整理润色的、面向公众的著作。
成文以后,又历经波折,包括被搁置地穴多年,原稿中平添了一些损蚀和模糊不清之处。
此外,历代(尤其是早期的)传抄者和校订者的增删和改动,有的或许符合作者的原意,有的则可能纯属杜撰,故此反而加大了理解的难度。
从“技术”的角度来衡量,《诗学》不是白璧无瑕的。
《诗学》中的术语有的模棱两可,个别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
文字的布局有些凌乱,某些部分的衔接显得比较突兀。
从十五世纪末起,《诗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各种校订本、译文和评注纷至沓来,一时间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以上内容参照了现有中译本的“导言”,并作了订正。
)
二、《诗学》论析
(一)诗的创作来自于人的摹仿本能。
艺术的分类以及诗的分类(音乐、绘画、雕塑、悲剧、喜剧、酒神颂、讽刺诗、史诗)标准依据模仿的媒介(声音、颜色或语言)、模仿所取用用的对象(神、好人、坏人等)和方式的不同(歌唱、叙述或扮演,韵文还是散文)而定。
要点:
亚氏将诗的根基放在人的摹仿本能上,强调了摹仿性的诗是不能任意取缔的。
也正是因为诗源自模仿性的本能,我们要善于利用诗来加以政治伦理教化。
故而亚氏强调模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
且看亚氏的这段话:
“作为动物而论,人类为什么比蜂类或其它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达到更高的政治组织,原因也是明显的。
照我们的理论,自然不造无用的事物;
而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
声音可以表白悲欢,一般动物都具有发声的机能:
它们凭这种机能可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
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
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它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在《诗学》第四章中,亚氏把诗的起源归结为人的两个天性:
“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攀仿的本能。
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子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
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
”两相结合(语言能力与模仿本能),诗的产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正因为亚氏把诗的产生归结为人超出动物的语言能力以及人的模仿本能之上,“模仿性的诗”就无法像柏拉图所设想的那样能够从城邦中清除出去了。
如果清除“模仿性的诗”不是一种可行的举措,那么,为什么不转而对其改造而加以政治利用呢?
说到底,在亚氏那里,诗不过是对语言的理性运用。
亚氏向他的门徒讲授诗的制作,无非是告诉他们如何将逻各斯灌注到人们的语言模仿行为之中。
好的诗人要学会利用人们的摹仿天性,从而让语言逻各斯进入到他们的灵魂。
如果没有合格的诗人来承担这项工作,人们就会滥用其语言能力和模仿本能,由此堕落到“禽兽不如”的地步:
“悖德(不义)而又武装起来,势必引致世间莫大的祸害;
人类恰正生而具备[他所特有的]武装[例如言语机能],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虑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末尝不可被运用来逞其狂妄或济其罪恶。
于是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
”
悲剧摹仿的对象是“好人”,而喜剧摹仿的对象是较差的人。
模仿好人的悲剧当然比喜剧有价值。
悲剧起源于酒神节仪式,本义为“山羊歌”(或羊人剧、马人剧等),解释不一而足,如因为
(1)比赛的奖品是山羊,
(2)演出时歌队围绕着作为祭品的山羊,(3)歌队由扮作山羊的萨图罗斯组成(在阿提开地区,马尾和马耳似是歌队成员常用的系戴物)。
第五章谈到了史诗与悲剧的几点不同。
(二)悲剧的定义及解读。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
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
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
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第六章)
重点是:
(1)模仿行动中的人,情节为第一要素:
悲剧是对“行动的模仿”,而非当今很流行的一种看法即对“人物性格”加以模仿。
人在行动中时时面临着“选择”的问题,所以亚氏强调悲剧对人物行动的模仿,就是要强调悲剧的本质在于展示“选择”的那一关键时刻。
“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
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
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
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
此外,没有行动即没有悲剧,但没有性格,悲剧却可能依然成立。
亚氏上面给出的解释显然是出自他的伦理学主张。
人的美德体现于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体现于他在行动中的“选择”,性格不过是行动的副产品而已,那么所谓的“自我”又何尝不是行动的副产品呢?
亚氏关于行动与性格之关系的论述是极具启发意义的。
情节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由一个完整的行动,也即一个关键时刻的“选择”构成的。
“合乎德性的行为并不因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譬如说,公正的或节制的。
除了具有某种性质,一个人还必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
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
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
第三,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
……因此,虽然与公正的或节制的人的同样的行为被称为公正的和节制的,一个人被称为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却不是仅仅因为做了这样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像公正的人或节制的人那样地做了这样的行为。
《诗学》中所谓的“发现”和“突转”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对“选择”这一关键时刻的照亮而已,也正是关键时刻的“选择”区分了“结”和“解”之间的边界。
情节应该是单线结构,不能用复杂的情节来分散悲剧的效果。
(2)悲剧发生的原因(过失)与效果(怜悯与恐惧)。
尽管这些被展示出来的道德实践活动不是十分明智,因为道德实践者是人而不是神,悲剧的发生不可避免。
“就是由于道德德性是这样的适度,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
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
”悲剧通过展示一个不够十分明智的却是向善的道德实践活动去教导民众以“明智”,通过其引发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来驯化民众的自然情感。
亚氏刻意强调了悲剧性的冲突应该设置在近亲之间,目的为何?
这是因为情节的“编织”越是能够激发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就越是能更好地完成其伦理的、政治的使命。
如何能够让悲剧引发观众最为深切的怜悯与恐惧呢?
《诗学》第十三章阐明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关节。
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详尽的阐明:
“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
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
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而引起的……”经由这三种否定之后,亚氏限定了悲剧之怜悯与恐惧效应的制造方式:
悲剧的主角应该既非完人,更非坏人,而是一个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又不够明智(所以会犯过失)的人。
悲剧应该表现主角从顺境转入逆境,“其原因不在于人物为非作恶,而在于他犯了大错误,这人物应具有上述品质,甚至宁可更好,不要更坏。
”亚氏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三卷对何谓“犯错误”(过失)作了详尽的分析。
此处再将亚氏的相关论述简要引证如下:
“违反意愿的行为并不产生于对普遍的东西的无知(这种无知受到人们谴责),而是产生于对个别的东西,即对行为的环境和对象的无知。
原谅和怜悯是对于对这些个别事物的无知的。
……不过,要说一个行为处于这种无知状态而违反当事者的意愿,它还必须是痛苦并引起了他的悔恨的。
……把出于怒气和欲望的行为称为违反意愿的行为似乎不妥。
亚里士多德用“过失”来解释悲剧的原因,并在《诗学》各处或隐或显地对此加以强调,目的无非是用其来消解以“命运”或“运气”来制造(或解释)悲剧的做法。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诸多论述可以说明这一点。
“幸福和不幸并不依赖于运气,尽管我们说过生活也需要运气。
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动,相反的活动则造成相反的结果。
”“如果幸福通过努力获得比通过运气获得更好,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就是获得它的方式。
因为在自然中,事物总是被安排得最好。
在艺术以及所有因果联系,尤其是在最好的因果联系中,也都是如此。
如果所有事物中最大、最高贵的事物竟听命于运气,那就同事物的秩序相反了。
“对于人间的事务,我们也不是全都加以考虑。
……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们能力以内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唯一还没有讨论过的东西。
因为被看作原因的东西中包括自然、必然和运气的东西,以及努斯和人为的东西)。
每一种人所考虑的都是他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关系到是一个人是善还是恶,做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就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我们希望这个理想城邦在各方面都具有足够的配备——外物的丰啬既寄托于命运,在命运成为主宰的范围以内,我们就只能作虔诚的祈愿。
至于城邦的善德却是另一回事:
这里我们脱离了命运的管辖,进入人类知识和意志的境界[在这个境界内,立法家就可以应用他的本领了]。
亚氏对待“fortune”的态度相似于孔夫子,看重人伦,搁置天命。
因此,亚氏将“过失”作为悲剧的原因来取代“运气”或“命运”的做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悲剧主角行动的过失可能为自己带来“死亡”,但悲剧的主角作为英雄人物,其高贵之处在于:
他愿意以死亡来承担自己的过失,并通过死亡来彰显生命的高贵。
所谓的“悲剧”并非指其结局是“悲惨的”或“悲伤的”,套用尼采式的说法,这是因为悲剧的“死亡”本质是对美德最具“权力意志”的彰显。
悲剧的主角是真正勇敢的人:
“人能够多勇敢,勇敢的人就能够多勇敢。
所以,尽管他也对那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物感到恐惧,他仍然能以正确的方式,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并为着高尚[高贵]之故,对待这些事物。
这也就是德性的目的所在。
“勇敢就包含着痛苦,它受到称赞也是公正的,因为承受痛苦比躲避快乐更加困难。
……他承受这些痛苦并非是出于意愿:
他肯承受它们是因为这样做是高尚[高贵]的,不这样做是卑贱的。
而且,他在德性上愈完善,他所得到的幸福愈充足,死带给他的痛苦就愈大。
因为,他的生命最值得过,而他又将全然知晓地失去这最大的善,这对他必定是痛苦的。
但是他的勇敢并不因这痛苦而折损,而且也许还因此而更加勇敢。
因为他所选择的,是在战斗中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做得高尚[高贵]。
我们不妨将上面这段话视为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之“牺牲”精神所作的礼赞。
如果所有类型的诗的制作都能向这种用逻各斯铸造而成的“悲剧”学习的话,城邦如何能够不成就其伟大与不朽?
(3)亚氏的悲剧定义最引发争议的问题就是关于“陶冶”(“净化”、“宣泄”)的理解问题。
“净化”在柏拉图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词汇,《斐多篇》中的苏格拉底这样说道:
“那些关心自己的灵魂,不肯为身体活着的人把背朝着普通人,不肯与他们为伍,感到他们不知往何处走。
这些人自己深信,哲学有解放作用和净化作用,是不能抗拒的,因此心向哲学,一切听从哲学,拳拳服膺。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这个词有医学上、宗教上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把在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哲学才具有的功能赋予了“悲剧”。
罗念生先生在其《诗学》译本“译者导言”部分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因此这个医学术语,在这里是指悲剧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使它们经过锻炼,达到适度的意思,而不是把怜悯与恐惧之情加以净化或宣泄。
我们姑且按照这里的解释,把《诗学》第六章中的‘卡塔西斯’一词译为‘陶冶’。
按照亚氏的看法,“灵魂的状态有三种:
感情、能力与品质,德性必是其中之一。
感情,我指的是欲望、怒气、恐惧、信心、妒忌、愉悦、爱、恨、愿望、嫉妒、怜悯,总之,伴随着快乐与痛苦的那些情感。
能力,我指的是使我们能获得这些感情,例如使我们能感受到愤怒、痛苦或怜悯的东西。
品质,我指的是我们同这些感情的好的或坏的关系。
例如,如果我们的怒气过盛或过弱,我们就处于同怒的感情的坏的关系中;
如果怒气适度,我们就处于同这种感情的好的关系中。
”所谓“适度”,有的中译本译为“中道”、“中庸”。
亚氏认为,单就恐惧、怜悯这两种情感自身而言,无所谓好坏。
好坏取决于它们是否“适当”,这就涉及到时间、场合、涉及到的人物、原因,以及方式等诸多因素。
恐惧、怜悯与勇敢是相关的,勇敢则是四种主要的美德之一。
套用海德格尔式的表述,恐惧与怜悯可以视为在世的基本情绪,一个人不能学会适当的恐惧与怜悯,也就不能有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
柏拉图在《法篇》中专门谈及了“恐惧”的问题,主导对话的“雅典人”得出结论说:
“对于培育好人的政治术来说,搞懂灵魂的本质与性情是极其重要的。
”这位雅典老人还提出:
“教育,就是对快乐与痛苦的情感加以正确地约束。
”这些说法都被亚里士多德完全接受。
既然美德来自于对自然情感的驯化,使其“合适”。
那么政治术的本质就是使用各种驯化手段以实现这个目的。
而作为政治术重要分支(或帮手)的诗自然也应该担当起这样的责任。
在所有的诗的类型中,悲剧又被亚氏赋予了最重要的使命,这是因为悲剧牵涉到了两种最基本,也是与美德的培育最具相关性的情感,即恐惧与怜悯。
只有自然的情感按照逻各斯的引导被驯化以后,人们才能学会如何明智地生活,才能在行动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三)诗与历史的区分:
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和诗至少有如下三点区别。
(a)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b)历史记载具体事件,诗则着意于反映事物的普遍性;
(c)历史叙述一个时期内发生的所有事情,诗却意在摹仿完整的行动。
历史把事实变成文字,把行动付诸叙述,把已经发生的事变成记载中的事。
历史取之于具体的事例,还之于具体的记载;
从这种由具体到具体的形式变动中看不到历史的哲学可塑性。
与之相比,诗取材于具体的事件,却还之于能反映普遍性和因果关系的情节。
“诗是一种“积极”的艺术,诗人的工作具有可贵的主动性。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诗”不过是其伦理观念的“虚拟情境化”。
诗之所以高于历史,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它的时间向度,诗是指向将来的,而历史只不过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记录。
由此诗蕴含了“选择”的可能性,而在历史中已不存在“选择”的可能性了。
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就不存在目的性,而没有目的性,历史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呢?
诗正是因为蕴含了“选择”而具有目的性,从而能够构造为一个有机的(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的)整体;
其二在于,诗有着虚构的“特权”,而历史则没有。
当然,诗不能随意虚构,而是要在遵守逻各斯的前提下进行虚构,这样一来,尽管某个事件并没有发生过,但却显得可信,而“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
”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尽管确实发生过,但其却并不符合“逻各斯”,因而没有普遍性的意义。
正是因为诗有着在遵守“逻各斯”的前提下自由虚构的特权,它就能灵活地变换各种情境以展示各种各样的“德性的实现活动”。
(四)亚氏《诗学》与柏拉图哲学、诗学的关系。
亚氏在讲授《诗学》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解决哲学和诗之间的争论。
亚氏对柏拉图关于诗的批判的批判就是这一意图的显露。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亚氏到底如何看待哲学和诗的关系。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区分诗与哲学的标准来自于灵魂的构造。
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哲学根植于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并联合激情对欲望加以节制;
而模仿性的诗则根植于灵魂中的欲望。
灵魂中的理性和欲望的冲突外化为哲学和诗之间的冲突。
民众的灵魂相较于哲学家的灵魂,前者的灵魂为欲望所主宰,而后者的理性部分牢牢控制了欲望部分,将对某个肉体的欲望升华为对智慧的爱。
模仿性的诗迎合民众那为欲望所主宰的灵魂,而哲学(诗化的形式:
辩证法)则是高贵的灵魂为俘获那些有追求智慧的“潜能”而又没有真正转向追求智慧的幼稚的灵魂所编制出来的网罟而已。
哲学和诗的冲突也表征了哲学家和民众的冲突。
当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指责模仿性的诗不过是影像,而非真理的时候,他并不是在指责诗的“虚构”,而是指责诗迎合了民众追新逐异的欲望,所谓的“虚构”并不是区分哲学和诗的标准,因为哲学为了对城邦实施教育也需要高贵的谎言。
所谓渎神一说,也不过是指责诗违背了理性而已。
事实上,柏拉图并不是要对诗本身加以完全否定,柏拉图不就是用诗化(戏剧化)的哲学来对城邦展开教导吗?
但在柏拉图看来,“模仿性的诗”乃是哲学(真理、智慧)哲学化的诗(辩证法)的对手。
哲学性的诗要想在城邦中获胜,就必须驱逐“模仿性的诗”。
但问题是,民众所喜欢的恰恰是“模仿性的诗”,而非哲学的诗化形式“辩证法”。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持的这种立场无疑是把哲学家放到了和民众对立的位置上。
问题是,这种对立除了给苏格拉底带来死亡之外,还能给城邦带来何种积极的后果呢?
这是亚里士多德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亚氏批判柏拉图的“理式”说,批判柏拉图对诗的批判,……如此种种都来自于亚氏对哲学家和城邦关系的反思。
在亚氏看来,哲学(哲学家)和城邦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哲学(哲学家)的“下降”去克服,即哲学必须“下降”为真正具有实践性的政治学,而哲学家必须“下降”为真正的政治家,“智慧”必须下降为“明智”。
如果不能完成这种“下降”,哲学对政治实践的参与必然失败。
所谓的“下降”并没有“屈尊”之意,而是说,哲学如果不作这种“下降”,就无法实现其对城邦生活的真正引导作用,不能对城邦生活施加真正影响的哲学到底是哪门子哲学呢?
这需要引述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说法来支持这一论断。
在《形而上学》中,亚氏这样说道:
“一个人在困惑和惊奇的时候,认为他自己是无知的……因此,因为他们是为了免除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显然他们是为了认识而追求科学,而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目的。
并且这一点是由事实加以确证的;
因为那是在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提供舒适和娱乐的事物都已得到保障时,才开始寻求那样的知识的。
那么,很明显,我们不是为了任何其他利益的缘故而寻求它;
而是当人们自由的时候,人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人而存在时,所以我们追求这门作为惟一自由的科学,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存在的。
亚氏的这段话似乎是对哲学所做的赞美。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七章“幸福与沉思”中,亚氏也指明“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最合乎德性的生活。
但如果我们从第七章读到这部作品的末尾,即第十卷第九章“对立法学的需要:
政治学引论”,我们就可发现亚氏对沉思生活(包括哲学)所作的赞美是有保留的。
沉思的生活是属神的,如果人能够过这种属神的生活当然是幸福的。
可是人毕竟过的是人的生活,而对于人的生活而言,单单过一种“沉思生活”是不够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来了个“突转”:
“但是,人的幸福还需要外在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自足的。
”“认为最高善在于具有德性还是认为在于实现活动,认为善在于拥有它的状态还是认为在于行动,这两者是很不同的。
因为,一种东西你可能拥有而不产生任何结果,就如一个人睡着了或因为其他某种原因而不去运用他的能力时一样。
但是实现活动不可能是不行动的,它必定是要去做,并且要做得好。
”从属神的方面来看,“沉思生活”由于其自主性而高于其他的德行实现活动,如政治。
但倘若从人的角度,从城邦生活的角度来看呢?
“这里,我们可以说,在今世以及上代,一切以善德为尚的诚笃的贤者,他们的生活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政治生活和哲学生活。
要确定真理究竟属于哪一边,不是容易的;
然而这正是一个重要关头,无论其为个人或为城邦,必需凭其明哲,抉择一条较优胜的行径,由以达成较高尚的志趋(目的)。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一个在沉思的人,就他的这种实现活动而言,则不需要外在的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反倒会妨碍他的沉思。
然而作为一个人并且与许多人一起生活,他也要选择德性的行为,也需要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过人的生活。
毫无疑问,亚氏是主张哲学从沉思走向政治活动的。
他肯定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参与政治的动机,但却批评他们的政治参与行动不够明智。
他们提出的许多见解太过于不切实际,他们太过于从“理式”出发来构想政治,岂不知,这是一种颠倒?
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说:
“事实与生活是最后的主宰者。
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东西必须交给事实与生活来验证。
如果它们与事实一致,我们就接受。
如果与事实不合,它们就只是一些说法而已。
”亚氏对柏拉图“理式”的批判,不能仅从哲学上去理解,而更应该从政治上去加以分析。
一个搞哲学的、有智慧的人,需要将哲学下降为政治学、伦理学。
哲学沉思只是理智德性的一部分,它需要转化为外在的实现活动,并且去指导人们该如何生活。
亚氏区分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但区分不是割裂,亚氏最终的目的还是企图通过“明智”将二者连接在一起。
苏格拉底、柏拉图不同于以往那些孤傲的哲学家(亚氏对那些只顾埋头沉思而不问政治的哲学家是带有嘲讽语气的)是因为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诗学 第五讲 亚士多德的诗学 第五 士多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城市规划基本知识》深刻复习要点.docx
《城市规划基本知识》深刻复习要点.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