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外商投资纠纷若干疑难问题文档格式.docx
论外商投资纠纷若干疑难问题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21820512
- 上传时间:2023-02-01
- 格式:DOCX
- 页数:13
- 大小:33.66KB
论外商投资纠纷若干疑难问题文档格式.docx
《论外商投资纠纷若干疑难问题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外商投资纠纷若干疑难问题文档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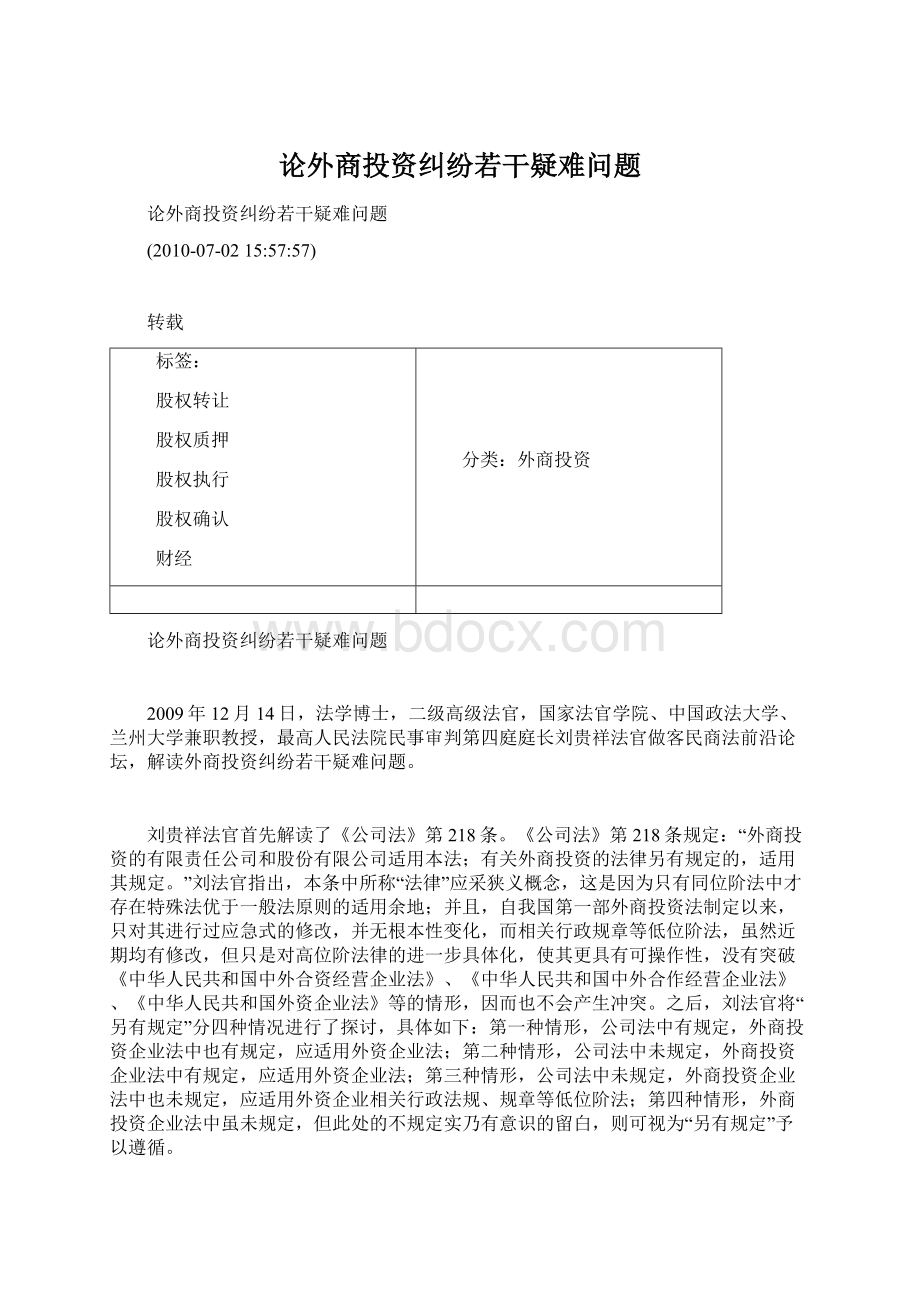
”刘法官指出,本条中所称“法律”应采狭义概念,这是因为只有同位阶法中才存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适用余地;
并且,自我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制定以来,只对其进行过应急式的修改,并无根本性变化,而相关行政规章等低位阶法,虽然近期均有修改,但只是对高位阶法律的进一步具体化,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没有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等的情形,因而也不会产生冲突。
之后,刘法官将“另有规定”分四种情况进行了探讨,具体如下:
第一种情形,公司法中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也有规定,应适用外资企业法;
第二种情形,公司法中未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有规定,应适用外资企业法;
第三种情形,公司法中未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也未规定,应适用外资企业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等低位阶法;
第四种情形,外商投资企业法中虽未规定,但此处的不规定实乃有意识的留白,则可视为“另有规定”予以遵循。
其次,刘贵祥法官介绍了股权转让的相关问题。
在实务中,股权转让纠纷出现率较高,约占外商投资纠纷的20%左右,股权转让纠纷多数发生在出让方和转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一方欲解除合同时,这类纠纷值得认真探讨。
接下来,刘法官从股权转让的行政审批、老股东的同意权以及股权质押以及股权执行四方面深入分析了股权转让纠纷。
他认为,对于股权转让的行政审批问题,在未经行政审批时,不宜直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而应认定此协议不生效,即此时股权转让协议处于一种效力待定状态,以一定条件的成就来决定该合同的效力,对当事人具有形式上的约束力,不能随便的解约,仍有一定的附随义务。
这样做的实务意义在于:
认定合同无效和合同不生效的结果是不同的。
在合同不生效的情况下,合同相对人得请求外商企业履行报批义务,法院可将外商投资企业追加为第三人,让其履行报批义务。
对于老股东的同意权问题,公司法与外商投资相关法规的规定并不一致,刘法官就此问题分别从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二个层面分别探讨了适用何者更为适宜,并提出了自己对于更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股权质押方面,刘法官指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股权质押方面规范的差别主要在行政规章层面上,而依据《合同法》,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
应此,对于股权质押合同效力的判定不应动辄就已部门规章作为合同无效的依据。
他认为,股权质押合同,自合同签订时合同生效;
股权质押合同生效时,股权并不发生变动;
股权质权,在办理质押登记时取得。
对于股权执行问题,目前商务部和法院对于在执行中,法院可不可以直接以折价、拍卖的方式将股权转移到他人名下,就价款执行的问题存在分歧。
股权执行的现状是老股东不同意,法院便不能执行。
而已执行其股权收益作为股权执行的替代办法并不能有效保护债权人。
刘法官认为采用类似于公司法中规定的方法,即老股东不同意时就应购买该股权,较符合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的要求。
最后,刘法官从对股东权的侵犯问题以及隐名股东问题两个角度阐述了股权确认问题。
刘法官首先将“股东权的侵犯”限定为仅指类似于侵权法中的对股东权的侵犯。
进而,分为在设立外企时以虚假登记的方式取得股东身份和已取得股东身份后以虚假材料变更股东两种情况对股东权的侵犯问题进行了分析。
针对隐名股东问题,刘法官主要探讨了委托投资协议问题,并着重探讨了委托投资协议的效力以及委托投资协议无效的后果等问题。
刘贵祥法官的报告结束后,叶林教授、刘俊海教授以及王轶教授分别紧扣刘贵祥法官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本次论坛在与会师生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主持人: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刘贵祥博士到我们民商法前沿就外商投资纠纷中的疑难问题做一个专题的演讲,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的到来。
首先请王利明副校长致词。
王利明:
尊敬的刘庭长、老师们、同学们,首先我代表学校对刘庭长在百忙之中能够抽时间来给我们做讲座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庭长不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可以说是专家型的、学者型的法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司法审判经验,而且坚持钻研一些学术前沿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民商法方面的著述。
特别是在涉及到公司法、担保法等等这些方面有很深的研究,有很多的观点对我们国家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我在过去写的许多文章也多次引用刘庭长的很多观点。
刘庭长对我们国家的许多司法解释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很多学术观点也都体现在这些重要的司法解释里面,可以说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是代表了现在实务界的主流观点的。
刘庭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讲座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实务经验,也会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
我相信我们广大师生一定会从刘庭长的讲座中得到很多的收获和很大的启发。
我本人非常感谢刘庭长对人大法学院的支持和帮助,也希望将来刘庭长能经常来人大法学院和我们交流,再次感谢刘庭长,谢谢大家!
刘贵祥:
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人大法学院的同学们就外商投资企业纠纷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
我过去从事了较长一段时间的非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从事涉外商事审判工作不足一年,还谈不上有很深的见解。
但在近期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过程中,对有关法律适用问题有一些感受,今天也算是有感而发吧。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对《公司法》第218条的理解问题
大家都知道,《公司法》第218条规定:
”这条规定虽然简明扼要,却解决了公司法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法律出现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了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一些难题。
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着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发、后法优于前法等规则,但实践中,当我们依据这三个规则选择适用法律的时候,并不那么简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除了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外,其他两个规则的适用以同位法之间的规范冲突为前提,如果不是同位法,没有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新法优于旧法之规则的适用余地。
这在立法法中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有人往往忽略这个重要前提。
比如,有人将民法通则与行政法规相比较,把行政法规视为民法通则的特别规定,这显然是欠妥的。
其二,关于同位法的判断。
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属于同位法,存在不同的看法。
有观点认为,全国人大制定的是基本法律,其效力应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果二者发生规范冲突,应优先适用前者。
我认为,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同样具有国家立法权,只是立法范围有所差异。
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具有最高效力外,宪法、立法法并未对二者制定的法律在效力等级上进行区分。
在《立法法》未明确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效力等级上有所区别的情况下,认为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属上位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属下位法的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就《物权法》与《担保法》的关系而言,二者当属同位法,在《担保法》的规定与《物权法》的规定不一致时,就不能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选择适用法律。
又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而公司法是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的,难到二者不是同位法吗?
在此,还应强调一点,在上位法与下位法出现冲突时,法官在裁判时应当选择适用上位法,但不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下位法的效力作出评判,那是立法机关应当作的事情,否则,将有僭越立法权之嫌。
其三,关于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判断。
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合同法相对于民法通则关于合同之债的规定,属特别规定,而相对于保险法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则属一般规定。
其四,三个规则适用的结果,可能会得出选择适用不同法律的结论,比如说,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这个规则时,应适用A法;
但如根据新法优于旧法这个规则,则应适用B法。
《立法法》第86条针对各种冲突的情形,给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
(一)同一机关制定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二)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三)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但这种方法很麻烦,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这种提请裁决的先例。
如果在实务中真是遇到这种情况,程序是十分复杂的。
我们注意到了,这几年出台的法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采取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办法,就是在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当出现冲突的时候如何适用法律,类似于《物权法》第178条、《公司法》第218条等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而对法律适用做了明确规定。
从立法的考量来看,这么规定是必要的,而且也能解决实务当中的一些问题。
问题是,《公司法》218条的规定在具体应用中,要比《物权法》第178条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
首先,218条所称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也就是我们要对它做限缩性的解释还是扩张性的解释,如果是狭义的法律,则仅指我们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三部法律,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
如果是广义的法律,则还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立法法》规定效力等级的时候实际上是采取了广义的法律的概念,把这不同类别的法律规范都做了表述。
如何理解这里的“法律”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这涉及我们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之外,相应的实施条例和实施细则,还有过去的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制定的、国家工商管理局制定的和外资有关的一系列的行政规章,比如说《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的比例的规定》、《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的规定》等等。
如果我们对《公司法》第218条的“法律”作广义的理解,这些规定均属于其中的“另有规定”。
我本人认为应作狭义理解,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讨论:
第一方面,如前所述,只有同位阶法才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新法与旧法的问题。
显然《公司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关外商投资的三部法律的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以及其他的行政规章,相对于公司法而言则是低位阶的法律,是对《公司法》或者外商投资企业的三部法律作具体性的、补充性的规定。
因此,当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与公司法存在冲突时,因其属于低位阶法,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一般应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之所以强调一般,是因为还要考量特殊情况。
如果实施细则或条例只是对三部法律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具体化,则应认为其体现的仍是该三部法律的精神,则在其与公司法存在冲突时,仍应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规则,认定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或条例应优先于公司法适用。
当然,如果实施细则或条例系对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所作的补充规定甚至本身就与三部法律存在冲突时,应认为其已不能体现三部外商投资法的精神,从而不能认为其仍属特别法。
此时,应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优先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第二方面,前一个方面是依法律适用规则进行的分析,着眼于我国立法现状的角度,也应得出相同的结论。
一般而言,我国的法律修改是比较频繁的,《公司法》1993年颁布后,又修改了两三次,到2005年作了彻底的修改。
其它法律的修改的间隔时间一般是10年左右。
但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几部法律30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为了适应入世的需要对个别的条款作了一些应急式的修改,没有从我们外资管理的制度、体制上做一些根本上的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与法学研究水平与后来尤其是《公司法》最新修改之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法学研究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应该来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司法实践还停留在那个时候的理念上,以其作为一个标尺来适应现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解决我们现在的纠纷,无异于削足适履,可以想象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来说,当外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规定不一致时,就要尽可能的缩小外资企业法的适用余地。
也许大家会说,低位阶的法律规范尤其是行政规章事实上并不是三十年前制定的,95年、97年、2000年、2001年甚至更新的也有,不能说这些新制定的规章都是过时的吧?
问题是我们的低位阶法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把三部法律有关外资行政管理的规定变得更具有可操作性,变得更坚不可摧,而没有更贴近目前的社会经济现实及新公司法的理念,行政管理仍然细致入微到了审查民事合同或当事人商业判断是否合理的程度。
当然,在高位阶法律未修改的情况下,要让新近制订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低位阶法律有根本性改变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事实上,低位阶法的规定,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并未规定,而与公司法又存在明显不一致之处者,俯拾皆是。
在此,我略举一二:
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规定,《公司法》第8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500万元人民币。
但是《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却对外商投资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作出了不同于《公司法》的规定,要求外商投资股份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不低于3000万人民币。
事实上,在公司法修改前该暂行规定已突破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000万元最低注册资本的规定;
工商局登记、外资部门审批坚持着3000万元的规定,那么真的发生纠纷了,我们到底以哪个为依据,就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人公司。
《公司法》规定了一人公司的最低资本额,外商投资企业法没有这样的规定。
还有内资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只能办一家一人公司,不能同时办若干家,但是外商投资企业方面的法律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这些恐怕都是二者不一致的地方。
尤其是,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的变动方面,如股权转让、股权质押,股权执行等等,行政规章、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法》的规定亦存在较大差异。
当出现这些冲突的时候,是依据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处理纠还是依据《公司法》处理,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我个人认为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当然,实践情况要复杂得多,简单地得出适用公司法的结论在实务中有时未必行得通。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规范可能都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越是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可操作性越差,越是低位阶的法律可操作性就越强。
往往有的时候低位阶的法律规范成了某一个法律领域具有支撑作用的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就是其中一例,而且是非常突出的一例。
此时,如果我们简单的根据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的规则适用《公司法》,会出现很大问题。
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股权转让的时候涉及到老股东同意的问题,《公司法》与商务部“关于股权变更若干规定”明显存在区别。
当你去具体操作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相关的行政审批部门要求你提供一系列的文件,包括所有老股东对股权转让合同书面同意的文件,没有所有老股东同意,要想在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审批手续是不可能的。
而根据公司法为,只要有一半老股东同意就可以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因此,行政审批部门现有的做法问题重重,实践中很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一般情况下要坚持《公司法》优于低位阶适用,但是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我们需要法院作出的裁判要能够执行,如果不能执行,你说的再头头是道也是一纸空文啊。
法官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当然应考量各种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公司法218条的规定、选择适用法律的基本规则以及我国外资行政管理的现状,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其顺序依次为:
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实施细则或条例及行政规章,其规则可以概括为:
(1)人民法院审理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纠纷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2)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合称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规定不一致或者公司法未规定的,应当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规定;
(3)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细则或相关行政法规(以下合称相关行政法规)与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一致,但与公司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
(4)外商投资企业法没有规定,相关行政法规作了规定但与公司法不一致的,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5)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均未作规定,相关行政法规作了规定的,适用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股权转让
关于股权转让,我分四个问题讲。
(一)关于未经审批的合同效力及后果
一是关于未经审批的合同效力及后果问题。
股权转让纠纷是近几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纠纷中出现比较多的一类纠纷,今年最高法院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纠纷中股权转让纠纷大概占了20%左右。
多数问题发生在双方签订股权协议之后一方想解除合同或者毁约,有的时候是出让方,有的时候是受让方。
发生这种纠纷的原因是,当签订协议之后出让方发现股权的价值上升,或发现有更大利益的时候,就会找理由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或者不生效。
相反,在股权价值变低的时候,则多是受让方提出来合同无效,有的甚至受让人已经在企业中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营管理,他经营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到股权不值钱了,可能要赔本,便以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外资审批为由主张无效。
这使我们产生一些思考,股权转让未经行政审批,如何认定其合同效力?
受物权法关于区分原则之规定的启发,在行政审批与合同效力的关系问题上,我认为最为科学的思路,应该是把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相脱钩,即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依然是有效的,所以应考察其履行情况,区分是否已经报批而作不同的处理:
如果有义务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未履行报批义务的,既然没有报批,自然谈不上批准与否的问题,此时应认为未报批方构成违约,自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如果报批了,行政机关未予批准,应认为合同无法履行,构成嗣后履行不能。
对于合同嗣后不能履行,因各方均无过错,所以互不承担责任。
这样,既可以避免陷入“不报批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就无义务去报批”的怪圈,又可以达到行政管理之目的。
这就行政审批的性质。
行政审批的性质可以归结为行政许可。
未经审批,意味着没有解除对该行为的禁止,具体到合同行为而言,就是不能履行。
比如,股权转让,未经审批,就不能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当事人就不能取得股权。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当事人不能取得股权,就足可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
如果我们的合同法44条是基于这一理念设计的,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便迎刃而解。
问题是,从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看,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是挂钩的。
尽管合同法的规定已经在合同效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现在看起来,在这一点上是令人遗憾的。
在此情况下,我们只能从解释论的角度考虑问题了。
事实上,合同法44条没有断然地规定未经审批的合同就是无效的,而是规定“经审批后生效”。
最高法院颁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
(一)据此规定:
法律规定需审批的合同,未经审批则不生效,从而突破了合同法理论中长期秉持的合同有效与无效的二分法,引入了合同不生效的概念。
现在看来,合同不生效概念,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有重要的价值。
但是司法解释最初规定合同不生效概念时,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有人认为它把问题复杂化了,不生效不就是无效吗?
对双方当事人仍然没有约束力。
但是当我们在后来进一步的去审理一些案件,如涉及到行政审批合同效力的案件的时候,在认定当事人的责任时我们就会发现,规定合同未生效在实务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合同未生效与合同无效不同:
在合同无效的状态下,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约束力,也就是说,对当事人来说,无效合同既无形式拘束力,也没有实质约束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但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合同对双方当事人是有约束力的,不但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擅自解除合同,而且还会发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在股权转让合同已经成立,但因没有办理行政审批而未生效的情况下,不仅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而且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还应履行报批义务,否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如此说来,未生效合同与生效合同的区别又何在呢?
生效合同是指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但在合同未生效的状态下,当事人虽然也要受到合同的约束,但当事人原则上不能直接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因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前提,是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在合同未生效的情况下,当事人自然可以拒绝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义务。
那么,未生效合同的约束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在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的情况下,当事人除了要受到合同形式上的约束,就是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擅自解除合同外,还需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承担相应的附随义务,类似于在附条件的合同中不得恶意阻止条件的成就一样,在附生效条件的合同中,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阻止条件的成就,从而表现为一种作为义务。
例如在股权转让合同中,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在合同成立后,积应极履行报批义务。
一方当事人如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则构成恶意阻止条件的成就,从而应承担违约责任。
基于未生效合同而产生的作为义务是基于诚信原则产生的法定义务,而非合同约定的义务,这是区别生效合同与未生效合同的关键。
由此可见,采取未生效合同的概念,确实能解决未经行政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
一方面,未经行政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不具有强制履行性,当事人不得根据合同请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
另一方面,股权转让合同成立后,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积极履行报批义务,尽快使合同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这样一来,既使得未生效合同与生效合同区分开来,也可以避免将合同认定无效所可能带来的种种弊病,不失为一种妥当的方案。
那么,如何解决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明确规定的关于不经审批股权转让就无效的规定与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呢?
《合同法》第44条只是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审批或者登记才生效的,不经审批、登记不生效。
《合同法》相对于作为行政法规的上述实施条例而言,是高位阶的法律。
何况,中外合资企业法并未明确规定不审批则无效,实施条例规定不审批则无效系对中外合资企业法的扩张性规定。
因此,要优先适用《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
基于上述分析,股权转让合同的转让人既然负有报批义务,法院当然可以据此判令其履行这一义务。
但法院一旦判令其履行报批义务,在实务操作上就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注意到,实践中到行政部门去报批的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而不是合同的相对人。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裁判案件中可考虑把外商投资企业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让外资企业履行报批义务的依据何在?
我想第一点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合同中虽然没有约定外商投资企业去履行这种报批义务,但是法律明确规定由你去做这件事,这就是法律让你承担的一种义务。
另外我也注意到叶林老师的观点,合资企业是投资者设立的独立法律主体,从信托法理论上,其地位相当于投资者投入财产的受托人,应在信托目的范围内履行对投资者的义务,向审批机构申请出资额转让的变更。
因为投资者转让出资额必须经过其他投资者同意,在其他投资者已同意转让的情形下,一般不会发生合资企业拒绝报批的问题。
如果合资企业无故不履行报批义务,投资者有权请求合资企业履行报批义务。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外商投资 纠纷 若干 疑难问题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ocx
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