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兰河传》作品赏析Word下载.docx
《呼兰河传》作品赏析Word下载.docx
- 文档编号:21318390
- 上传时间:2023-01-29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36.77KB
《呼兰河传》作品赏析Word下载.docx
《《呼兰河传》作品赏析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呼兰河传》作品赏析Word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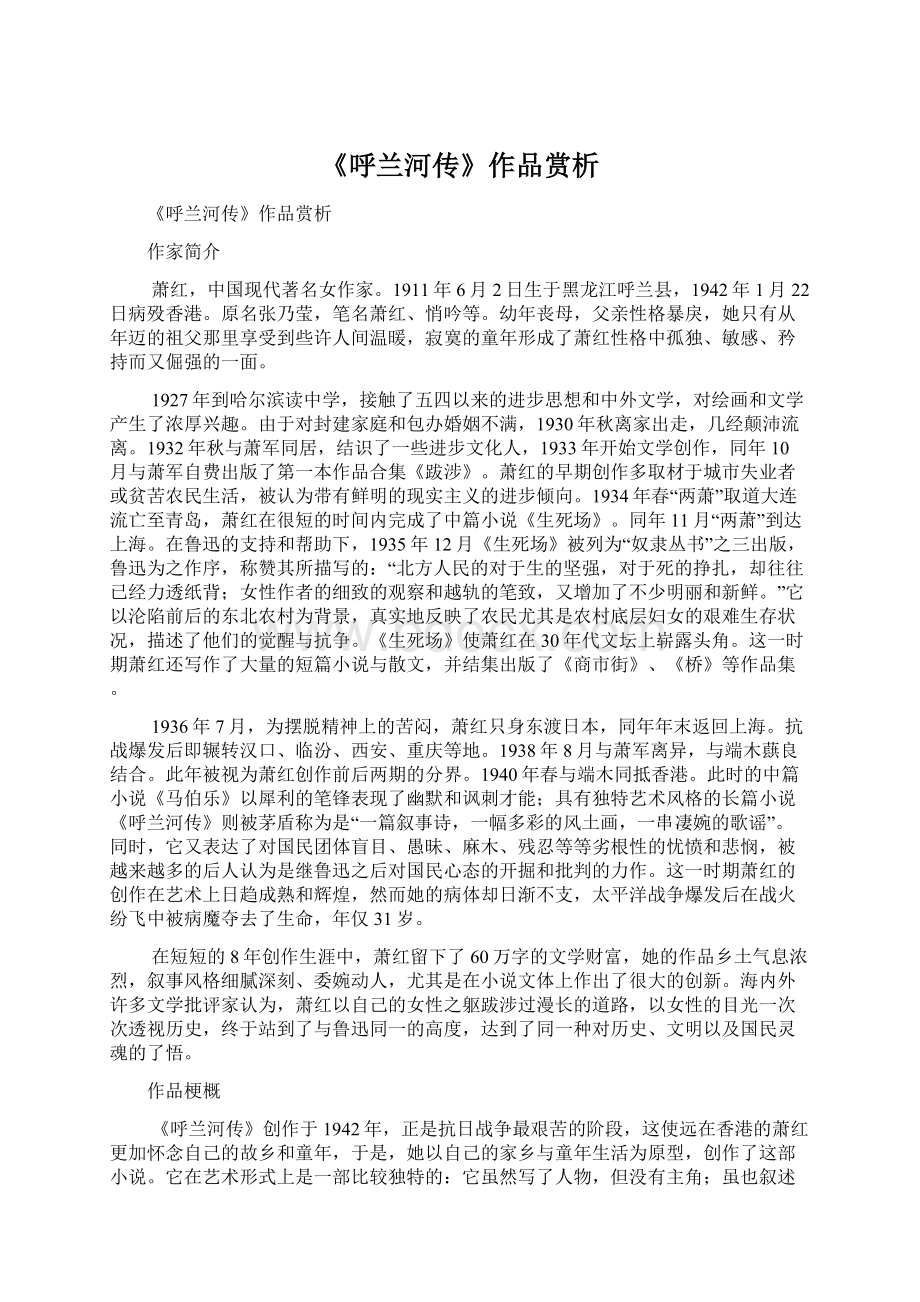
1938年8月与萧军离异,与端木蕻良结合。
此年被视为萧红创作前后两期的分界。
1940年春与端木同抵香港。
此时的中篇小说《马伯乐》以犀利的笔锋表现了幽默和讽刺才能;
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则被茅盾称为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同时,它又表达了对国民团体盲目、愚昧、麻木、残忍等等劣根性的忧愤和悲悯,被越来越多的后人认为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心态的开掘和批判的力作。
这一时期萧红的创作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和辉煌,然而她的病体却日渐不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战火纷飞中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31岁。
在短短的8年创作生涯中,萧红留下了60万字的文学财富,她的作品乡土气息浓烈,叙事风格细腻深刻、委婉动人,尤其是在小说文体上作出了很大的创新。
海内外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萧红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终于站到了与鲁迅同一的高度,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
作品梗概
《呼兰河传》创作于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
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
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
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
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
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
那是一个既僻远又热闹的小城,在城中的交通要道上坐落着一个“大泥坑”,它常常淹死一些骡马和小孩,可居民都在看热闹,没有人出来加以整治。
有的说应该拆墙,有的说应该种树,但没有一个人说要填平的,尽管填坑并不难。
又到了小城举行盛举的日子,人们有跳大神的、唱秧歌的、放河灯的、看野台子戏的、看庙会的,热闹异常。
我的祖父已年近七十,他是一个慈祥、温和的老人,家里面只有祖父最关心我,所以,一天到晚,门里门外,我寸步不离他,他常教我读诗,带我到后花园游玩,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祖孙俩相依相伴,有着无穷的快乐。
我们有几家邻居,西边的一间破草房租给一家喂猪的;
还有一间草房租给一家开粉坊的,他们常常一边晒粉、一边唱歌,过着很快乐的生活;
厢房里还住着个拉磨的;
粉坊旁的小偏房里还住着个赶大车的胡家。
胡家养了个小童养媳——小团圆媳妇。
她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成天乐呵呵的,可胡家想给她个下马威,总是无端打她,左邻右舍也支持胡家的行为,都说应该打。
胡家就越打越凶,时间也越打越长,小团圆媳妇被折磨得生了病。
老胡家听了跳大神的人的话,决定给小团圆媳妇用开水洗澡。
洗澡时,很多人来看热闹,只见她被滚烫的水烫了三次,几天后终于死去了。
我有一个亲戚有二伯,他是个老光棍,性情非常古怪,同人不大爱打腔,却喜欢同石头、麻雀、黄狗谈天。
听祖父讲,有二伯三十年前就到了我家,日俄战征时,多亏有二叔在,才守住了家,他最怕人骂他“绝后”,只要听到有人这样骂他,就会伤心的大哭起来。
人们都管拉磨的那个邻居叫“磨官冯歪嘴子”,他不但会拉磨,还会做年糕。
有一次,我去磨坊买年糕,看到里面炕上躺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原来冯歪嘴子成家了,那女人就是同院老王家的大姑娘王大姐。
然而,冯歪嘴子的幸福生活遭到了邻人们的羡慕和嫉妒,大家都说王大姐坏,谣言层出不穷,冯歪嘴子受尽了人们的冷嘲热讽。
过了两三年,王大姐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因难产死去,冯歪嘴子常常含着眼泪,但他看到大儿子已会拉驴饮水,小儿子也会拍手笑了,他就不再绝望。
在儿子身上,他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文本分析
读萧红的作品,会看到她的人生一直是处在一种非常窘迫的情境中,身世坎坷,漂泊流浪,生活困顿,还有爱情的销蚀破灭……她曾在散文中写道,她有一种“与人间隔绝着般的寂寞感”,她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
她是如此地沉落在现实的生命困境中不得超越升腾,她也虔诚地忠实于独属于她的慰藉生命、展示人性的本真表达方式。
民族、时代是萧红无法摆脱的生存背景,而她所关注的却始终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展示,她的作品所呈现的也正是一个置身于荒野中的孩子似的女人的细致、清澈、凄婉而有时近乎琐碎的感受。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通过描绘呼兰河整体文化氛围的沉滞及个体生存状态的寂寞来表现城与人的存在悲剧,表达生命原始的悲哀,以一种诗化的散文体小说形式传达出独特的荒凉美学况味。
一 整体生存状态的沉滞
《呼兰河传》不是为某一个人作传,而是为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作传,可以说,呼兰城是全书的主角。
小说是一部只有7章的小长篇,作家用两章的篇幅落墨于风土人情,着眼于文化意识心态和风俗意识的视角,从宏观上展示了呼兰城的总体形象。
小城人的生活空间局促、逼仄、简陋,城里除了十字街外,还有两条都是从南到北五六里长的街,再就是有些小胡同,街上为人而做的设施不多———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染缸房,东二道街上唯一的文化设施是两座小学校,西二道街还有一个设在城隍庙里的清真学校。
由此可见呼兰小城的文化产品数量之少、质量、品位与层次之低劣是惊人的。
当然,东二道街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全城引为光荣与骄傲的五六尺深的大泥坑,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
呼兰河人虽然深受其苦,但一直没有想法用土去填平,因为这泥坑子施给当地居民两条福利:
一是“常常抬轿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二是居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吃“又经济,又不算不卫生的瘟猪肉”围绕这大泥沼所映现的世风世相,正是愚昧萎缩的民族性格和精神痼疾的折射。
在呼兰河畔,人们对生活抱着麻木不仁、听天由命的态度,“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
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故乡农民浑浑噩噩的死和无聊寂寞的生。
“在东北,生存的压力是巨大的,生存的意志是人的基本价值尺度,感情的东西,温暖的东西,都被生存的意志压抑下去了,人与人的关系没有了那么多温情脉脉的东西,一切的欲望都赤裸裸地表现在外部。
在精神上,人们感到孤独与荒凉”。
在东北大地上生存的这些愚夫愚妇,只有靠一种坚韧、盲目、简单的承受力来应对外来的灾难和生活的困顿匮乏,对他们来说活着就是全部。
历史文化的惰性封闭着人,人们没有一丝一毫的对生命可能更好的意识和争取,甚至没有对幸福的微茫的想象,只是凭着本能与命运盲动,这里其实深隐着一层浓厚的悲剧意味。
呼兰河人过着卑琐平凡的生活,对生命抱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漠然态度,而在对鬼神的精神依附上他们却又保持着极大的热情———也许正因为对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无知,才促使他们把最大的希望投注在对遥遥无期的来世的关怀上。
呼兰小城有非常齐全的为神鬼服务的设施:
几家扎彩铺、老爷庙、娘娘庙,还有龙王庙、祖师庙、城隍庙……相应的便是异彩纷呈的不少精神上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呼兰河人也就在这些信仰风俗中找到他们的一点卑微的生存的理由和乐趣。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生死场》在审美思考和艺术结构上相接续的潜在的逻辑线索———“以生与死的隐喻结构将作品的意蕴层层递进,以此来把握一个民族灵魂的病态世界”。
在《生死场》中,以人与畜类的骚乱和纷扰反衬人生的木然、乏味和无聊,而在《呼兰河传》中这一主题有了另一样式的接续,在“人”与“鬼”的交织中完成了更为深邃、成熟的隐喻结果。
作品不吝笔墨地写了许多触目惊心但又是无足轻重的生命的消亡:
王寡妇儿子、染缸房里伙计、豆腐房里孩子、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他们生前如同蝼蚁,无人重视,表明那个社会对生命和人的价值漠视到了什么地步。
然而对鬼神就不同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扎彩铺生意的兴隆,送葬祭奠的热烈,为鬼跳神唱戏的火,与对活人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
从呼兰城的群体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来看,这是一个荒诞的以神鬼为中心,见鬼不见人的社会生态环境,呼兰河人呈现出的生命状态的集体无意识显示出他们完全处于“非本真地存在”的沉沦状态之中。
在这里,人们被吞噬了主体性,沦为环境的囚徒,分裂为物的碎片,在一种灵魂沉睡的迷顿状态中忙生忙死。
这似乎造出了一种喧嚣,然而喧嚣中却裸露出这是一片荒原的事实。
二 生命个体的寂寞
《呼兰河传》是为城作传,城与人的命运都在作者的充满悲悯和痛惜的观照中。
作者除了第一、二章摹写呼兰城的民情风俗面貌之外,在后三章中则更多地集中在对故乡农民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切关注上。
在这里,个体的生命价值是一片可怕的空缺和荒芜,他们既不被自己重视,也同时受到他人的漠视和轻贱,从生到死都未有清醒的生命意识。
即使有极个别的人想要做出些微“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年传下来地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姿态和努力,也必将被一种顽固的惯性机制所操控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挤压、封杀。
作者细笔勾勒了几位她童年记忆中的人物,在封建宗法制社会里,他们是没有经济实力、没有社会地位甚至也没有话语权力的城市贫民,对他们来说,生存权从来不是能自主掌控的,更别说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
1、家族之外的零余者
有二伯身处被奴役被蹂躏的地位,十分可怜,但他毫无觉悟,自欺欺人,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东北阿Q。
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竟然没有一点同情,埋葬了小团圆媳妇之后,他连连夸赞“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本来是个扛活的却偏偏喜欢别人叫他“有二爷”、“有二东家”、“有二掌柜的”。
这个“二东家”不敢反抗真正的东家,只能对着绊脚的砖头发牢骚。
他的自我贬损、自我宣泄,都是精神重压下性格异化的表现,充满了喜剧意味,可怜可叹。
但这个人物在萧红笔下通过众多细节的展示,又是非常生动而富于人性的。
他是卑微、寂寞的,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你二伯活着是个不相干……”。
再如,有二伯偷澡盆时“顶着个大澡盆咣郎咣郎东倒一倒,西斜一斜,两边歪着走出后园”的情景,特别是有二伯和“我”在阁楼上偷东西时的巧遇:
他的肚子前压着铜酒壶,我的肚子前抱着一罐黑枣。
他偷,我也偷,所以两边害怕。
有二伯一看见我,立刻头盖上就冒着很大的汗珠。
他
说:
“你不说么?
”
“说什么……”
“不说,好孩子……”他拍着我的头顶。
“那么,你让我把这琉璃罐拿出去。
他说“拿罢。
他一点也没有阻挡我。
我看他不阻挡我,我还在门旁
的筐子里抓了四五个大馒头,就跑了。
光是这一幕情节喜剧就让人对有二伯讨厌不起来。
在这片荒原上,生命就是这样自生自灭,无人理会关心,如蚊虫、如野草般低微、寂寞地生存啊!
还有磨倌冯歪嘴子,生活境遇的局促挤压得他失却了生命的激情,只知道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一套单调乏味的工作。
为了生存,仅仅是为了生存,他一点儿也不偷懒地为东家劳作着,那蒙着眼睛带着笼头的小驴是他的伙伴,他是孤寂的,封闭的。
如果他的存在意识一直处于这种没有记忆、没有时间也不追问意义的蒙昧状态,他也就跟一般的常人无异。
但是当王大姑娘出现在他的生命中时,爱情唤醒了他的生命感觉,他有了一种主动投入生命的激情,尽管这种生命形态仍是极其卑微的。
他此后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深悲巨痛———他的女人死了,扔下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生下来———东家西舍的都说冯歪嘴子这回非完不可了,但他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承受力挺过来了,他有一种找到归宿以后的平静与安宁,他有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混沌但又坚定的信念,带着一种原始的顽强。
尽管他所面临的生活只能带给他一份艰涩的笑,像他刚出生的孩子“又不像笑,又不像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么一咧嘴”,这却是一抹绽放着人性光辉的笑,让人看到一种“反抗绝望”式的挣扎。
2、比底层更底层的悲剧女性
作为女人,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她深深地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缺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关怀的话,那女性总是比底层更为底层的承受者。
如果说日常迷顿状态的生是属于所有这些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么非自然的死则主要由那些善良可怜的女性来承担,而她们的不幸只是因为她们是女性,只是因为她们的身上还带着一丝隐隐跃动的健康而略带野性的生命之光。
在前两章描绘社会风习画时作者已不时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如写到指腹为婚给年轻女子带来的悲剧命运,“不是跳井便是上吊”,而节妇坊上却写着“温文尔雅,孝顺公婆”;
写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作者生动而细腻地描述了老爷庙和娘娘庙的景观。
塑像的男人“把女人塑的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性很不好”。
实际上呢,男像的凶猛“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心服”;
而女像的温柔呢,作者这样激愤地写道:
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负的,告诉人快来欺负他们吧。
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
甚或是招打的缘由。
《呼兰河传》的后面几章在静止般的叙述流程中,展示了两位女性由鲜活到死亡的命运。
小团圆媳妇是个“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姑娘,就因为长得太高大,见人不知道害羞,而且“头一天来婆家就吃两碗饭,又不会看眼色”,不像个团圆媳妇。
于是街坊邻居都“好心”地帮她婆婆出主意,把她吊在大梁上狠狠地打,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将这个健壮的小姑娘折磨得不成人样,于是又跳神赶鬼,最后竟然将她脱得一丝不挂,用滚开的水当众给她洗澡。
小团圆媳妇就这样被活活折磨死了。
还有像一棵“大葵花”一样的王大姑娘,本来在众人眼里是“怪好看的”、“真响亮”、“带点福相”,但是她竟然嫁给了一贫如洗的冯歪嘴子,这在他们看来又是违反传统习惯的事,于是她马上被说得不成样子,“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人给她做日记的。
”她终于在众人的谣言和冷眼中凄惨地死去。
在这里,萧红以她超乎常人的深邃目光,不仅从社会机制而且从文化层面进一步探讨了妇女悲剧命运的深层因素。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并非一个罕见的恶婆婆,只不过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
打出毛病以后,这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婆婆舍得花大把的钱给小团圆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蓄意残害或谋杀媳妇,而那些赞成婆婆行动的街坊四邻更与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让她成为一个“真正的团圆媳妇”。
一句话,打人的人和看打人的人皆出自良善的愿望。
而王大姑娘也只是因为她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这让依照传统意识和习惯而生活的大多数感到好奇以至不安了———在呼兰河城这个锁闭的时空圈子里,民众需要看到一点新鲜,制造一些热闹,但他们却又本能地反对任何改变他们生活的态度和做法,也排挤一切可能的异端。
作品中几乎没有算得上坏人的人来与妇女作对,但她们却又的的确确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状态,成为一出出“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受害者,这是怎样令人颤栗的可悲命运啊。
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分不清是真诚还是残忍,只有历史在阻绝了一切希望、自由、美好、慰藉以后仍无声无息前行。
三 存在的救赎
萧红曾说:
“中国人的灵魂在全世界中说起来就是病态的灵魂”,但是当面对着故乡这些赤裸裸地展现出的荒芜粗野的灵魂时,当她刻写出这种死寂到了失去一切生命的活力、冷漠到了忘记一切生命欲望的似乎万古未变的乡土社会生存形态时,她的感情是异常复杂的,这甚至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几个字所能涵括———愚蠢与残忍是这里的一些现象,所以愚蠢、所以残忍却另有原因;
苦难与死亡被抽空了意义,但在这一切苦难、死亡的背后,却深隐着作者的大悲恸、大绝望。
在《呼兰河传》中作者构筑了一个与荒凉世界完全相对的别样空间———由祖父、“我”和后花园所组成的充满生机和自由的自足的伊甸园,寄托她对温暖和爱的向往,对美好人性的召唤。
米兰昆德拉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诗性记忆”。
萧红的诗性记忆则是关于后园和祖父的。
萧红是一位有着鲜明的孩子气的女作家,在《呼兰河传》的第三章中,她以孩子的眼光看世界,以一种诗性的“越轨笔致”描绘事物,赋予那些无生命事物以生命,赋予那些有生命事物以情感,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纯净、透明、真实的世界,这世界透着一种自在生命的欣喜: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
萧红就这样在赋予万物血肉的同时,从万物的体温中感受温暖,在进入外物的灵魂时进入了自我的中心。
后花园是自由、繁华而充满生气的,在这里,我可以任意地跑,放声地笑,舒展儿童的心灵。
后花园还有那个童心犹存的老祖父跟我一起锄草、摘花,烧掉井的鸭子来吃,念些好听又有趣的诗歌……“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和我,这三样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后花园是一个任生命自在、自然生长的地方,与外界构成了一个空间的二项对立式,映照出外面世界是何等的荒凉、锁闭与冷漠。
然而这个乐园却建立在人生初始的童年,它注定是一个要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逝的伊甸园。
而且这个伊甸园本身尽管一方面是生命可以无限扩展的空间,“愿意怎样就怎样”,另一方面却也意味着是生命被彻底地疏忽、遗忘的虚空,而这几乎是和外面世界有着同质的荒凉意味。
当“我”的视角漫出这个院子,便会触及满目的阴沉昏昧,这个后园只是整个黑暗王国的一抹柔弱的光亮,所以才有文中那反复的叹息声———“我的家是荒的”———在这一声声叹息中,让人感到天荒,地荒,人荒,无处不荒的基调。
茅盾先生在《〈呼兰河传〉序》中认为《呼兰河传》是寂寞萧红的寂寞之作,现在看来这仍不失为一个经典论断。
可以说作者以如此凄婉的笔调写故乡,其意就在于寄托自己的“寂寞”之情,并于“寂寞”中谛视人生,作家的寂寞感决定了作品的荒凉感。
“对于世界中的萧红而言,经历的是一个从初始的伊甸园到生命的荒原的路程,然而在她自己的小说世界里,却呈现了一种从生命的荒原到初始的伊甸园的返回。
”当她这样做的时候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涉入了一条无岸之河,但尽管无法救赦或减免荒原中的生灵与生俱来的命运的惩罚,却足可显出抚慰荒凉人生的人文关怀,因为这毕竟意味着有“永久的对爱与温暖的憧憬和追求”在为世界提供着意义。
有人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许萧红比别人更逼近“哲学”。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凭着她特有的艺术直觉和对民间世界的了解,用一种非逻辑的叙述方式,结合众多富于感性的细节和场景,构建出一个破碎而荒凉的生存空间,透出一种喧嚣的匮乏。
丰富背后的苍白、沉滞,显示氛围本身的深刻性,自然、生动地呈现了对这土地上的人与物所怀着的情感记忆,展现出对世界的一种超然的洞视和混沌的把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和张爱玲是经常被并提的两个特异的存在。
如果说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通过用心的参差对照手法营构一种“苍凉哲学”,传达出对这个正在沉没下去的时代和在这个时代中被抛弃的人的认识,那么萧红则似乎根本无意于做出任何对时代的启示姿态。
萧红所看到的是一个锁闭的时空和一群被彻底遗忘以至于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被彻底遗忘的人的生存,那是一个荒凉颓败的时空,那是一种偏僻粗野的人生。
苍凉的启示是需要背景的,而荒凉的人生则是超乎具体时空的散漫存在的生命的全部,对这种人生状态的谛视和摹写昭示了一种浸润着悲悯和痛惜的“荒凉美学”。
写作特点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作家萧红在生命中最孤寂的时候、在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候,写出了一部引人哀叹落泪的诗一样的小说—《呼兰河传》。
每一位走进这部作品的读者,都会有一个共通的痛彻的阅读感受:
“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何以一位女作家以回忆的方式、平淡的语调、不经意地连级起一些童年生活的片断,竟能令人获得如此的审美感受?
英国作家帕西·
舜洲白克说:
“小说写作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事观点—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运用上。
”视角的运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
虽然有时作者创作时并不自觉地注意视角间题,但其所采用的视角却可以表现出作者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视角的独到运用往往可以导致叙事文体的变异和革新。
它也是读者进人语言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
《呼兰河传》的叙事视角是值得玩味的,既有明显的变化,又有细微间的差别,从中我们能体会到作家在创作时的感情波澜。
这部小说从整体上来看是成年叙述者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顾,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式叙述,目光落在童年的故乡风景、民俗、个人和村民的日常生活上。
在前两章中,是对故乡整体印象的描述,此时作品的视角是高于事件、全知全能的视角。
叙述者对呼兰河的街巷、店铺、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扫瞄,这些是作者再熟悉不过、回忆起来倍感温暖亲切的东西。
叙述者的目光无处不在,她无所不知,这时的叙述也可以说是客观化的、第三人称叙述。
从第三章开始,作品的视角从事件之外的旁观的视角转人了事件参预者的视角,叙述者聚焦于“我”寂寞的童年和荒凉的家。
小说的最后三章,叙述者把目光又一次拉远,身份从回顾往事的主人公转变为处于边缘地位的见证人,对与她相关的人和事进行了聚焦。
这样的联缀表面上看来漫不经心,甚至缺乏逻辑,不符合小说章法。
但实际上,这正体现了作者创作意图与创作情感的矛盾。
“呼兰河传”,顾名思义是为呼兰河这个地方做传,因而叙述者在开篇所选用的视角既可以说是第一人称外视角,也可以说是零视角。
但呼兰河这座小城毕竟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魂牵梦萦的地方,而纯客观的旁观者的叙述方式所产生的叙述效果是不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呼兰河传 作品 赏析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ocx
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