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包围李靖民译Word格式.docx
大包围李靖民译Word格式.docx
- 文档编号:21208755
- 上传时间:2023-01-28
- 格式:DOCX
- 页数:10
- 大小:29.47KB
大包围李靖民译Word格式.docx
《大包围李靖民译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包围李靖民译Word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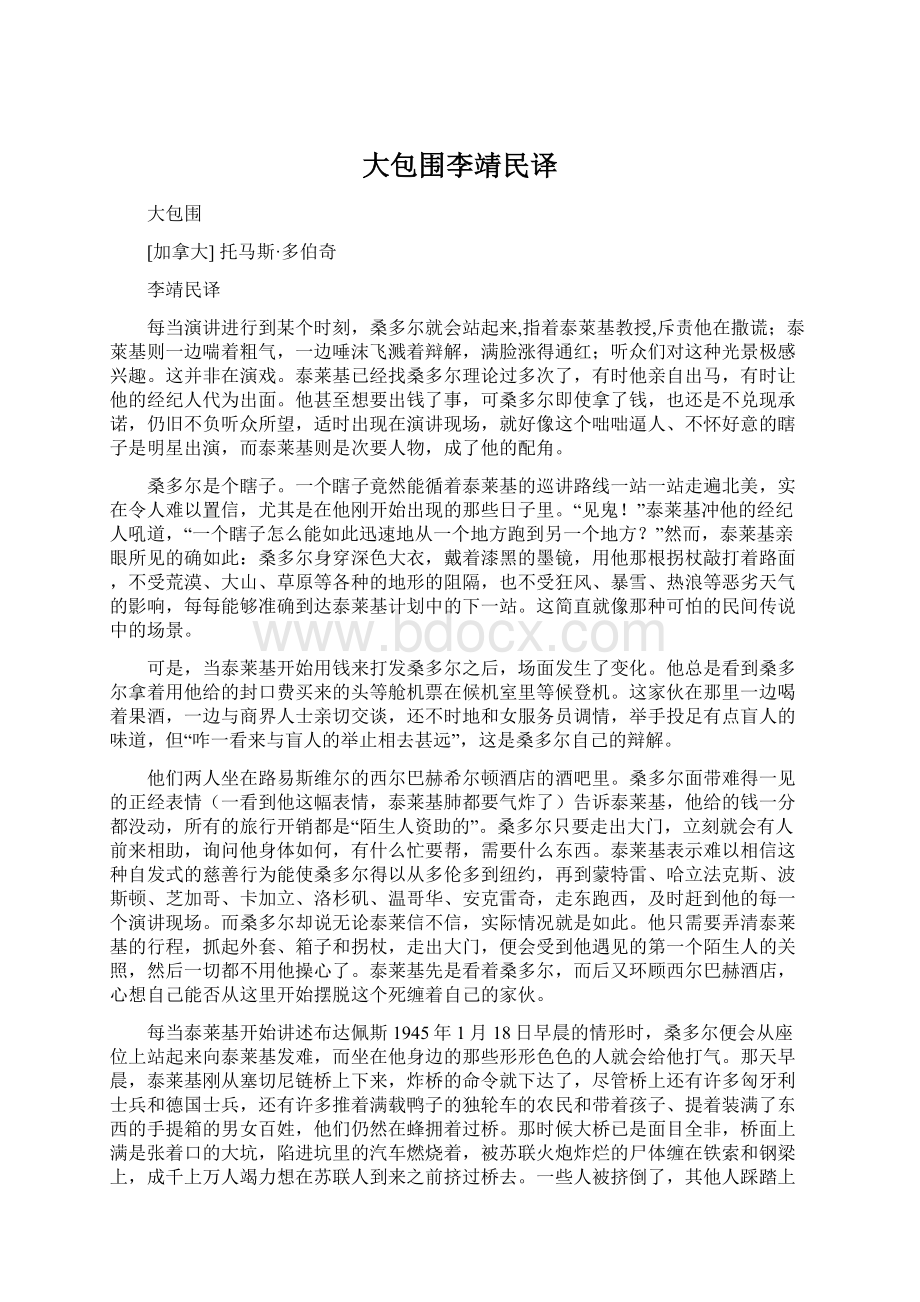
那时候大桥已是面目全非,桥面上满是张着口的大坑,陷进坑里的汽车燃烧着,被苏联火炮炸烂的尸体缠在铁索和钢梁上,成千上万人竭力想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挤过桥去。
一些人被挤倒了,其他人踩踏上去,叫骂声在昏暗的天空中不绝于耳,还有一些人被挤过桥栏掉进冰冷的河水里,被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和机关枪射杀。
在他们身后,在对岸那一半布达佩斯城,围剿仍在继续,大街小巷、建筑物之间飞弹穿梭,一片火海。
泰莱基一讲到这里,桑多尔便会冲着他吼叫:
“告诉大家,你怎样抓住了两个过桥时父母双亡的孤儿。
告诉大家,你怎样把那两个孩子抱在胸前,对纳粹军官说你不能参加反围剿行动是因为你的妻子刚刚死去。
告诉大家,你是怎样在下一条街上把那两个孩子扔掉的。
告诉大家!
”他一边叫嚷着,一边用手中的拐杖指点着泰莱基。
“根本没这回事!
”泰莱基也会冲着桑多尔吼叫。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
听众们此时会起哄、嘲笑、鼓掌,怂恿桑多尔继续说下去。
桑多尔所说总是与泰莱基讲的不同,一到他的嘴里,泰莱基讲的东西便走了样。
当泰莱基讲到自己登上城堡,“志愿”在拉兹罗·
福尔斯沃里中校的麾下参加保卫战时,桑多尔站了起来。
他用旁人递给他的手提扬声器上演了一场高分贝的模仿秀,叙述泰莱基如何在扔掉那两个孩子之后遇到了一个箭十字党士兵。
那士兵见泰莱基是个四肢健全的壮汉,便命他到城堡里去。
“可……可是,我在找吃……吃的东西,”桑多尔用可怜兮兮的腔调模仿道。
“我……我……我把孩子留在那条街上了,正要回去找他们呢。
我妻子,哦,在炸桥的时候死了……”接着,桑多尔发出一阵哭泣声,他把哭泣声模仿得惟妙惟肖,许多听众也冲着泰莱基学桑多尔的样儿。
“可那个士兵还是逼着你上了城堡,对吧?
”桑多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每走几步,他就会往你的屁股上踹一脚,一直赶着你上了城堡。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泰莱基道,他看上去在极力保持平静。
“如果你再妨碍我的讲话,我就要向法庭申请对你的禁制令了。
但是,泰莱基的经纪人却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他认为,泰莱基是通晓二十世纪中欧历史的名教授、多部获奖传记和回忆录的作者、布达佩斯大包围的幸存者,这样有身份的人竟然害怕一个瞎子胡言乱语,那成什么体统。
他还解释说,这样做只会使桑多尔更有名气,而这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
他最后建议泰莱基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演讲,直接面对桑多尔的挑战,因为他毕竟是历史学家嘛。
他甚至对泰莱基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感到吃惊。
泰莱基看了看自己的经纪人,疑惑他是否出席了最近那次演讲。
他难道没有看到那里发生的一切吗?
桑多尔让他丢尽了颜面,而且就在自己本应是权威的现场。
他又看了经纪人一眼,意识到他或许并不希望自己摆脱桑多尔。
这有可能,不,很可能。
他的经纪人其实乐于见到事情像这样发展下去,贪婪地算计着近来“猛涨”的演讲票房收入中他的那一份。
“我的意思是,”经纪人说,“你应该弄清楚桑多尔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查清别人的过去,这不正是你的本行吗?
泰莱基不晓得怎样作答。
那家伙名叫桑多尔·
维斯兰伊,这是他们与他头几次见面时得到的惟一线索。
要想径直走进最近的档案馆,抽出写着这个名字的档案,即可找到从他的出生记录到致盲事故再到他如何决定毕生致力于羞辱泰莱基的所有资料,那是不可能的。
这种调查要花费数年的功夫,就像泰莱基撰写传记和回忆录时收集资料一样。
遗憾的是,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的演讲竟然令听众们“激动不已”,以往的任何演讲都望尘莫及,而泰莱基却因受合同的制约而不得不继续演讲下去。
若是能站在讲台上,等桑多尔再开口,就彻底揭露他,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他肯定第一个赞成。
泰莱基相像着自己在演讲时播放关于桑多尔的幻灯片,他身穿法西斯军服,是个箭十字党成员,最好是昆神父谋杀团的成员。
他们这帮家伙不像德国人那样讲究杀人效率,而是用尽各种手段,只要能达到杀害犹太人的目的,哪怕增加再多的麻烦也在所不惜。
最后,他会给桑多尔致命的一击,揭露他丧尽天良,如何在疯狂搜寻、屠杀犹太人时双目失明,或许就是被他亲手炸毁的犹太人居住区一幢楼房飞起的玻璃碎片弄瞎的,而当时有许多犹太家庭全家人都被困在楼房里。
可是,泰莱基只有关于自己的资料,没有桑多尔的。
他走上讲台,带着黑白幻灯片和激光笔,舌头不听使唤,总感觉与自己的母语相比英语这种语言太蹩脚,表达起来困难重重,妨碍他的演讲,使他显得过于呆板,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桑多尔被两个商界人士搀扶着走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带着仨孩子妈妈,四个穿着老式外套的老人,还有两个做着前刃变后刃半周跳滑冰姿势的家伙。
泰莱基继续他的演讲,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正常,把注意力放在听众身上。
他的听众通常是学术界人士、作家、记者、移民、学生、历史学爱好者和上了年纪的市民。
他指着自己的一幅图片,图片上的他身穿福尔斯沃里驻防部队的军服。
当时,驻防部队正在竭力阻止苏联军队夺取布达城堡,而党卫军和箭十字党的将领们则在这个苏联红军包围圈的中心里搓手顿足,苦思冥想着该怎么做。
到了晚上,一些年轻人(其实只不过是些男孩子)企图乘滑翔机飞跃包围圈,结果被苏联人的高射炮在空中打掉。
泰莱基语气沉重地告诉听众,男孩子们打算降落的地方“Vé
rmezö
”可以被翻译成“血染的草场”。
当桑多尔保持沉默的时候,泰莱基的胆子就大一些。
他向听众们讲述大包围最后几天的情况,讲述城堡里的德国士兵和匈牙利士兵的秩序如何一片混乱,讲述士兵们如何害怕遭到脑袋上挨枪子的处罚而不敢说出的心里话:
为什么党卫军副总指挥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没有把他们带出布达佩斯,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坐以待毙。
福尔斯沃里手下的士兵处境更糟,他们都像泰莱基一样,是被形势所迫加入部队的难民或者罪犯和劳工。
福尔斯沃里随时都会用他手里的马鞭抽打他们,或是在走过他们挖掘并守卫的战壕时在头顶上挥舞马鞭,就好像他四周嗖嗖飞过的苏联子弹是一群群蚊子似的。
福尔斯沃里总是对胆怯的士兵处以死刑,而后又减轻处罚,接着在随后的几天里及其残忍地对待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冲他们喊叫,拳打脚踢。
最后,这些人会从战壕里站立起来,看上去是为了更好地瞄准敌人,而实际上他们那种拿枪的姿势比自杀好不到哪儿去。
他们站在那里,直到半个脸在一阵噼啪声中突然消失,或者后背被炸开,露出红色的肉、紫色的血和白色的骨头。
这种情形令福尔斯沃里感到满意。
他们倒下的时候,他会称赞他们,一边让其他士兵看着他们如何跌倒、跪在地上、脑袋朝后落地,一边说:
“这才是战士,你们这些胆小鬼们听着,这才是战士!
“因此你们就密谋要除掉他?
密谋搞破坏、当内奸、谋杀你们的长官?
”桑多尔站起来质问泰莱基。
“你一定是弄错人了,桑多尔。
“就是你干的。
你在士兵中搞串联,让他们跟你一起干,然后你又出卖他们,去向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告密,说你听到他们在密谋兵变。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离谱的谎……”
“大家看看下一张图片。
看下一张图片。
听众们的视线从桑多尔转向泰莱基。
他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手里拿着遥控器,手指虚放在按钮上,不晓得桑多尔究竟是在虚张声势,还是用某种方式得以操控投影仪,在里面放了另外一套幻灯片。
“让我们看下一张图片,”一个听众喊道,引得大家一阵哄笑。
泰莱基摁了一下按钮,一个画面出现了:
因叛国罪被逮捕的人都在那里,他们是五个遍体鳞伤的士兵,衣不遮体,满脸胡子茬,松散地站在一起,身后是被炮火熏黑的城堡墙。
看上去他们似乎还没有受到指控,正在设法提前逃跑。
泰莱基记得这张图片总是在这里出现的,没有变动顺序。
“就是这张图片。
你当时站在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的左边。
瞧瞧,你就在那儿,肮脏可耻的告密者!
你把所有的同志都出卖了!
泰莱基转过脸去,斜视着那张图片,惊异地发现那个人的确跟他有点像。
三十年前,在经受了七十多天的包围之后,他或许就是这副模样:
面黄肌瘦、惊恐万分、极度绝望。
听众中响起一片鼓掌声。
“那家伙看得见图片!
”泰莱基对他的经纪人说。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你在演讲现场为什么不说呢?
“我说了!
但没人能听见我的话!
他们都在忙着鼓掌!
经纪人耸了耸肩。
“或许他在失明之前看到过这张图片,或许有人给他描述过。
“这不可能,”泰莱基说。
“那么,他怎么对你如此了解?
“他对我一点也不了解!
全是胡言乱语……他在撒谎!
经纪人望着他,一只眼上的眉毛朝上挑着。
“怎么?
连你也相信他的鬼话?
“我只关心票房收入,”经纪人说,脸上的表情很快恢复了正常。
“票房收入好极了,”他说。
“咱们把演出地点换到大点的地方去,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是在‘演出’!
”我是在给人们讲述历史,向他们传授知识。
接下来,泰莱基发现桑多尔的随行人员越来越多,似乎给予他帮助的人不再只是把他送到演讲现场就离开,而是留在那里,好像桑多尔说的话及其说服力使他们接触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一种信仰体系。
“真是不可思议!
”泰莱基心想。
“难道我的演讲需要的就是这种结果?
桑多尔都快要成为一个教主了!
另外,桑多尔现在讲的话似乎比泰莱基还要多。
他不时地用拐杖冲着泰莱基吼叫,支持他的喧嚣声此起彼伏,紧挨着他的那些人发出的喊叫声要比其他听众大得多。
那天晚上演讲结束后,泰莱基意识到自己讲话的时间仅比桑多尔多三分钟。
泰莱基站在酒店的阳台上,连着喝了十二盅苏格兰威士忌,当即决定不再跟桑多尔僵持下去了。
但是,促使泰莱基做出这一决定的因素并非仅仅是桑多尔讲的越来越多,还因为桑多尔讲的内容。
自从与桑多尔这个瞎子发生争执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对大包围的了解是否真的比那家伙多。
不然的话,他最初的猜测就是对的,桑多尔根本就不是残疾人,而是一个复仇的幽灵,一个神话中的人物。
他的眼瞎并非因为他看不见,而是因为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能够窥视一切秘密。
当然,一想到桑多尔撞上柱子或者被座位绊倒时那模样,泰莱基便会笑出声来,打消这个念头。
不过,这个念头总是萦绕不去,令他从睡梦中醒来,苦思冥想,桑多尔怎么会对大包围了解得如此之多,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得知遥远的过去那些往事的。
当泰莱基讲述城堡里最后几天的情形,讲述福尔斯沃里如何命令他们用从国家档案馆拿来的望远镜对着多瑙河西岸的布达观测街道、绘制监测地图时,桑多尔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频频点头。
当泰莱基讲到一连数日城堡里流传着突围的传闻时,桑多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却什么也没有说。
泰莱基战战兢兢地继续往下讲,在二战期间,德国士兵绝不会投降。
他们宁肯战死、撤退,也不愿被俘,因为他们被告知流放西伯利亚是如何恐怖和痛苦,似乎能想象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死亡就是得到拯救。
泰莱基被派去给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送他们绘制好的地图。
讲到这里,桑多尔便开始摩拳擦掌了,等着泰莱基讲述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那天从泰莱基手中接过地图之后说的话。
当时,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直愣愣地望着前方,就好像房间里根本就不存在泰莱基似的,就好像房间里只有他这个党卫军副总指挥,独自面对着难以做出的抉择。
“如果我下达突围的命令,”他自言自语道,“所有人都会死。
此时,桑多尔终于开始插话了。
他模仿着泰莱基的腔调说:
“当……当……当然不会是所有人。
泰莱基把麦克风的声音调大了一些,继续讲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对他说的话:
“很可能第一批死的人中就有你。
“这……这……这样做是正确的,先生,”桑多尔又把他打断了。
“我没有这么说!
”泰莱基把麦克风的音量调到最高,大声喊道。
有人又把手提麦克风递给桑多尔。
“直接面对敌人是正确的,副总指挥先生。
不退缩。
突然,桑多尔开始扮演起两个人的角色,左右交替摆着身子以示是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在讲话还是泰莱基在讲话。
听众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他的表演,对泰莱基的麦克风里传出的反驳声充耳不闻。
“如此一来,”桑多尔说,此时他扮演的是泰莱基,“当士兵们勇敢地去战斗时,咱们就可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通过城堡的下水道离开这里。
“咱们自己应该做的事?
”桑多尔把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厌恶的口吻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这……这不是畏缩,”桑多尔结结巴巴道,再次充当泰莱基的角色。
“这些词属于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他们在意的是自己的声誉,在意历史将如何记载他们。
”桑多尔以泰莱基的身份摇了摇脑袋,“不,我们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对于荣耀的缺乏勇气的向往。
战争需要我们……需要你……活下去。
你必须为了更重要的目标牺牲自己的荣誉感。
”接着,桑多尔用夸张的动作摘掉眼镜,从这边扫视到那边,这是泰莱基站在讲桌后面经常做的动作。
“副总指挥先生,我听到有些士兵密谋杀害福尔斯沃里中校。
因此,在下水道里你需要可靠的卫兵……为了证明我的忠诚,我可以把那些密谋者的名字告诉你。
“于是,”桑多尔接着说道,现在是以他自己的身份(泰莱基对他这种身份越来越习以为常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在突围中丧命,而我们这位朋友,”他指向泰莱基,“却在下水道里淌着污水逃跑。
下水道!
桑多尔对这方面知识的了解也不容小觑。
在匈牙利语中,下水道被称作“Ordö
gá
rok”,即“魔鬼渠”,正好与那些逃亡者的境遇相符。
他们钻进下水道里,污水上漂浮着一个个衣箱、浸湿的卷宗、破碎的文件、被人们丢弃的男女套服,还有一个木质圣母玛利亚雕像。
那雕像面朝下浮在水面上,她的手被另一只手紧握住,那是卡在她身下的一具尸体的手,比她的手小得多。
他们遇到了一些党卫军散兵游勇,便等在那里。
那些士兵顺着下水道的梯子爬上去,推开铁栅,探出头,随即响起狙击手子弹的炸裂声,最上面的士兵应声掉下,其他爬在梯子上的人全都被砸落下来。
他们来到下水道里的分水区,分布在那里的管道一个比一个狭窄。
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命令泰莱基钻进管道里去探路(或者说是桑多尔这么说的)。
一开始他还可以蜷缩着身子往前走,接下来就只能靠膝盖和双手支撑着前行,最后就是贴着肚皮往前爬了,直到他吓破了胆,像虫子一样前胸和肚皮蠕动着一寸一寸退回来,却发现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赫那些人已经丢下他走了。
此时,他遇到了匈牙利军官伊凡·
辛迪及其夫人和两个士兵。
辛迪夫人依然像平时一样,穿着与她身份相符的华丽服饰。
为了使气氛不那么紧张,她不时地与左右两边搀扶她的士兵小声说话,连衣裙的下摆在她的身边飘荡着。
他们看上去聊得很惬意,尽管下水道里前后会不时传来士兵们的尖叫声。
虽然两个士兵搀着她的胳膊肘,但仿佛是她在搀扶着他们,特别是那个一只胳膊上缠着绷带的士兵,仿佛她的说话声能支撑他们继续往前走,仿佛允许他们搀着她就可以给予他们力量。
如桑多尔的叙述所说——泰莱基不得不承认桑多尔讲的东西引人入胜,就连他自己也想听听结局究竟是什么——泰莱基当时不愿听从辛迪的命令跟在后面断后。
辛迪见他面有难色,便提议他走在前面,可泰莱基还是不愿意。
“那么,你想怎样?
”辛迪问。
泰莱基说他想紧靠着辛迪夫人走在中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他们的笑声在下水道的墙壁和水面上回荡,泰莱基开始意识到这些人已经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了,意识到自己被夹在几个笑对被捕、审判、处决的人中间。
“哦,哦,或许咱们可以再推开几个铁栅试试,”他等到笑声间歇的时候,指着下水道的上方说。
“你愿意第一个上去,还是第二个上?
泰莱基说他愿意排在第二个,又引起众人一阵哄笑,只有辛迪夫人例外。
她只是向泰莱基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脸颊。
最后,大家决定由那个没受伤的士兵第一个上去,因为他最胖,需要两个人把他抬起来才能够着第一根梯级。
他的任务是弄清楚外面有没有狙击手,把他们的火力从下水道井口引开,尽可能不要让对方把自己的脑袋打烂。
泰莱基排在第二个,因为辛迪可以一个人把他托上梯子,他上了梯子之后还可以从上面帮忙把受伤的士兵和体型丰满的辛迪夫人拉上去。
最后辛迪再上去。
那个没受伤的士兵拿起一瓶从下水道的水面上捡的拿破仑牌白兰地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向众人点了点头,踩到他们伸出的手上,抓住梯子,迅速爬上去,推开了井口的铁栅。
“咔嗒”,传来一声步枪撞针敲在哑弹弹壳上响声。
大家随声望去,只见那士兵面对着一杆苏联人伸到他眼前的枪筒愣了一下,随即挥起酒瓶朝苏联士兵的脸上砸去,接着一个翻滚躲开枪口和井口。
那挨了一击的苏联士兵晃了晃脑袋,方才起身去追赶那个士兵。
辛迪立刻向泰莱基伸出手去。
泰莱基望着那双手,战战兢兢地把一只脚踩到绞在一起的手指上,挺身向上,一抓住梯子便蹬开了辛迪的手。
只见他吊在梯子上,没有力气引体向上,又害怕落回下水道里,因为这是他惟一的逃生机会。
辛迪和那个受伤的士兵见状哈哈大笑,可辛迪夫人没有笑。
她止住他们的笑声,竭力伸手去帮助泰莱基。
而泰莱基却将他的大靴子径直踩到辛迪夫人仰起的脸上,任凭她的鼻梁骨在自己的鞋底断裂,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只有亡命求生的欲望和冷酷无情。
他一登上梯子,便一级一级向上爬,出了井口撒腿就跑,而剩下的人还在喊叫着要他帮忙把他们拉上去。
讲到这里,桑多尔停顿了一下,正欲继续讲下去,被听众席上冲着泰莱基发出的嘘声打断了。
那嘘声越来越大,直到泰莱基被迫离开讲台。
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泰莱基睡得很香。
要说甘拜下风可以使人异常平静,这不无道理,似乎失去了好胜的欲望可以慰藉失败的伤痛。
可是第二天中午,他再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当时,他和经纪人坐在沙发上,经纪人正在给他看报刊上的新闻、特写和社论,写的都是关于他的演讲如何被“别开生面地搅局”。
与近日里霉运缠身的泰莱基演讲时的遭遇一样,文章作者们对他和桑多尔着墨不匀,厚此薄彼,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找出那个瞎子的任何破绽,他会随时敲打着拐杖出现,发表长篇大论,揭露真相,拆穿骗子的谎言。
在那些文章里,桑多尔是道德高尚的化身,而泰莱基则是个骗子。
“这儿有一篇文章怀疑你们是一伙的,”经纪人一边把一份《纽约时报》推到泰莱基眼前,一边说。
泰莱基扫了一眼那篇文章,平静地告诉经纪人他打算退出了。
“退出?
”经纪人道。
“你不能退出!
“我想我需要消失一段时间,”泰莱基説。
“等事情平息了,咱们再讨论下一步做什么。
“咱们?
如果你退出,就不再有咱们了,”经纪人说。
泰莱基望着他,陡然意识到此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你一直和桑多尔有来往,对吧?
为什么?
你同时做我们两个人的经纪人?
经纪人望着窗外,然后又扭过头来看着他。
“你很清楚这其中的奥妙,对吧?
这叫爆冷门!
“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演讲,”泰莱基从茶几边上站起来说。
*********
依泰莱基的秉性,他若不愿意的话,是不会坚持履行一个合同或此类承诺的,而现在他却发现自己在极力打消逃避的念头。
或许,他是想向桑多尔证明他不是懦夫,不会轻易被赶下台,不在乎向他泼脏水。
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想达到另外一个目的,这需要冒更大的风险。
整个下午他似乎一直在下决心这么做,结果每每心生恐惧而放弃。
自己的这种感觉令他狂怒不已,不止一次见他自言自语,假想与桑多尔争论,每次都让那家伙占尽上风。
然而接近旁晚时分,就在泰莱基即将登上讲台前不久,他终于说服了自己,桑多尔讲的那些东西,包括那个人利用两个孤儿逃避兵役,被普菲费尔·
维尔登布鲁当成炮灰,因怯懦而受到辛迪及其卫兵的奚落等等,并非一无是处,好像即使你讲的东西被颠倒黑白,被指失去了起码的良知(无论是谎言还是事实),或许其中有些东西也能为你所用。
那天晚上,当泰莱基走上讲台站到讲桌旁时,他不再是六个月前第一次遭遇桑多尔或两天前竭力替自己辩解的那个小丑了。
他的身上多了一份严肃,似乎已经到了这一切该结束的时候,即使他的辩解无济于事,他也不会计较得失,一身超脱,不在乎名誉了。
他的眼里满是求生的欲望,这欲望与荣耀或任何其他东西无关,仿佛桑多尔最初站起来打断他的演讲花了五分钟描述的情景再一次展现在眼前:
那是大包围期间最可怕的一幕,士兵们被迫参加数月前就应采取的突围行动,而现在突围几乎与集体自杀无异。
他记得二月十一日那天早晨,当时谣传无线电报务员已经开始销毁自己的设备了;
许多士兵抱有幻想,以为只有匈牙利人在守卫突围点,这些人一见到法西斯士兵就会仓皇逃跑,所以用不了半个小时他们就能穿过无人守卫的空城到达接应他们的德国增援部队驻地;
尤其荒唐的是,他们以为俄国人根本不是运筹帷幄的纳粹和箭十字党指挥官的对手。
泰莱基和桑多尔都知道,当时福尔斯沃里把他的部队带到维也纳门准备突围,在那里遭遇炮击,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行动便被炮弹炸得尸横遍野。
他开始讲述那天的惨剧,竟然讲得与桑多尔一字不差。
没有多少人能够说自己亲眼目睹过那场惨剧——参加突围的二万八千人中幸存者只有不到百分之三。
或许这些人不愿旧事重提,因为回顾那座城市里三公里范围内遭遇的可怕经历需要承受压力,那压力如此之大,比让他们去死还要可怕。
大街小巷炮火连天,熊熊的火焰照亮了天空。
士兵们如同受惊的困兽般尖叫着,昏头转向,他们发现计划中的突围路线到处都埋伏着苏联部队,坦克、火箭炮、狙击兵早已到位,做好了将他们全部歼灭的准备。
他们有的被倒塌的门框压住,有的一瘸一拐地在黑暗中挣扎,有的爬在同伴们被炸掉的胳膊、大腿上央求别人给他们补一枪以了残生。
可是,就连这一点最后的祈求其他人也无暇顾及,前边的人被后面的人推挤着向前涌去。
英雄广场和赛尔·
卡尔曼广场附近的楼房之间堆集着尸体,越堆越高,到处都是炮弹、曳光弹、火焰、装甲车、不断喷出火焰的机关枪口。
城市被毁坏得破烂不堪,变成一座道路不通、难辨东西、生死不卜的迷宫。
泰莱基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演讲大厅里一片寂静。
此时,桑多尔又站起来开始讲话,他的墨镜冲着泰莱基。
“这是你从下水道里钻出来的时候看到的。
这是你们那些人所支持的。
霍希与纳粹签订同盟条约时,你们狂热地支持他,而当他想与纳粹分手而被废黜之后,你们又转而支持希特勒的傀儡萨拉西和箭十字党。
你常说“荣耀!
”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包围 李靖民译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