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逃港成为一种风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当逃港成为一种风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 文档编号:20054467
- 上传时间:2023-01-16
- 格式:DOCX
- 页数:5
- 大小:21.97KB
当逃港成为一种风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当逃港成为一种风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当逃港成为一种风气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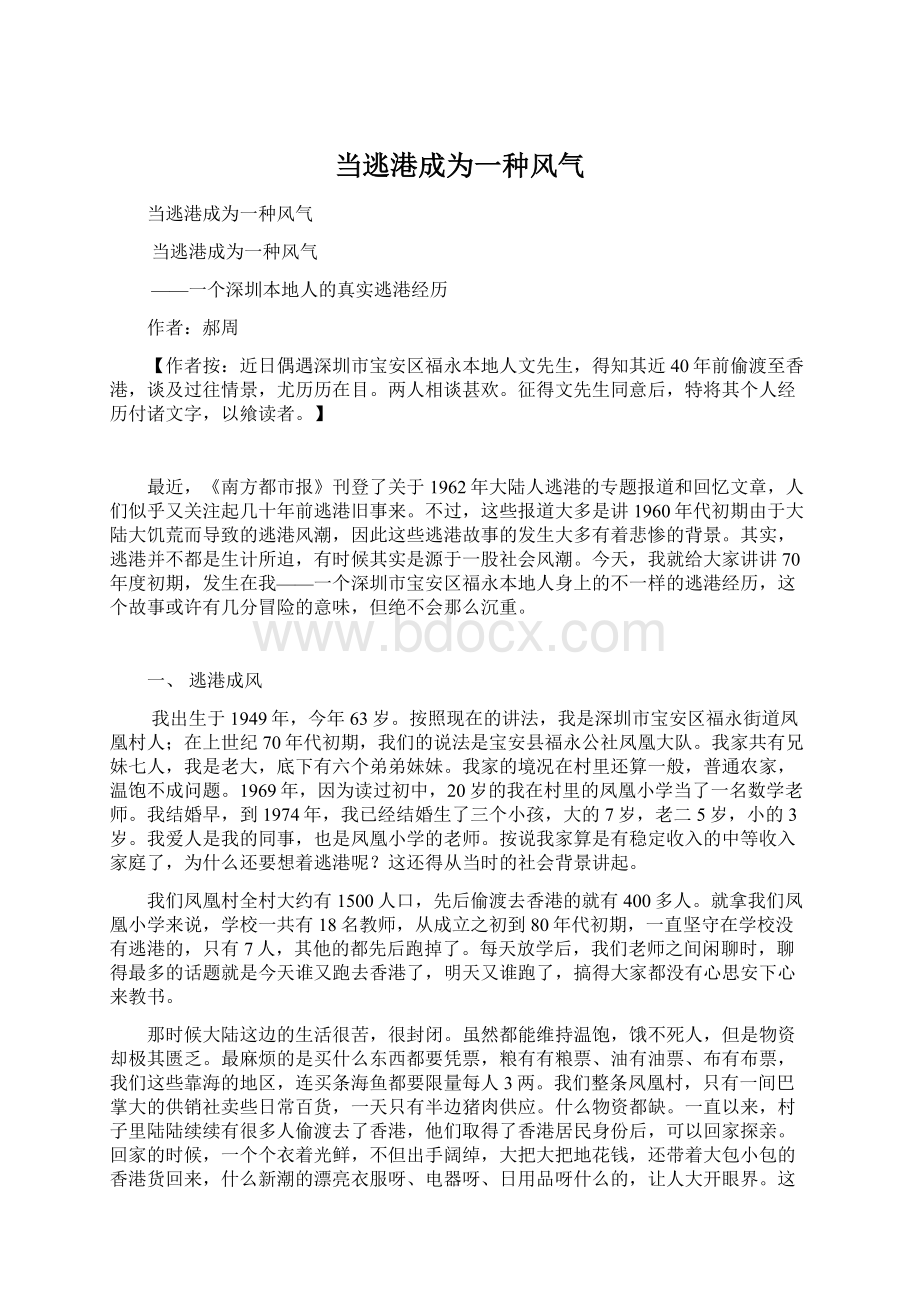
按照现在的讲法,我是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村人;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说法是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
我家共有兄妹七人,我是老大,底下有六个弟弟妹妹。
我家的境况在村里还算一般,普通农家,温饱不成问题。
1969年,因为读过初中,20岁的我在村里的凤凰小学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我结婚早,到1974年,我已经结婚生了三个小孩,大的7岁,老二5岁,小的3岁。
我爱人是我的同事,也是凤凰小学的老师。
按说我家算是有稳定收入的中等收入家庭了,为什么还要想着逃港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讲起。
我们凤凰村全村大约有1500人口,先后偷渡去香港的就有400多人。
就拿我们凤凰小学来说,学校一共有18名教师,从成立之初到80年代初期,一直坚守在学校没有逃港的,只有7人,其他的都先后跑掉了。
每天放学后,我们老师之间闲聊时,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今天谁又跑去香港了,明天又谁跑了,搞得大家都没有心思安下心来教书。
那时候大陆这边的生活很苦,很封闭。
虽然都能维持温饱,饿不死人,但是物资却极其匮乏。
最麻烦的是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粮有有粮票、油有油票、布有布票,我们这些靠海的地区,连买条海鱼都要限量每人3两。
我们整条凤凰村,只有一间巴掌大的供销社卖些日常百货,一天只有半边猪肉供应。
什么物资都缺。
一直以来,村子里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偷渡去了香港,他们取得了香港居民身份后,可以回家探亲。
回家的时候,一个个衣着光鲜,不但出手阔绰,大把大把地花钱,还带着大包小包的香港货回来,什么新潮的漂亮衣服呀、电器呀、日用品呀什么的,让人大开眼界。
这些司空见惯的场面给村里人反复灌输了一个重要信息:
香港是一个可以赚大钱的人间天堂。
郁闷的是,我家没有一个香港亲戚,因此见到或者听说哪个村民的亲戚从香港回来,大包小包地带了许多礼物,羡慕得不得了。
我的许多同学很早就去了香港。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初中同学,姓吴,家在南山区向南村,他1972年去了香港,在香港结婚生子了。
他给我写信,说他一个月能拿2000块港币,我那时当老师一个月才38块人民币,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让我不能不动心。
其实,在逃港之前,我心里十分矛盾。
如果也随大流逃港,最大的好处就是多赚些钱回家,改善一家人的生活。
但是,这样做也是有风险和代价的。
首先,如果半路被抓了,就会被边防武警剃个光头遣送回家,(当时深圳边检对于偷渡的男人,会施以剃光头的人身处罚)更重要的是,教书的饭碗就得弄砸。
这样的例子我们学校之前就有过。
当然,最大的风险来自逃港途中的人身危险了。
因为,我听过太多关于偷渡客在途中被海水淹死或者在山上失足摔死的故事了。
凤凰村有两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后生,他俩从南山区白石洲附近的海滩下水游泳去香港,结果直到今天,无论是香港亲友那头还是深圳家里这边,都没有他们的音讯,那肯定是淹死了嘛。
我还有一个家住南山区的初中同学,他和另外两人自制了一个橡皮艇从海路划船偷渡,本来一路上风平浪静,不料半途中遇到两个游泳偷渡的人,可能是游得筋疲力尽了,见到橡皮艇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拼命地往艇上爬,结果把小艇掀翻了,大家都落水了。
我同学不会游泳,淹死了。
我们村还有一个叫文宝仔的小伙子,他在家排行老七,有六个姐姐。
说来也怪,六个姐姐全都先后成功偷渡去了香港,宝仔游水渡海时偏偏就淹死了,这就是命吧。
我也征求过我父母的意见,他们当时的意思是随我。
其实,我知道,他们内心也希望我去。
毕竟这么一大家子,没有一个人去香港,总觉得在村子里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那时,在整个福永乃至整个宝安,去香港谋生活已经成了一种浓厚的社会风气,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有人逃了许多次,每次都在途中被抓,边防武警今天把他遣送回来,明天他还去,不到香港不罢休。
我们村有一个叫文福财的,先后逃了七次,前六次都失败了,第七次时终于如愿以偿。
我听说更夸张的是邻镇的沙井人。
沙井地域靠海,大多数是渔民,有船,胆大。
他们不是像我们几个人偷偷摸摸地行动,而是公开聚集一群人搭乘一条渔船大张旗鼓地驶向香港。
每次出发之前,他们事先约定某个人这次只管开船,把其他人送到对岸后还得一个人把船开回来,免得渔船被香港警察扣了,损失一条好船。
思前想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教书这份工作,去香港!
二、偷渡、偷渡
我是和我最小的妹妹一起去的。
那一年,她17岁。
我俩的路线很简单:
海路。
交通方式:
划橡皮艇。
这个橡皮艇是我用尼龙绳把8个塑胶充气枕头平铺绑制而成的,与其说它是橡皮艇,还不如说它是救生筏更确切些。
那用什么做桨呢?
简单,带上4只乒乓球拍就行了。
出发之前,我们带了饮用水、猪油糕。
猪油糕是那时常见的一种点心,用糯米、花生、白糖做成的,与饼干有些类似,吃了能顶肚子。
1974年的冬天,接近元旦的时候,我父亲送我和妹妹来到了福田区沙头那片红树林海域。
我们下午抵达红树林后,就一直蹲在密林里,等待天黑行事。
在途经福田上沙附近的海滩时,我们看到一对年轻男女膝盖以下都陷在海泥里,上身挺直,我们还以为他俩脚陷进烂泥拔不出来,等到走进了一看,天哪,眼睛都闭上了,原来人已经死了。
从他们身上灰尘仆仆的毛线衣来看,我猜测他们是从外地来宝安逃港的,可能是迷路了,又累又饿,踏进烂泥里冻得断了气。
我妹吓得直哆嗦,我也惊吓不小,本来有几分兴奋的心情顿时变得低沉起来,我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不测之旅在等待着我们。
等到下午5点多,天黑了,潮水涨了起来,淹没了海滩的烂泥,我俩就把橡皮艇推到海里,两人一前一后爬上去坐稳,朝着事先认准的方向拼命地划去。
我父亲就站在岸边目送我们远去。
一路上,我俩没有遇到边防武警。
现在想想,我俩也真是胆大。
因为我水性不好,只会一点“狗爬式”,而我的妹妹则完全是旱鸭子。
幸好,那晚海面上风平浪静,小艇也没有漏气,否则一旦半途翻船,我俩都得沉入海底喂鱼。
事后,我父亲告诉我,那天我们的“橡皮艇”离开海岸不久,他听到附近传来边防武警的枪声。
他一直为我们有没有中枪或者被抓住而忧心忡忡。
不过,也行是因为距离得太远,也许是因为我俩一心只顾划船,我和妹妹都没有听到枪声。
尽管两岸直线距离不过数海里,也没有什么大风,但海浪还是经常打乱小艇的方向。
我俩一边拼命地划水,一边顺着风向试着调整方位。
划累了,两人就轮流休息。
胳膊肘又酸又痛,仿佛有千斤重似的,也只好咬牙坚持着。
差不多到了当晚午夜,我俩才抵达香港新界的流浮山附近的一个叫尖鼻嘴的小镇。
快靠近海岸时,我俩发现头顶上有直升飞机盘旋,探照灯射过来,在海面划过一片光圈。
我俩吓得赶紧从橡皮艇上翻下来,滚落在又粘又臭的海泥里,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污泥。
我和妹妹赶紧爬上岸顺着岸边的红树林往里跑。
跑着跑着就看到前面出现很多养鱼的池塘。
我突然发现池塘岸边竖立很多长棍子,我觉得好生奇怪,就扔了一块烂泥过去试探。
妈呀,霎时间,许多只手电筒齐刷刷地发出雪亮的光束,直朝我俩照射过来,亮得人都睁不开眼睛。
原来,池塘岸边的斜坡下面蹲了很多手持长棍的巡警哩。
我的脑海里“嗡”的一声响了,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一把抓住我妹的手,说了声“快跑!
”
我俩转身朝海岸边的红树林跑去。
那时的红树林又高又密,钻进去了很难被发现。
我俩身后传来马靴发出的“咚咚”的脚步声,还有人用白话高喊:
“朋友,不要跑,这里有夜茶和夜饭!
呼呼的风声在我的耳边刮着,我和妹妹没命地往前跑,我俩才不理会他们的花言巧语呢。
如果被他们抓到了,结果只有一种——被他们五花大绑后押送回大陆。
我俩钻进了树林里的灌木丛,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远了。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晚追赶我俩的不是巡警,而是港府的雇佣兵,大多是尼泊尔人。
他们手拿长棍埋伏在偷渡客必经之路旁,专门用棍子偷袭偷渡客的腿,要打得你走不动路才好。
摆脱了追捕,我俩开始沿着山路朝内陆方向走。
从在福田沙头下海到抵达尖鼻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个小时。
我俩带的猪油糕早就吃完了,水壶也在路上跑丢了,人又渴又饿又乏,但是我俩丝毫不敢停留,心里只想着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
直到第二天天黑,我俩才摸进新界的一个小村子里。
衣衫褴褛的我俩敲开了一户农家的大门。
一对中年夫妇好心招待了我俩,他们给我俩每人拿来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又端来热饭热菜给我俩吃。
到了深夜,一个男人开着私家车来到这户人家,和屋主聊了几句后,就让我俩上车,说是送我俩去市区。
他把我俩带到元朗,暂时把我俩关在一间黑屋子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男人是专做为偷渡客联系亲友的中介生意的。
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亲戚。
我就报了吴姓同学的电话,我的同学过来了,他为我和妹妹各交了5000元港币的赎金,就带我俩去他家了。
三、身份漂白
到了同学家,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发了一份电报,告诉家人我和妹妹已经平安抵达,家人心头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
我同学给我俩买了衣服,然后就带我俩去市区里的“人民入境事务处”,也就是移民局。
那时香港的政策,偷渡过来的大陆人,如果在边境被发现,就会抓你遣返大陆;
但是如果到了香港市区,你就是走在大街上大摇大摆警察也不管你——你可以光明正大地去移民局申领身份证了。
申领证件的队伍排得很长,有点像电视上看到的春运时期火车站买票的情形。
经过几小时的漫长等待,移民事务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申请表,还给我们拍照,例行问我们姓名,从哪里来的,家里有哪些人。
如果回答是澳门来的,就予以遣返;
要是从大陆来的,则会当场发给你一张临时身份证。
拿了临时身份证,半年后就可以领到正式的身份证和一份身份证明书。
有了身份证明书,你就可以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办理合法回大陆探亲的回乡证了。
我第一次拿的那张身份证并不是永久的,上面盖的是绿印,俗称“绿印身份证”。
只有当你在香港住满七年,才可以拿到“黑印身份证”,也就是永久居民身份证。
在拿“绿印身份证”的头两年内,每隔三个月续期一次,两年后就是两年续期一次。
有了合法的身份,就开始赚钱吧。
当时就是冲着赚钱才来香港的嘛,况且还有5000块港币的“赎身费”要还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楼打杂。
打杂不是做服务生,是比服务生还低级的工作。
拿汽水呀、找辅币呀、收拾碗碟呀、搬货呀……服务生不愿意干的你都得干,而且还得手脚麻利。
当时第一份薪水是1000块港币,尽管辛苦,但比起我在大陆的那份教书工资那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
在第一家酒楼干了一年,我跳槽去了另外一家。
因为有一点经验,在这里我就做起了服务生,薪水也提升到了1600块港币。
后来,我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做服务生需要在外抛头露面,不太好,便转行做起了厨房工作。
我去了第三家酒楼,先从厨房杂工做起,洗菜啦、杀鱼啦、收拾台面啦、把做好的菜端到升降机里呀,反正又重新当起了“小弟”。
由于我生性温和,别人骂我说我,我都不吭声。
大厨们喜欢和我相处,也愿意教我,我便开始学着做菜。
等到学得差不多了,我就跳槽去了一家煲仔饭馆去做煲仔饭、煲仔菜,相当于所谓的厨师助理吧。
当时已是80年代初期,我一个月可以拿到2500块港币的薪水了。
就这样,我在厨师行当一直干到了1989年,做到了一家酒楼的二号厨师,每月拿9000块港币的薪水,算是我打工生涯的顶峰了。
在香港打工的生活压力很大。
人每天过得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没有停歇。
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到14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两天。
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总幻想着等去了香港要去哪些地方好好地玩个够,可人到了香港,才知道事实完全不一样。
每天工作那么累,就是轮到了休息日,也不愿意出去,宁可待在宿舍睡觉。
四、“衣锦还乡”
1975年,拿到了回乡证,我第一次经罗湖口岸坐车回家了。
这里所说的“衣锦还乡”,是字面上的意思。
回家那天,我上身穿了一件时髦的夹克衫,下身穿了一条牛仔裤,脚上还蹬着一双白色的波鞋,这样的装束出现在我的家人面前,比起他们身上那些灰蓝黑绿的粗布衣裳,那真是“衣锦还乡”了。
我也像以前我见过的那些从香港回来的村民一样,背着鼓囊囊的大包小包,一点都不觉得累。
包里装的全都是大陆所买不到的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饼干、水果糖、牛仔裤、波鞋、护肤品、牙膏、洗发水呀,一家老小开心得像什么似的。
听说我回来了,我们学校的同事也跑来看,向我打听香港那边的情况。
一回到家,那些本来还在为“去还是留”而犹豫不决的同事都下定决心要跑出去了。
1979年,小我五岁的三弟也用同样的方法成功偷渡至香港。
1990年,我辞掉了厨师工作,和我三弟合伙在位于港岛东区的北角开了一家做淡水鱼生意的鱼档。
1996年,我爱人办理了教师内退手续,申请移民香港。
时隔22年,我们夫妻终于得以在香港团聚。
2005年,由于行情不好,加之年纪大了,思乡心切,我和三弟盘掉了香港的鱼档生意,正式回深圳定居。
值得一提的是,我妹,当时才17岁的小姑娘,后来在香港和一个同样从深圳偷渡过去的小伙子结了婚。
她现在还生活在香港,过得很好。
她有一儿一女,两个子女都在香港念了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在香港从事金融工作,已经是真正的香港人了。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成为 一种 风气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