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doc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doc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 文档编号:20010869
- 上传时间:2023-01-15
- 格式:DOCX
- 页数:13
- 大小:26.20KB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doc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doc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doc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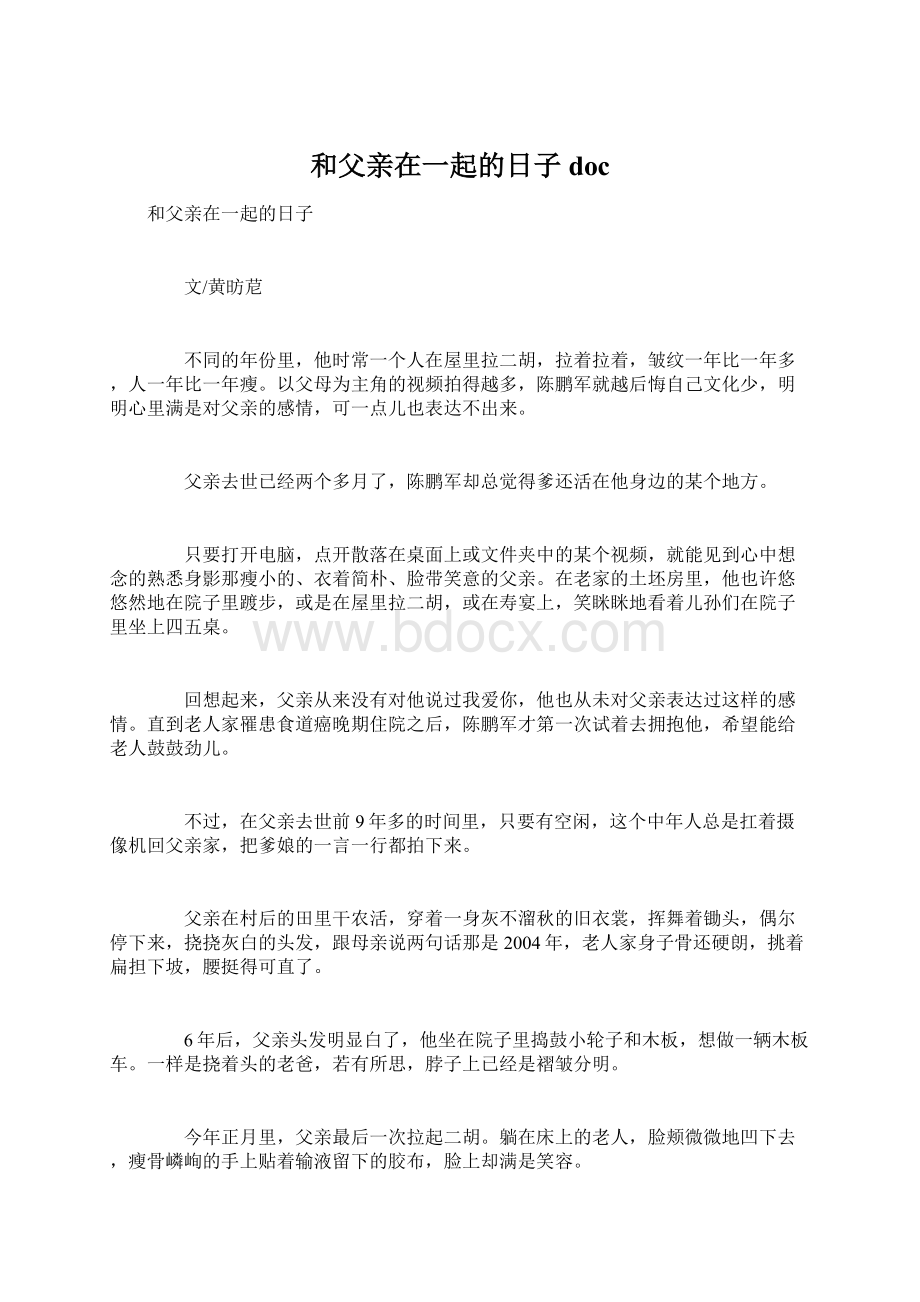
外人要到达洛阳市嵩县的车村镇并不容易。
长途汽车清早从洛阳城出发,驶上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到嵩县已经是中午,但车村还在一百多公里以外。
汽车时而绕着山蜿蜒而行,时而沿着高高的公路桥从一个山头快速驶向另一个。
雾霭萦绕天际,迷雾后青翠的山峦一重接着一重,似乎完全没有尽头。
陈鹏军的父亲陈芸,一辈子都生活在这层层的山峦中。
小时候,陈鹏军常常被父亲架在脖子上,跟着他翻山越岭上班去。
爷俩饿了就吃母亲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窝窝头,渴了就喝山脚下的溪水。
如今想起来,陈鹏军会懊悔当初不懂事:
听父亲说声我不饿,自己就毫不客气地把干粮都吃了。
2004年,也是沿着这样蜿蜒的山路,陈鹏军抱着一台沉甸甸的摄像机回到了车村。
那是一台进口品牌的银灰色标清摄像机,画质能赶得上县城的小电视台,车村街上买不到这样的摄像机,县城里也买不到。
他乘着长途汽车去郑州,从那里的专卖店里取回了这台专门从上海订来的机器。
如果不是前一年父亲被误诊为骨癌,在镇上开设婚纱摄影店、生意正忙的陈鹏军可能不会冒出念头,就为了清清楚楚地拍下父母的日常生活,借钱去买这样一台摄像机。
他刚跟父亲去商量这事儿的时候,老人家也满是不愿意:
为啥要给我拍录像?
拍了录像可以放着看啊。
你不拍,我也好好地在这里,这不一样能看?
父亲不知道曾被误诊为癌症,却也看得出儿子在想啥。
当年,一听到医生说出骨癌这个词,陈鹏军就懵了:
快满40的他刚刚才意识到,年过古稀的父亲,随时都可能离开。
我真怕,要是有一天,我爸离去了,咋办?
哪怕父亲不赞成,他还是下了决心开始自己的拍摄。
买回摄像机的第二天,陈鹏军就扛着它回到了父母家里。
这些近10年前的事情,如今回想起来,还是清晰得跟昨天刚刚发生一样。
那天,二老正在村后的田里干活。
陈鹏军想试试新机器,他刚扛起这个大家伙,手就不由自主晃悠了起来。
摇摇晃晃的镜头对准在干农活的老爸,老爷子的动作也不自觉僵硬起来,讲话都不在平常的调上。
镜头前几步路一走,陈鹏军都快笑出来了。
他把机器一关,对父亲说:
爹,您老就当我不存在就成啦,该干啥就干啥。
重拍的时候,儿子的手还是晃悠,父亲却学会了不看镜头。
这段拍摄于2004年2月、微微晃悠的画面被陈鹏军放在了视频的最前面。
从那天起,陈鹏军就多了一种新的和爹相处的方式。
说起来,陈鹏军第一次见到相机和镜头,就是因为父亲。
那时候陈鹏军才4岁,有天正跟村里的孩子一块儿在一棵大榆树下玩,二姐跑过来说:
快回家,爹要给咱照相啦!
他问姐姐:
啥叫照相?
跟着二姐一跨进院子,陈鹏军就见窗上钉上了一块娘织的靛蓝色粗布,爹在前面摆弄着一个黑色的方匣子,方匣子上有一上一下两个圆圈。
跟着父亲的指挥,姐弟俩在蓝布前坐着,姐姐一手搭在弟弟肩上,父亲按下了快门。
我还在愣愣地看着镜头,心想照相是咋回事呀?
10多年后,少年陈鹏军在父亲工作的嵩县文化馆里又见到了一模一样的方匣子。
他问爹:
小时候你第一次给我照相,用的就是这样的相机,是不是?
陈芸很惊讶:
就是这种120相机,你居然还记得?
我姐姐还大我两岁,她一点也不记得这事儿了。
可我就记得清清楚楚,大概是和镜头有缘。
陈鹏军回忆说。
那时候,是陈芸记录着儿子的成长。
而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儿子扛着摄像机,一路零零碎碎地记录下了他的生活。
逐渐地,逢年过节,全家人都适应了院子里多出来一个扛着摄像机的身影。
大多数时候,老父亲把摄像机视若空气,他闲不住,总在院子里忙这忙那,修修补补。
偶尔回头跟老伴儿说话,目光瞥过蹲在脚边正摆弄摄像机的儿子,流露出几分这孩子在捣鼓啥呀的困惑。
父亲过世以后,陈鹏军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了18盒小录影带和20G的记忆卡,一边看,一边哭:
里面满满的都是父亲。
影像与文章
父亲去世的这两个多月来,陈鹏军把自己拍过的录像看了又看,只觉得到处都是不足。
要是当时跟老爸多讲讲话,现在看片子能听到和老爷子的对话多好?
要是刚开始爹在地里干农活时那些奇奇怪怪的动作没有擦掉重拍,现在看起来该是多有意思?
要是当初好好想想,定好了要拍父亲的哪些镜头,然后一个个去拍上了,今天可能也就没这么多遗憾了吧?
父亲生前,隔三岔五就骑着电动自行车,带上母亲在自家地里种的蔬菜,挨家挨户地送给住在附近的6个儿女。
到80岁的时候,父亲还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母亲坐在车后座上,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
那些年,陈鹏军总想着,下回要拍拍父亲沿着车村街一路过来、带着两兜水灵灵的新鲜蔬菜的样子。
可是时光倏忽这么一溜过去,他到底还是来不及拍下这些心里最怀念的镜头。
为什么这最家常的一幕却没能留下来呢?
也许是因为一直都忙?
陈鹏军想了想,停顿数秒后又断然否认,压根不是忙的问题
以父母为主角的视频拍得越多,陈鹏军就越后悔自己文化少,明明心里满是对父亲的感情,可一点儿也表达不出来。
憋急了,他在纸上写出了很宏大的句子:
每次看到视频中的您,总能感觉到您还活着,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您的一生是那样的勤劳朴实慈祥和伟大,老爸呀,我想您!
他是真的老想起自己小时候。
父亲背着他,翻山越岭,去离家六七十里外的村子里上班。
他坐在父亲肩头,晃晃悠悠,时不时就见老爸从随身的布袋子里揪出一小块窝窝头,递到头上来给自己吃。
六七岁的时候,陈鹏军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好几天都在村里自称是潘冬子,还从厨房里拿个馒头顶着当军帽,跟小伙伴大打一通。
父亲见了,虎着脸问他:
能别糟蹋粮食不?
几天后,屋里多了一顶红军帽,那是父亲做的,不光是灰布做的帽子,还有一颗从笔记本塑料封面上剪下来的红星。
有了老爸的鼎力相助,陈鹏军在村子里的一帮小捣蛋鬼里,就恁跩了。
这些关怀,他没法拍出来。
他能捕捉到的画面,往往是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忙忙碌碌。
在那个用土坯墙围出的十米见方的院子里,种了几排自留地、放着若干盆景,都是父亲摆弄出来的。
父亲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手巧的人。
平常左邻右舍有个什么坏了破了的家具电器,父亲都能修补;
还写得一笔好书法,懂美工,擅乐器,一手二胡如泣如诉。
平时在父亲家吃晚饭,父子俩总有说不完的话。
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年过80的陈芸听说影楼里缺拍古装照时使用的古筝,坚持着非要帮儿子做一架。
您还懂这个?
可别操劳坏了身子。
陈鹏军有点犹豫。
一架古筝得2000多块吧?
费那个钱干嘛,我会做。
你只管把琴弦买来就是了。
两个多月后,爹真的给了他一架古筝。
在儿子惊讶的目光中,他亲手弹奏了一曲,笑着说,乐理都是一通百通的。
镜头里,他认认真真地在这把道具古筝上描出小篆体的琴韵古筝几个字,还在旁边画上两枚印章。
那两年,老人家已经习惯了他的拍摄,逐渐地视镜头为无物。
但儿子却开始觉得,镜头有时候并不足以表达出自己对父亲的感情。
他有时想,要是自己能写出个啥父爱如山这一类的文章就好了。
我心里是真的能感觉到父亲那种爱,真是比山还要重,比海还要深。
唉,这种感觉,我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他挥着手无奈地说。
他通过网络认识了在县城司法局工作的七峰秋庙,还认真向人家请教过:
我不会舞文弄墨,你是文化人,能不能帮我写写?
那时候,陈鹏军拍摄父亲的录像带,加起来就已经有60多个小时了。
七峰秋庙二话不说答应了。
他回忆,当时听说了陈鹏军给老父亲拍录像的事儿,特别感动。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去世后,家人竟怎么也找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来。
但这些约定都没来得及实施,看起来富余的时间,到头来一眨眼就过去了。
七峰秋庙真正看见这些画面,还是今年5月27日。
那天凌晨,陈鹏军在嵩县吧里上传了用整整一天剪辑完成的视频《我的父亲和母亲》。
七峰秋庙看得都流泪了:
我苍白的几句话怎能描绘陈老伯勤劳的一生?
如今,陈芸长眠在老家院子后面的玉米地里。
贴吧里熟识的网友曾特意去陈老伯的坟前鞠躬。
那天下午,陈鹏军与兄弟们一言不发在已长满青草的坟头站成半圈,被视频吸引而来的几拨记者三三两两谈论着如何拍摄、采访网友。
某个时刻,不知是谁带着哭腔喊了一声:
爹,我们来看你了!
一时天地间突然安静,只余风吹过玉米田的作响。
回忆与追悔
扛起摄像机后,陈鹏军留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关的生活画面。
大哥家修鸡舍的时候,爹在院子里劈砖头;
二哥家需要小板车,父亲就找来俩小车轮,乒乒乓乓地把车轱辘锯短了再接上。
干活间隙他喝水,一仰头,脖子瘦骨嶙峋这是老父亲被确诊食道癌晚期前不到两年时留下的影像。
还有更多一家欢聚的时光。
逢年过节,孙子孙女们都回到爷爷家一起吃饭。
小孩子们嘻嘻哈哈闹成一团,有的手上抱着小花狗,眼睛眯成月牙;
有的嘴角还沾着奶油,稚嫩的眼神好奇地瞪着镜头。
老父亲往往在旁边微笑地看着,西斜的阳光打在他脸上,暖暖的。
这种时候,陈鹏军常常用视频线把刚拍下来的画面连上电视机播放,全家人一起看着,边聊边笑。
他注意到,父亲也喜欢看这视频,尤其喜欢看孩子们的镜头。
10年里,老人家常常陪着孙子孙女一块儿玩,也往往在妻子揉面做饭的时候,在旁边帮着生火。
不同的年份里,他时常一个人在屋里拉二胡,拉着拉着,皱纹一年比一年多,人一年比一年瘦。
每一次,陈鹏军拍了关于父亲的视频,迈出小院时,总是祈祷似地想着:
老爸,我下次还要来给你拍。
他知道,父亲心里还有遗憾。
现在想起来,陈鹏军感到特别不是滋味。
陈芸拉得一手好二胡,有时候听着琴声,陈鹏军隐隐觉得,老人家是把自己的心情寄托在了旋律里面。
到了晚年,老爸流露出常常忧心:
爹总得将这把二胡传下去呀!
可是,陈鹏军兄弟几个谁也不喜欢二胡。
去年有一回,看爹对着二胡虎着脸,他忍不住松了口:
好,我学。
老爷子大喜过望:
你说真的?
午饭才吃了一半,父亲急匆匆地把碗往桌上一搁:
吃好了!
随后朝着儿子招招手:
跟我进屋去。
做啥?
不是说要学二胡吗?
父亲在一旁认真地翻乐谱,想找些简单的曲子给儿子练习。
陈鹏军老大不情愿地拿着琴弓,划拉着。
听着儿子没边际叽叽嘎嘎地乱拉,陈芸给二胡一一做上了标记:
拉这儿是Do,这儿是Re,这儿是Mi这个应该这么练习最后,他把手里的二胡递给儿子:
给,你带回去练着。
二胡就放在陈鹏军的卧室里,可他从来也没有正经拿起来练习过。
影楼里的生意很忙,忙起来的时候,陈鹏军十天半个月也未必能回一次家。
我们再也没有说起过这把二胡。
但他知道,老爸只是不说,心里一定很失望。
在媒体上,因为拿着摄像机拍了父亲10年,陈鹏军被人称为洛阳孝子。
他一听到这话就难过。
我父亲已经去世,回头一想,还有那么多遗憾。
父母一辈子太不容易,陪他们的机会也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他把视频传上网,是想提醒认识的网友,趁着父母还在身边,多多关怀他们。
但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孝子称谓让他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痛:
我知道我不是孝子,我做的远远不够,我根本称不起孝子。
小时候,兄弟几个里只有他跟着父亲一起生活。
不用说,他的绣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小书包,是父亲亲手缝的。
每天放学回家,在油灯下,父亲都帮着他温习一遍功课。
我老爸一直很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可是我辜负了他。
上中学时,陈鹏军迷上了摄影,说什么也不愿再读书。
倔脾气一上来,一言不发,直接下地干农活去。
学校来人叫他回去上课,他不听,在屋里给同学写信:
想照相不?
只要买一卷胶卷来,我就能帮你拍照!
一年后,眼看着儿子每天还是琢磨着拍照,牙缝里挤出来的钱都拿去买冲照片的药水,陈芸终于忍不住了:
我帮你开个照相馆,你以商养艺,中不中?
陈鹏军喜出望外:
中,中中中!
照相馆选在车村镇最繁华的街边,父子俩一起造起了房子,添了设备。
照相馆里的道具都是父亲做的,还有30多幅高3米、占了整面墙的幕布背景,也都是父亲在接着10多年里一一画出来的。
父亲去世后,这些往日不在意的小事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如今,在崭新的台北莎罗婚纱摄影影楼里忙碌的陈鹏军总是时不时地想起,多年前,在父亲最初取名为中州的照相馆门前,他满怀歉疚地目送着刚刚搁下画笔的父亲骑车回家,瘦瘦小小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午夜的暗幕里。
老人与大海
如果说这10年里,有什么事儿让陈鹏军想起来觉得并无后悔的话,大概就是带着父亲去看海了。
2012年7月,在洛阳的医院里,陈鹏军被告知父亲罹患食道癌。
医生说,陈芸的生命还能延续半年。
与兄弟姐妹们抱头痛哭一场后,陈鹏军下定了决心:
立刻放下手上所有生意,带老爸去看海趁着最终诊断出来前就出发。
陈芸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伏牛山区。
从前,县里组织旅游,妻子晕车不能离家,他便也在家守着。
后来自己患了心脏病,就更不愿长途旅行了。
但陈鹏军记得,父亲说过,想去大海边看看。
等待另一家医院的检验报告出来还要四五天,反正都要去洛阳拿报告了,不如开远一点,去山东玩一下,看看大海。
他故作轻松地对父亲说。
这一次,陈芸没有坚持。
于是,给母亲备上晕车药,陈鹏军与大哥、大姐护送着父母,驱车一路向东而去。
在日照的沙滩边,陈芸朝着大海凝望了很久。
他与儿子在岸边散步,后来脱了鞋,掠起裤脚,踩着浪花一路走过去。
陈鹏军想扶着父亲,但陈芸在海浪中走着,放开了儿子的手。
突然间,老人家童心大起,一弯腰,用手蘸了海水,再舔舔手指,惊喜地说:
海水真是咸的!
见儿子拿出手机拍摄,陈芸还对他说:
等等呀。
然后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
爹,您真帅。
陈鹏军忍不住跟他开起了玩笑,这哪里是陈芸,简直是陈毅了。
不经意间,他见到老父亲抹了抹眼睛:
真没想到,我80多岁了,真的见到大海了。
陈芸去世的第二天,陈鹏军整理父亲的遗物,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名为《忆今生》的手稿。
手稿写在病历纸的反面,字迹有些涂抹,但装订得整整齐齐。
那是父亲的字:
我家祖居张槐杨家岭,说起来也算一个中等殷实的人家。
爷爷不到六十而亡,父亲忠福,乳名须娃,忠厚老成不识一字。
大约在1927年前后(民国变乱后期)被刀客拉走当小夫,到合峪逃跑至蝉堂,被地方拾住,误为刀客,用铁条烧红火烧臀部,严刑拷问。
后经寡妇奶奶,东抓西借,当了父亲的全部业产(三亩薄地,一间草房),将父亲赎了出来。
子女一直都向老父亲隐瞒着病情,但父亲去世后的这两个月,陈鹏军常常寻思,也许老人早就洞悉了一切,只怕真相令大家崩溃,因此并不戳穿家人的谎言。
日照看海归来,父亲入院接受治疗。
陈鹏军的大姐注意到,每天深夜,借着手机光,老人家总在病床上孜孜不倦地写着什么。
子女们并不知道,黑暗中,陈芸已经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
我于1930年11月初七生于张槐沟平地娘舅家。
和张氏跟前,共生孟良、爱莲、鹏立、爱芹、宁、敏,四男二女。
目前都住在车村,姊妹们四方为邻,亲密无间,有事相商,有难同当,和睦有加。
我已八十三岁,四世同堂,妻贤子孝,一家康乐无比。
我一生的工作鉴定是:
工作积极,勤奋业务,为人正派,团结同志,斗争性较差(指历次反左反右运动,光当动力,不会斗人)。
长音乐,有书法、美术特长,被编入《厚重车村》一书。
罢了!
一句话:
我没愧党,党没愧我,一生走十几个单位总算落个好人的名声,好人一生平安嘛!
大海是我最最想见到的地方。
我一生对啥也不感兴趣,今有幸已过八十二岁,对死亡已有充分思想准备,唯独没见到大海而遗憾。
这次借这个空,我一定要去趟大海,让海水抹去我的过去,冲刷我的现在,洗掉我的遗憾。
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我心里兴奋、激动,感叹人生的短暂。
一个深受孩子们爱戴的父亲,八十二岁的老人,即将与世长辞了!
我留恋而不遗憾,孩子们圆了我的心愿,我不能辜负孩子们的孝心。
这篇近3000字的回忆文章中,六分之一的篇幅都在描述去日照看海之行。
只是,到了看海的这一段,陈鹏军为父亲制作的视频,也已接近尾声。
二胡与棺木
父亲去世后,陈鹏军觉得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说不出来,也不懂怎么写。
他从屋里翻出了近10年来拍摄的视频,看着看着,泪水涟涟。
如果可以,我想再为我爹拍10年,20年。
他跟着作响的录像带回到了2004年那个日光正好的下午,他在田里第一次扛起摄像机对着父亲。
那两年,父亲还养着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花狗。
有回,他把小狗抱起来放在花盆上,小家伙巴巴地在上面望着四周,老爷子看着笑,大家也都笑。
他还想起了总闲不住的父亲,当年在这院子里补补水管,做做小车,甚至捣鼓出了一架古筝。
看到父母在厨房里忙着的镜头,他想起好多时候自己回家,不想吃零食,不想喝饮料,母亲会笃定地说一定又是昨晚半夜才睡,早上没吃早饭吧,便下厨去为他煎最喜欢吃的饼。
父亲在一旁烧火,他把火烧得那么旺,母亲的面还没揉好呢
我父亲,他一辈子为我们子女6个付出太多。
他在世的时候,我没让他少操一天心。
我都几十岁人了,可他对我,爱护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又有什么能回报他呢?
整整一天,陈鹏军坐在卧室里,在电脑桌前翻出那些看似散乱无章的镜头,照着自己的回忆一段段拼接起来。
关于父亲的最后一段视频,拍摄于今年初的某个午后。
那时,老父亲在家养病,在一旁守着的陈鹏军见他看电视也是无精打采,便说:
爹,你给我拉段二胡吧?
我想听你拉二胡。
真的,你想听?
老人眼里闪出了光,不用儿子搀扶,自己在床上坐了起来。
被子软软的,二胡不好放,老爷子嘟囔了一声,调试了两下弦,流畅的乐声便从琴弦上飘了出来。
陈鹏军交叉着双臂坐在父亲面前,手机的镜头悄然地朝着父亲。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拉起二胡,他笑眯眯地,像孩童一样带着期待的目光问儿子:
我(耳朵不好)听不全乎,拉的还像那么回事不?
像,像!
陈鹏军连声说。
转过头去,他的眼泪涌了出来。
听着那咿咿呀呀的乐声,他心里知道,父亲身体虚弱,已经没力气了。
从2004年2月到2013年正月,关于父亲的视频拍到这里,戛然而止。
其实后面原本还可以有一段。
葬礼那天,像从前一样,陈鹏军还带着摄像机回到老屋。
上屋里,小辈们正围着祖父的遗体悲泣。
他本以为自己能稳稳当当地扛着机器,记录下父亲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路途。
但揭下镜头盖后,镜头只是潦草地掠过了上屋一圈,最后落到父亲的遗像上。
这个38秒的镜头就停在了那一刻。
陈鹏军再也拍不下去,他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已经永远过去了。
我爹只给了我10年的时间去拍他,现在我再也没那个机会了。
他能做的,就是把二胡与乐谱,放进父亲的棺木中。
父亲节:
一位老父亲的独白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父亲 在一起 日子 doc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ocx
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教育投资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