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比较.doc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比较.doc
- 文档编号:1890358
- 上传时间:2022-10-25
- 格式:DOC
- 页数:5
- 大小:12.31KB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比较.doc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比较.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比较.doc(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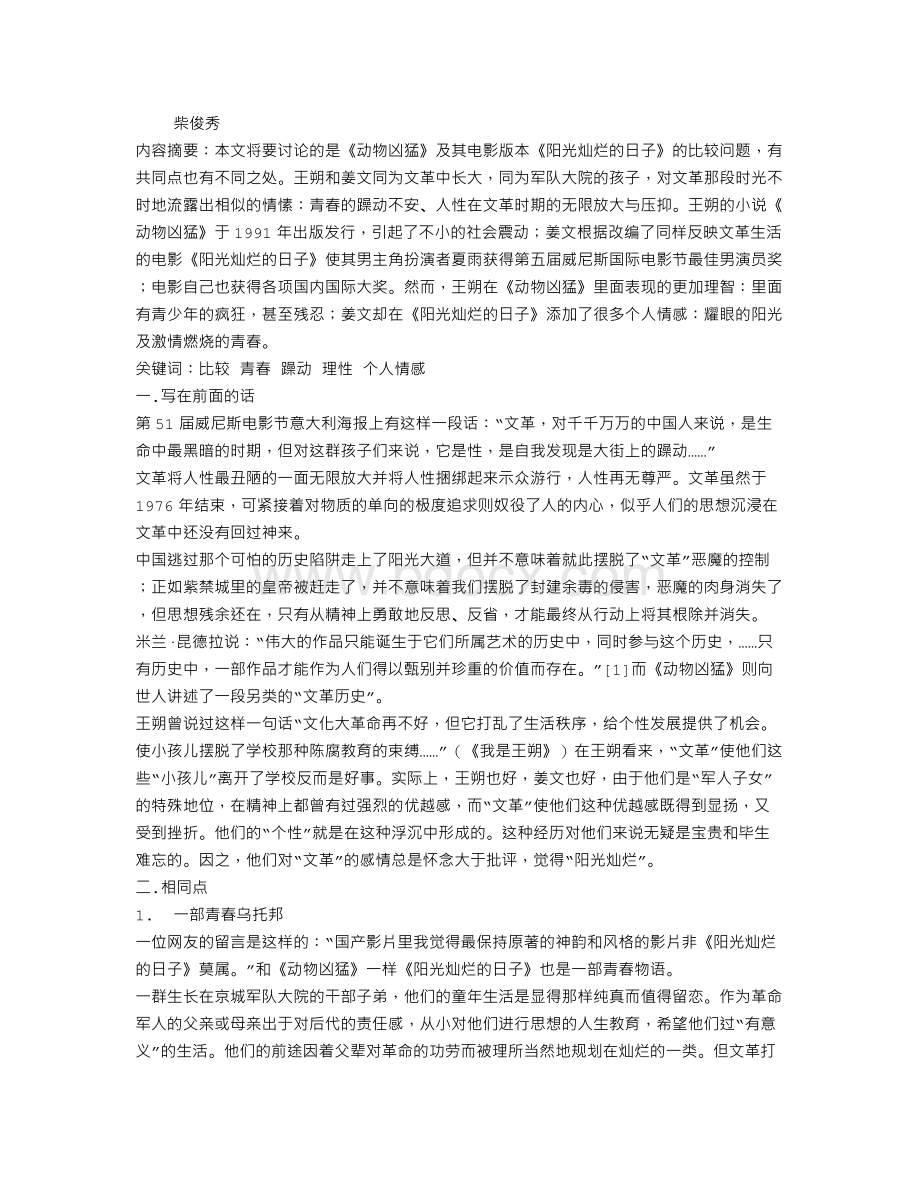
柴俊秀
内容摘要:
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动物凶猛》及其电影版本《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比较问题,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
王朔和姜文同为文革中长大,同为军队大院的孩子,对文革那段时光不时地流露出相似的情愫:
青春的躁动不安、人性在文革时期的无限放大与压抑。
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于1991年出版发行,引起了不小的社会震动;姜文根据改编了同样反映文革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使其男主角扮演者夏雨获得第五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电影自己也获得各项国内国际大奖。
然而,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表现的更加理智:
里面有青少年的疯狂,甚至残忍;姜文却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添加了很多个人情感:
耀眼的阳光及激情燃烧的青春。
关键词:
比较青春躁动理性个人情感
一.写在前面的话
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意大利海报上有这样一段话:
“文革,对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但对这群孩子们来说,它是性,是自我发现是大街上的躁动……”
文革将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无限放大并将人性捆绑起来示众游行,人性再无尊严。
文革虽然于1976年结束,可紧接着对物质的单向的极度追求则奴役了人的内心,似乎人们的思想沉浸在文革中还没有回过神来。
中国逃过那个可怕的历史陷阱走上了阳光大道,但并不意味着就此摆脱了“文革”恶魔的控制;正如紫禁城里的皇帝被赶走了,并不意味着我们摆脱了封建余毒的侵害,恶魔的肉身消失了,但思想残余还在,只有从精神上勇敢地反思、反省,才能最终从行动上将其根除并消失。
米兰·昆德拉说:
“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
”[1]而《动物凶猛》则向世人讲述了一段另类的“文革历史”。
王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再不好,但它打乱了生活秩序,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
使小孩儿摆脱了学校那种陈腐教育的束缚……”(《我是王朔》)在王朔看来,“文革”使他们这些“小孩儿”离开了学校反而是好事。
实际上,王朔也好,姜文也好,由于他们是“军人子女”的特殊地位,在精神上都曾有过强烈的优越感,而“文革”使他们这种优越感既得到显扬,又受到挫折。
他们的“个性”就是在这种浮沉中形成的。
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宝贵和毕生难忘的。
因之,他们对“文革”的感情总是怀念大于批评,觉得“阳光灿烂”。
二.相同点
1.一部青春乌托邦
一位网友的留言是这样的:
“国产影片里我觉得最保持原著的神韵和风格的影片非《阳光灿烂的日子》莫属。
”和《动物凶猛》一样《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一部青春物语。
一群生长在京城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童年生活是显得那样纯真而值得留恋。
作为革命军人的父亲或母亲出于对后代的责任感,从小对他们进行思想的人生教育,希望他们过“有意义”的生活。
他们的前途因着父辈对革命的功劳而被理所当然地规划在灿烂的一类。
但文革打碎了他们红色的美梦,且沦为受人嘲弄的一群。
他们由愤慨而绝望,最痛心的是深深感到自己被欺骗,被父母与师长的红色理想所欺骗,使自己在凶猛的动物世界中缺少利爪,缺少觅食的本领。
从此这一群自以为有高贵血统的人以一种叛逆的姿态蔑视父辈的教育:
打架、玩妞、逃学、说谎、无所事事而高谈阔论,但内心时时不忘自己是“人尖子”,以致一边胡作非为,一边“绝望的无声哭泣”。
《阳光灿烂的日子》片首处有一段姜文/王朔极为个人式的旁白:
“北京,变得这么快!
20年的工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聚集在屋顶上唱俄国民歌的悠悠浪漫,两帮团伙集体斗殴前的惊恐和剑拔弩张,肆无忌惮的调侃嬉戏,半夜假山上明灭晃动的烟头……年轻人的骚动,幻想的神秘,青春期的性好奇,不受束缚衍发的残忍和暴力,不敢正视自己狂躁的内心,时时作践自己和别人……
2.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由一次叙述的游戏,来对传统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进行大胆的质疑,颠覆和解构话语真实性的神话,这是《动物凶猛》/《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叙事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小说叙事人在表述伊始,企图给读者以纯然冷静客观的态度,似乎在求一种巴特式的“零度写作”,引导读者进入其不动声色的叙述状态。
但随着故事在回忆中展开,过去与当下的时间差,在场与缺席的距离感,再加之记忆的叛逆,价值观、现实情感倾向对记忆的深刻抵触,使叙事人在表述中愈来愈感到了一种强制性的扭曲:
越是想讲真话,就越谬误迭出、言不由衷——撒谎成性的话语原来根本无法从技术上还原真实。
尼采所谓的艺术创造历史记忆的深刻二元对立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就在叙事人在对故事的真实性的信心产生根本动摇之后,于是叙述游戏取代了一切关于真实叙述的可贵努力,故事过程被多次中断,叙事人甚至跳出来把读者直接拉入文本,与之一道来完成这场叙述的游戏。
由此,叙事人获得了除去伪装与深度后的轻松和超脱,叙事嬗变为话语的不断挣脱的运动,文本所指随同叙事者一道被流放,叙事故事的过程成为记忆碎片的堆积,整个叙事显得似真似幻,扑朔迷离。
该小说里叙事人大概有两处对表述谬误的质疑和指正。
其一是“我”在米兰家海吹神侃并尽力不去看睡后米兰无意裸露在外的身体,其二是在莫斯科餐厅“我”对米兰进行奚落、捉弄,后又因她和高晋大动干戈。
就叙事的态度来看,故事有着真实叙述的强烈追求,但追求的结果又只能是“一种客观的真实,梦幻般的真实”。
事实上,完全客观的对历史进行重写永远只能是文学/电影写作的神话,对历史的表述取决于叙事人道德叙事规则,故事不是历史,一切关于叙事的真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动物凶猛》/《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故事模糊而又暧昧,于北蓓为什么悄然而去而米兰又突然出现?
是否她们两个本来就是一个人?
马小军同米兰的相识过程真有那么浪漫?
通过刘忆苦才得以认识米兰是否更加准确一些?
众所周知,传统的文学或是电影叙事形态是一种高度缝合系统,故事情节清晰透明,具有稳定感与自足性,读者或是观众在作者所营造的梦一般的文本中来进行感知和解读的。
而作者却有意识的搅乱读者或观众的幻觉感,阻隔着他们完全进入故事情景,将叙述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乃至欺骗性直接暴露在人们面前,电影成了不断破坏和消解自身的文本。
叙事游戏已经使文本再也难以指涉什么意识形态、形而上的意义了。
在谈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姜文说:
“我不能发誓要人老老实实地讲故事,可是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干扰就有多大。
我悲哀的发现,根本就无法还原真实,记忆总是被我的感情改头换面,并随之捉弄我,背叛我,把我搞得头脑混乱,真伪难辨。
”到了末了,他甚至否认电影前面段落的真实性,直称其为伪造的谎言。
王朔/姜文的这种叙述策略使青春记忆更加张牙舞爪,在主观有意识的塑造中,选择或修改到记忆的一个乌托邦——阳光、灿烂、喧闹、欢乐、不负责任、自由自在、初恋的甜蜜或心虚,精力的夸耀,害怕孤单和被人排挤,《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讳言其叙事立场,堂而皇之的略去了青春苦涩的一面,让世人欣赏北京少年擂着胸膛向全世界吹大牛的气魄和纯真。
三.不同点
1.王朔理智但是残酷的讲述一个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我”始终没有名字,这正是作者惯用的手法,随便你把他当成后来的“橡皮人”,或是当成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个顽主形象。
小说把故事的背景放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品中的人物: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北京城里的小青年也普遍深入地兴起了群众性的‘流氓运动’。
‘二本正经’的红卫兵对‘革命运动’渐渐厌烦,开始酗酒,打群架,‘拍婆子’,抢军帽,北京市‘山头四起’。
什么‘三级联防’,‘百万庄‘‘纪委大院’与‘山寨’的‘孩儿们’,横行于市,称霸一方,调皮捣蛋,寻欢作乐。
全北京12岁以上乃至20多岁的青少年不分男女,几乎无不以‘狂’为乐,以‘色’为荣,直到1969年‘老三届’的娃儿们,一窝蜂地被赶出北京上山下乡,然后北京才得以平静……七十年代,随着对当年大孩子的所作所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小字辈的王朔们呼啦呼啦的成长壮大,比哥哥姐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为非作歹,又在北京城卷土重来,只不过规模相对无限性。
”[2]
小说主人公及其主要人物大都生长在七十年代军队大院里,小说采用倒叙形式,由主人公在车站和另一个人物的偶然相遇引出对过去的回忆:
那时才15岁读初三的“我”带着一种浓厚的厌学情绪,因为无聊而养成了用钥匙开别人家锁的癖好。
一天在一个房间里迷恋上一个姑娘的照片并想方设法结识了她,处于虚荣心把她约到自己大院里向哥儿们炫耀,不想米兰却和高晋的关系远远超过了同“我”的关系。
这使“我由嫉妒而变得无法容忍,为了寻找心理平衡,就千方百计挑起事端,捉弄她,侮辱她,谩骂她。
由这种追求施虐和侮辱的快感渐渐形成一种恶性的心理定势,蛰伏在“我”我身上的动物本能成为“我”的主宰,在一种疯狂心理的支配下,“我”终于象完成了一项神圣使命一样庄严地强暴了米兰……
小说名为《动物凶猛》指的就是主人公身上日以增长的具有强烈破坏力的动物本能。
但是我认为,这种本能并不完全等于心理学上所说的处于人的道德压抑下的潜意识本能,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扭曲的,变态的价值观,它通过蔑视正常的人性和张扬人身上某些动物性来同各种世俗传统道德价值对抗。
“我”和米兰的故事揭示了“我”怎样一步步丧失少年天真纯洁的人性而变得“动物凶猛”。
“我”对米兰的感情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开始,真诚依恋阶段。
主人公本质上存在着相当纯洁天真的成份。
例如他刚刚接触于北蓓时,固然也和众人一块比赛说脏话,但是,只剩下他们俩时,还是象一下关了开关,没词了,甚至真诚的善意的关心起于北蓓了。
那时主人公对女孩还是一种神秘朦胧的感觉阶段,并且把这种感觉诗意化。
他初见米兰是可谓一见钟情,只觉“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看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溢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致使我明知道没有花仍有睹视化花丛的感觉。
”和米兰相识以后,几乎天天到她家和她相会,把她脸上的微笑视作深得她欢心的信号。
米兰只是把他当作小弟弟,他这时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不带任何掩饰的。
第二阶段,主人公这种真诚和顽主的价值发生了矛盾冲突。
当顽主是主人公追求的理想。
“真正的顽主是不惮于单枪匹马的”,因此他硬着头皮在大街上拦截米兰。
为了要做顽主,米兰是他通向顽主道路的关键性祭品,他把米兰作为向哥儿们炫耀自己“对异性有不可抗拒的感召力”的标志,但他毕竟还是模仿阶段,还不能像真正的顽主一样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轻易的对待别人。
最后一个阶段:
主人公人性的彻底毁灭。
“我”终于和顽主式的价值方式完全达成了妥协,从此以后,“我便以看待畜牲的眼光看待女人。
”他不顾一切地去强暴米兰:
“我热血沸腾得向他走过去,表情异常庄严。
”主人公完全变得“动物凶猛”。
《动物凶猛》的主人公有以下三个心理特征:
第一、几乎是带着一种英雄意识自觉地趋同于顽主的价值观。
既然不能迂尊降贵去信奉世俗的价值观,中苏开战的幻想虽然伟大,但遥遥无期。
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社会责任感在动荡时代很快地烟消云散,而竞相以比赛玩世不恭和能打能闯为能事。
第二、极其敏感易受伤害和报复心理极强。
例如,主人公有一次去找米兰,没找到,就认为受了骗,有一种屈辱感,其实这只能说是主人过强的优越意识所造成的畸形自尊,以致不能正视现实任何有意无意的不利于自己的细节,并把它引申为对自己的伤害耿耿于心。
第三、使自己处于从来不容否定的地位,而无条件地蔑视自己的对立面。
小说中有这样的话:
“我习惯于从逻辑上贬斥与我奉行准则不同的人,藐视一切非我族类的蹊跷存在,总以为他们是不健全的,堕入乖戾的人。
”正是这种心理作用使主人公丧失了人性的自我检讨的功能。
小说不惜以大量篇幅渲染后来我对米兰的蔑视心理和谩骂情景,其中有着很深的心理学意义。
表面上是由于米兰同“我”的疏远,损失了我的自尊心,“我”只有加倍的看不起她,处处找她的麻烦来安慰自己,但实际上还是主人公内心深处对真诚依恋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动物凶猛 阳光灿烂的日子 动物 凶猛 阳光 灿烂 日子 比较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保育笔记.doc
保育笔记.doc
 幼儿园日常安全检查记录表.xls
幼儿园日常安全检查记录表.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