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的界限文档格式.docx
法律的界限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17900482
- 上传时间:2022-12-12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37.50KB
法律的界限文档格式.docx
《法律的界限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法律的界限文档格式.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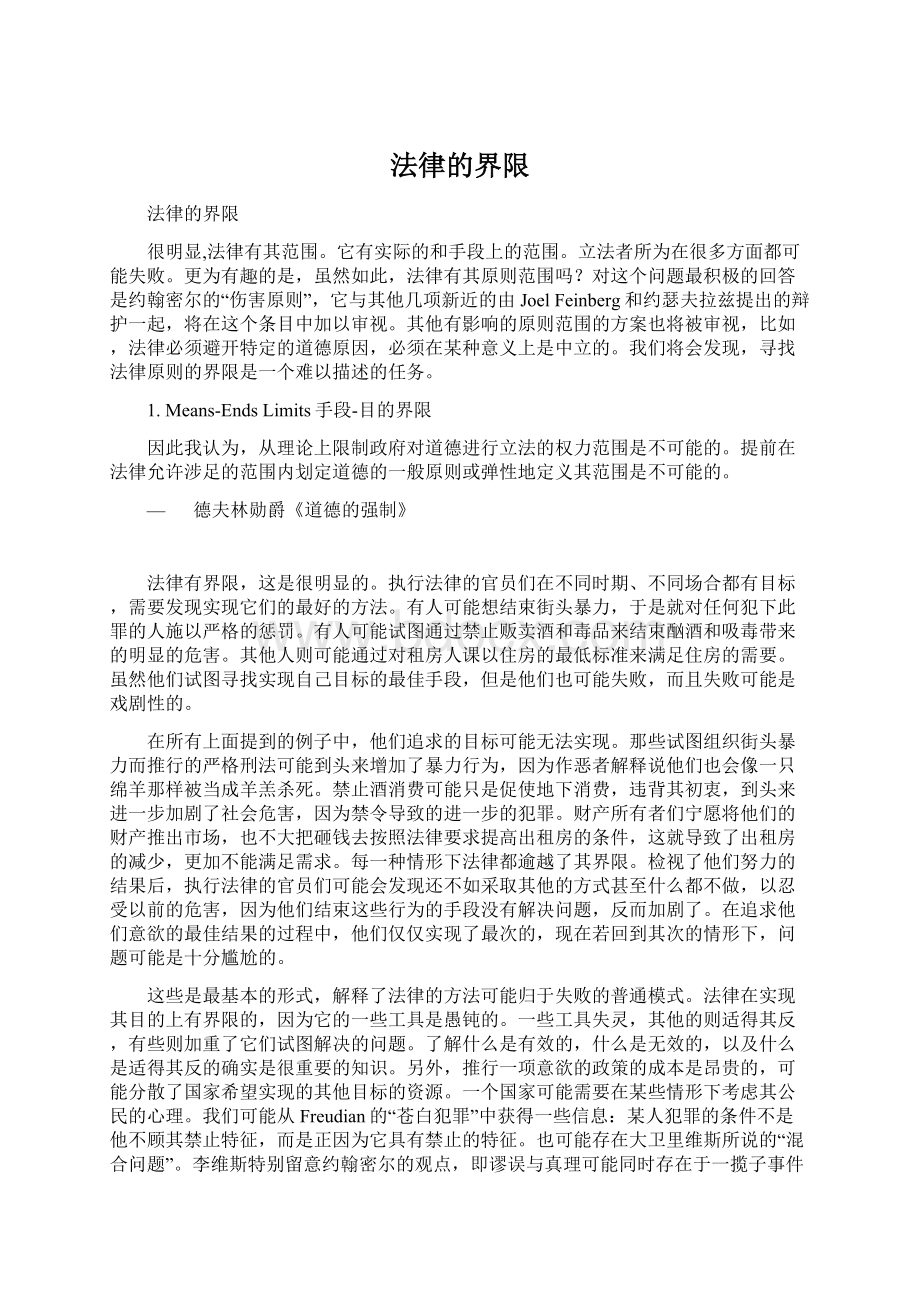
法律在实现其目的上有界限的,因为它的一些工具是愚钝的。
一些工具失灵,其他的则适得其反,有些则加重了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
了解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以及什么是适得其反的确实是很重要的知识。
另外,推行一项意欲的政策的成本是昂贵的,可能分散了国家希望实现的其他目标的资源。
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在某些情形下考虑其公民的心理。
我们可能从Freudian的“苍白犯罪”中获得一些信息:
某人犯罪的条件不是他不顾其禁止特征,而是正因为它具有禁止的特征。
也可能存在大卫里维斯所说的“混合问题”。
李维斯特别留意约翰密尔的观点,即谬误与真理可能同时存在于一揽子事件,所以无法在不阻碍真理的前提下阻止谬误。
但是这个观点可以更加一般地加以阐述:
国家无法在不干扰公民十分意欲追求的行为的同时压制十分不受欢迎的行为。
简而言之法律在其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以及这些工具将会实现的效果上是有界限的。
我们可以称之为“手段-目的界限”或“实践界限”。
法律可以强制,可以制定规则,可以调整,但是只能有这些工具了。
法律必须努力利用这些可能的工具尽可能做好。
法律确实有界限。
它至少存在已经讨论过的手段-目的界限和实践界限。
但是它还无争议,以至于无法成为一个不那么有趣的论断,也没有提出为什么这个话题如此的具有争议性。
我们随后会转向那个话题。
但是,我们必须留意下列实际的界限,因为一种描述法律之界限的可能方式是,这样的界限仅仅是国家必须在立法及更广泛的法律行为时必须加以考虑的,而不是国家必须以一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为的陈词滥调。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的非道德性或者其所追求的目标的价值本身并不是国家强制的充分条件。
当我们提出原则界限的问题时争议就来了。
手段或实践的界限仅仅适用于邪恶或不正义的制度,就像它们适用于合法的制度一样,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
如果我们假设通过其法律的手段,国家必须或应该有建立合法政府的正式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要问法律是否有一个原则的界限?
在本文开始的罗德德夫林的引语中,他否认有这样的界限。
我们将要看到,要应对清晰地阐明原则之界限的挑战,远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任务
争论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正当化国家行为,最普遍的是正当化国家强制。
人们普遍认为行为的非道德性不是国家行为的充分条件,因为我们看到还有手段和实践上的界限。
但是几乎没有共同的根据。
国家是否一定要免于做一些考虑,并从固守派系或什么可以促进幸福生活的有争议理解上挣脱出来?
我认为中心议题是国家对什么是事实的陈述应该求助于道德的前提假设。
如果有人否认在国家通过法律时存在一个原则限制国家求助于道德事实,那么就很难达成一致了。
分歧可以十分广泛和棘手,那么即使理性的人对什么应该做也没有达成共识时,国家此时此刻该怎么办呢?
它能否简单地将有争议的法案当作正确的解决方案加以推行?
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试图在原则上限制国家诉诸于道德论辩,不去考虑基于道德事实的某种意见,困难就是以一种不仅仅基于此的令人满意的方式解释它。
2.CandidatesforPrincipledLimitstotheLaw法律的原则限制的选项
自古至今最著名的解释法律的原则界限的方案是约翰密尔的“伤害原则”
允许人类个体地或集体地干涉他人行动自由的唯一界限就是自卫。
权力可以正确地、违反其意志地施加于文明社会之个人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其伤害他人。
为了他的自身福利,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是充分条件。
密尔认为这个原则最终还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建立在维护人类最为一个进步的存在之永恒利益的基础上。
”他认为这个原则不适用于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社区里的人们。
在已经有足够的进走向文明之进步的社区,保护并促进行动的自由就显得十分重要。
国家应该认识到这种自由的重要性,并且相应地限制其法律。
干涉行动的自由,尤其是以国家权力或强制的方式,要求特别的正当化理由:
它有必要用来阻止他伤害别人,以避免一个人伤害另一个人为理由推行强制当然是一个道德根据。
密尔认为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道德依据。
这个观点一直极具影响力。
表面上看伤害似乎确有一些特别的东西。
将一个结果描述为有害的观点——就像很多人思考的——意味着“从广泛的有利的观点来看它是有害的”。
就密尔而言,伤害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有力论点,对很多“伤害原则”的支持者来说,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被视为特别有有力的,即便不是独一无二的。
对密尔来说,伤害别人有别于冒犯别人,伤害一个人,她可能是自己通常会同意这种伤害并自己加以克制,而行为上完全的不道德,她可能自己也会试图去做。
密尔特别强调安全利益和自治利益。
国家可能合法地去阻止A殴打B,即使它是限制其行动自由,因为它阻止对B的伤害,这就保护了它的安全利益。
它也可能阻止A偷B的东西,它保护了B和其他人依其意愿处分其财产的自由。
但是如果国家一次阻止A打烂自己的财产,或者它保护C不受他知道这种行为之冒犯时,它就逾越了自己的适当的界限了,
最近JoelFeinberg试图证明广泛意义上密尔对法律之界限的理解。
他提出了一个伤害原则的不同形式:
支持刑罚立法的充分条件是,它将有效地阻止(消除、减少)对他人而不是自己(被禁止行为的那个人)的伤害,并且可能也没有不以其他价值为代价的更为有效的手段了。
与密尔的原则相比,这似乎相当无力。
密尔强调的对他人的伤害,是证立国家强制的唯一目标,而Feinberg的公式则更为柔和,它国家强制的“合适的理由”,他宣称对他人的伤害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这使得其可以提出另一个国家强制的合适理由——“冒犯原则”。
支持一项刑事制裁的法案的适切的理由可能是,它对于阻止对他人而不是行为者自己的严重冒犯是必要的,可能会是结束该行为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的话。
虽然密尔称其伤害原则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不包括冒犯在其中,但是Feinberg事实上认为在密尔的语境中可以找到支持其“冒犯原则”的元素,不管这是否正确,他内心的想法是他的主张是值得支持的。
那么如果“伤害别人”和“冒犯别人”都可以构成国家强制的充分理由,那么依Feinberg之见解,还有多少国家强制的充分理由?
在他的四辑关于法律之界限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一种宽泛的答案,尽管也存在一些隐忧:
即简单地说没有政府强制的其他充分理由。
他提出的自由主义立场要求政府应该认识到,合法行为的根据只有上面提到的两条。
如果对别人没有伤害或冒犯,就没有强制。
他承认,虽然还有很多国家强制的充分理由被提出来,但是它们还不够充分或不是合法的理由。
Feinberg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密尔《论自由》中充满生机的精神的忠诚。
某种意义上讲,Feinberg与密尔在个人利益关系的问题上对伤害的理解是不谋而合的。
准确的说,他没有采纳密尔强调“人类作为一个进步的存在之永恒的利益”的观点,他把有害条件理解为对“利益的妨碍”,当这个妨碍是错误的时,就充分的理由加以强制,而不仅仅是在网球职业比赛中失败,或者被对手更优秀品牌挤垮这样的妨碍。
另一方面,Feinberg最急于排除的两种理由是法律家长制和法律道德主义。
前者是这样描述的:
支持对行为者的禁止的充分理由可能是,有必要阻止对他自己的伤害(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或者经济上的)。
可能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了,如果不以其他价值为代价的话。
法律家长制对法律之界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不想说太多,因为它在自己的百科全书体系中有其理论进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Feinberg不是对所有的法律家长制都同样的反对。
它区别“柔性的家长制”和“刚性的家长制”。
在很多的情况下,个人意愿之强制性的履行可以符合个人自治原则。
Feinberg将这种情形描述为“柔性家长制”,并将它们与那些牵涉“刚性家长制”的因素加以对比。
Feinberg反对的是“刚性”的一类,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他人意愿去推行强制。
Feinberg也同样急于否定“法律道德主义”的合法性,因为他是一个(刚性的)的家长制者。
禁止一项行为可能在道德上是合法的,因为其具有内在的不道德性,即使它对比人或自己既没有伤害也没有冒犯。
下一部分我们将集中关注这个伤害原则的对手。
介绍冒犯原则和某些种类的法律家长制作为可能的强制的充分理由,使得所有与这个原则相关的思想家共同支持的“伤害原则”有些误导性了。
我将继续做一些速记性的工作。
下面的表格显示了一些关注伤害原则的主要思想家在法律强制之界限问题上意见的分野。
没有一个与他人有完全相同的结论。
LiberalAccountsofpotentiallylegitimatinggroundsforlegalcoercion
自由主义的法律强制之可能的合法依据
强制的合法依据
伤害别人?
冒犯他人
对自己之伤害
法律道德主义
密尔
是
不
Feinberg
哈特
有时是
拉兹
后面我将转入另一个思考法律界限的方式:
法律必须在善良的不同意见之间坚持中立。
它必须有强制,并且在强制时在这些不同的理解之间保持中立。
3.LegalMoralism法律道德主义
哈特在他的论文“社会连带与道德强制”的开头中这样写到:
我们可能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可能还有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中节录出本篇论文关于法律在推行道德中扮演的角色:
城邦的法律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人们可以在美德中善存,还要明白他们所做之事。
根据这个理论,法律不仅仅是用来惩罚在道德上凡有错误的人,还应该这样发挥作用,因为以这种方式或其他方式推行美德是一个建立了法律体系的复杂社会的目标。
这个理论与一种特别的道德理念紧密联系,这种理念是独一无二真实或正确的一系列原则——不是人为的,要么等着人类依靠理性去发掘或通过探索行为去揭示。
我把这个理论称作“经典命题”,不会进一步讨论它。
哈特即已不厌其烦地陈述了被考虑的问题——国家应该照顾人民使其过上好的生活,并且引用了两个重量级的理论作其支撑,他最后的一句话显得十分突兀。
他将该观点看作:
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依其见解,它有待于理性或探索行为的发掘。
所以它不值得严格的讨论。
它与人为的道德——哈特人为十分值得讨论的——有所区别。
理性基础的、探索基础的和人为的观点都会因其疑问。
道德主义这已经被加了一个无趣的恶名,更坏的是,审问官。
莎士比亚的SirTobyBelch中做了第一种抱怨:
难道你不认为没有艺术道德就没有啤酒和蛋糕吗?
无害的行为带来了欢乐或被一些人做珍视,被道德主义者视作公平的游戏,因为它们无涉道德或不邪恶。
亚瑟·
米勒的熔炉形象是第二个恰当的形式的怀疑:
一个金属在里面加热到极限,融化、精炼的容器。
依其见解,道德主义者就是一个询问官,总是倾向于看到那些没有遵守正确意见的人,将其视为不纯洁,准备进一步地提高温度以净化这些人。
哈特反对的那种法律道德主义是罗德·
德夫林的。
罗德·
德夫林在作应该法院的法官时,反对政府的一项关于成年人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同性恋行为的立法。
这个报告名为“沃尔芬顿报告”,得出结论说在个人道德和不道德之间必须有一个界限,简明扼要地说就是,不是法律要管的事。
德夫林的主要观点是这个理论站不住脚。
密尔当然认为无害行为不是法律要管的事,不管它是否是不道德的,哈特挑战德夫林的目的就是重申对密尔之见解的修饰。
密尔的经典公式伤害原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始于如下的语言:
德夫林虽然十分坚定地反对密尔后面写的文章,但是又似乎同意,“自卫”对他来说,延伸至政府一方的自卫。
依德夫林之间社会部份地是由其道德组成的,因而有权对该道德的任何攻击加以自卫。
因为社会不是以物理的方式结合起来的,而是以无形的共同思想结合起来的。
如果这个结合太松散,那么其成员就会游离出去。
共同的道德就是部分的粘合剂。
这个粘合剂是构成社会的部分的代价,人类需要社会,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社会需要其道德,因其需要政府,于是为了自卫的目的,被授权“使用法律来维护道德,并以同样的方式维持任何对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
”对德夫林来说,沃尔芬顿委员会的见解,有一个道德和非道德领域是法律不管的,这种见解既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简练的,而是彻头彻尾的谬误。
法律必须尽其必须做的去追求社会的代价,这是对社会道德保护。
早先已经说过,德夫林的道德主义是哈特所谓之“人为道德”的一种。
他认为看不见的共同思想这个纽带在不同社会是不同的。
比如一些社会憎恶一夫多妻制,而其他的则人为他对于社会组织来说是有价值的。
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社会构成那个看不见的共同思想纽带。
于是对德夫林来说,在一个社会法律可以被用于推行一夫一妻制而反对一夫多妻制,而另一个社会则可能恰好相反,如果任何一个会威胁到前者的话。
德夫林告诉我们,在工业化社会,一夫一妻制一般会深入每个我们所居住的家庭,非战胜不得放弃。
但这仅仅是偶然的事实,如果我们的家庭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的,那么法律所推行的内容就会合法地与之相反。
对德夫林来说,道德因袭习俗的。
德夫林有关道德的见解是相对性的。
一方面要考虑生活在该社会的普通人的的观点以确定道德的内容;
以德夫林的英语术语即:
应该问及“陪审团”或“克拉彭公交车上的人”的观点。
“在实施刑法时,应该最大限度地容忍个人自由,因其与社会的内在完整性相一致。
”德夫林的著名论断是,容忍的界限不仅仅在于社会的大多数憎恶一个行为。
他说,没有“不存在不宽容、愤怒和厌恶”的社会,这些是道德之法的背后力量,确实可以辩称如果它们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不存在,那么社会的感受不可能有足够的分量去剥夺个人的选择自由。
在20世纪59年代晚期的英国社会,至少可以反驳德夫林的如下观点:
有足够的不宽容、愤怒和厌恶去正当化禁止两情相愿的成年人同性恋行为的刑法
没有什么可以支持德夫林将同性恋解释为“上瘾”或“悲惨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对这个解释赋予太多的理论分量:
对她来说具有理论意义似乎是人群的信仰——由厌恶或麻木不仁的感情所支撑。
如果他今天仍健在的话,也许也会反驳同样的前提假设:
对两厢情愿的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施加刑事处罚是非法的。
在今天的英国社会,没有主流政党会采纳德夫林认为在1950年代广为流传的同性恋观点,或者更适切地说,在德夫林的措辞里,他认为应该会有人投票支持这样的观点。
但恰恰是他自己观点的这个面向使其站不住脚。
伯纳德威·
廉姆斯证明德夫林提出的这个诱人的思想路线,经常是以相关或不相关的观点为基础。
1、行为X是错误的
2、行为X在功能的意义上讲是错误的,易言之,为了该社会的持久存续
3、于是社会S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去维护自己的存在;
它可能采取必要措施压制行为X
但是结论并不是普世适用的。
可能确实如果不采取特定的行动的话,社会将瓦解。
南非的种族隔离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通过推行更为持久的种族主义的中心要素,它成功地存续了更久呢?
这种持续的存在会被道德权利承认吗?
有人有义务维持社会制度的存续吗?
或者当这个社会瓦解后还存在这样的义务吗?
当然,时有些社会欠缺合法性,可能或断然地会瓦解。
德夫林错就错在他说:
“真正重要的不是教条的品质,而是内存与信仰中的力量。
”
依德沃金之见,德夫林理论的谬误在于他没有认清道德论辩是什么。
他指出,当我们做成先决之见,重复别人,理性判断或仅仅表达感情时,我们不是道德性地论辩。
当然,如果有人采纳了德夫林的建议然后搭上了克拉彭的公交车,有时会无意中听到真心的道德内容的交流,其中一些还很坚决,但也有人通过大量的先决之见、理性判断、拾人牙慧甚至仅仅是抒发感情中获益。
德夫林没有给我们导致对其见解产生偏见的东西,这对他来说是很平等的。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德沃金的论断——感情的反应不可能是道德的反应,但是德夫林却挑中一种情感——厌恶,其对曲解特别敏感。
很明显,在为“推行道德”辩护时,德夫林没有一点也没有集中于道德论辩。
德夫林的解释暗示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观点:
一个腐败和不道德社会有很多权利去维持其作为一个体面社会而存在,只要它还能将结合在一起。
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他还对道德做出了一个不令人满意的理解。
它为另一个没有犯这些错误的法律道德主义创造了机会,其正确地看到道德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但也坚持本文开头引用的德夫林的论断:
没有法律不能涉及的道德领域。
他自己的解释没有给出任何清楚的路径,但是他对那些支持伤害原则和其他类似限制原则的人的挑战,显示了禁止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干涉一些道德领域的基础。
4.APerfectionistHarmPrinciple伤害原则的完美主义版本
新近对伤害原则最具影响力的辩护是拉兹的关于对道德的理由敏感性的说明。
稍后我将探讨拉兹对伤害原则提出的基础,但是首先要谈几句密尔这项原则最初的基础。
密尔宣称实用性是所有道德问题的最终诉求。
但是若考虑到密尔对这个问题的其他说法,我们一开始可能会对为什么实用性会支持伤害原则感到困惑。
因为他也坚持实用性原则——“一个行为是正确因为他促进幸福,若导致了不幸则是错误的。
”这个最后的简介陈述似乎在告诉国家在立法时选择要开放,建议似乎是“尽你所能去阻止不幸,去促进幸福”,“如果能够防止不幸就要实行强制来阻止伤害;
如果能够受到同样的效果就要强制另一端。
”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强制阻止无害的错误行为是密尔所否定的,不管这项行为是不是国家认为的最能够阻止不幸。
不要担心无害的错误行为让他人痛苦,也不要担心强制这些坚持该项行为的人会祛除不幸:
国家不可实行强制,不幸必须得到保留。
这里的迷惑锤炼了密尔的大作了吗?
在某些方面没有。
这个困惑所指向的只是需要对密尔的实用主义的正确基础做更好的阐述。
约翰·
格雷认为,因为这里无法再产生一个十分精妙的理论,因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间接的功利主义或结果主义。
总能促进幸福的行为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密尔确实说,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行为只要能够促进幸福就部分的是正确的”,依格雷之见解,这个论断不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如果我们阅读完密尔全部著作其余部分的话。
根据格雷的解释,密尔所提出的是,对幸福成功的最大化必须同时在其直接目标上存在一个对某些方面的禁止:
国家尤其要尊重伤害原则,而不是直接诉诸功利原则。
那样的话,幸福本质上要求对个人自由极大的考量,会得到更好的最大化。
然而格雷自己在其第二本书中却得出结论说,这种妥协是不能成功的。
他给出了很多辩护,其中之一就是宣称上面提出的妥协不能给自由足够强有力的优先性。
确实,在考虑对他人之伤害时,要禁止对自由的限制,密尔的自由原则反对对自由的任何非自由主义的限制,比如说家长制或的到考量。
它之所以反对这些是因为除了讨论中的对他人之伤害,其他的任何考虑,甚至是功利主义的考虑都不能支持对自由的限制。
问题是一旦有自由原则设定的界线被逾越了,甚至是对他人微小的伤害,都会导致对自由实质性的限制。
这个保护为密尔的自由原则提供了优先性,虽然表面上看来很严格,但由于上述原因,实际上是很宽松的。
总结来讲,在多种方式上自由的原则都在伤害原则和功利原则之争后有了定论,功利原则无法确保像伤害原则那样成为自由的原则的强有力原则。
拉兹没有遵循密尔的对伤害原则辩护的功利主义进路。
他采取了道德关的二元价值论,声称:
1、即便国家一方没有追求道德目标的原则限制,
2、也存在追求人民的福利和道德信仰的合法手段上的限制。
在这个辩护上,即使
(1)表面上对道德家们做了很大的妥协,问题还远没有得出结论,因为原则限制可以不通过为了实现法律之目标的手段。
是
(2)而不是
(1)使得拉兹赞同伤害原则。
乍一看,支持
(1)还支持伤害原则似乎很奇怪。
难道确切地要对法律施加原则限制的原则,会排除基于选择的福利或价值的正当化理由吗?
这怎么与宣称国家追求道德目标没有原则限制的论断协调的?
在阐述这个问题之前,还要对拉兹的“完美主义”的深层结构多说说几句。
为了重申
(1)所考虑的问题,拉兹关于道德见解与德夫林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拉兹的道德观是基于理由的。
德夫林的道德观点没有任何关于道德仅仅由特定社会的道德信仰感觉所组成的暗示。
道德是基于理由的,但是拉兹的考量限于存在“自治自重的文化”的国家,其是为了要在该社会生活的更好。
关键在于——正如“自治自重文化”这个短语所指出的——自治。
国家在相关的社会的首要目标在于,促进、保护和培养所有人民的自治。
这要求提供“适当范围内的有价值的选择”,但是“有价值”的质量是这个考量的最重要因素。
国家不需要费心去保护无价值的选择;
它没有义务在人民所追求的选择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
此外,拉兹很清楚自治原则“允许甚至要求政府创在道德上有价值的机会,消除令人生厌的选项”
这个说明对我来说似乎是正确的。
但是在它之下,伤害原则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强制不能被用来消除令人生厌的选项?
在使用国家强制来消除令人生厌的的选项时,注定会出现我们先前所说的“手段-目的界限”或“实践问题”。
强制的使用可能会难以容忍的昂贵,比如说,会严重挤占国家本可以用来促进其他有价值选项的资源。
很可能出现难以克服的“混合”问题:
通过强制手段消除无价值选项增加了同时消除真正有价值选项的可能性。
令人生厌的选项不大可能完全孤立于社会其他有价值选项而存在。
但是现在我们假设所有这些都已经考虑到了,所要付出的代价没有那么高。
是否有某种论辩可以证明为什么国家还是不能使用强制力去压制无价值选项,且不会遇到实践或手段-目的界限的问题?
让我们仔细研究拉兹的论辩。
他的中心论点是伤害原则在自治原则基础上是值得辩护的,原因很简单:
使用的手段,强制干涉妨害了受害者的个人自治。
他解释道:
首先它妨害了独立的条件,显示了一种统治关系和对被强制的个体的不尊重的态度。
其次,刑罚的强制是一个普适性的和不带歧视的对自治的侵犯。
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值得一定的注意。
我将从第二点开始,因为这样第一个问题就会更加清晰地凸现出来。
那么,使用强制力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不偏不倚的对自治的一中侵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法律 界限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