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上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上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 文档编号:17839314
- 上传时间:2022-12-11
- 格式:DOCX
- 页数:10
- 大小:29.20KB
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上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上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上篇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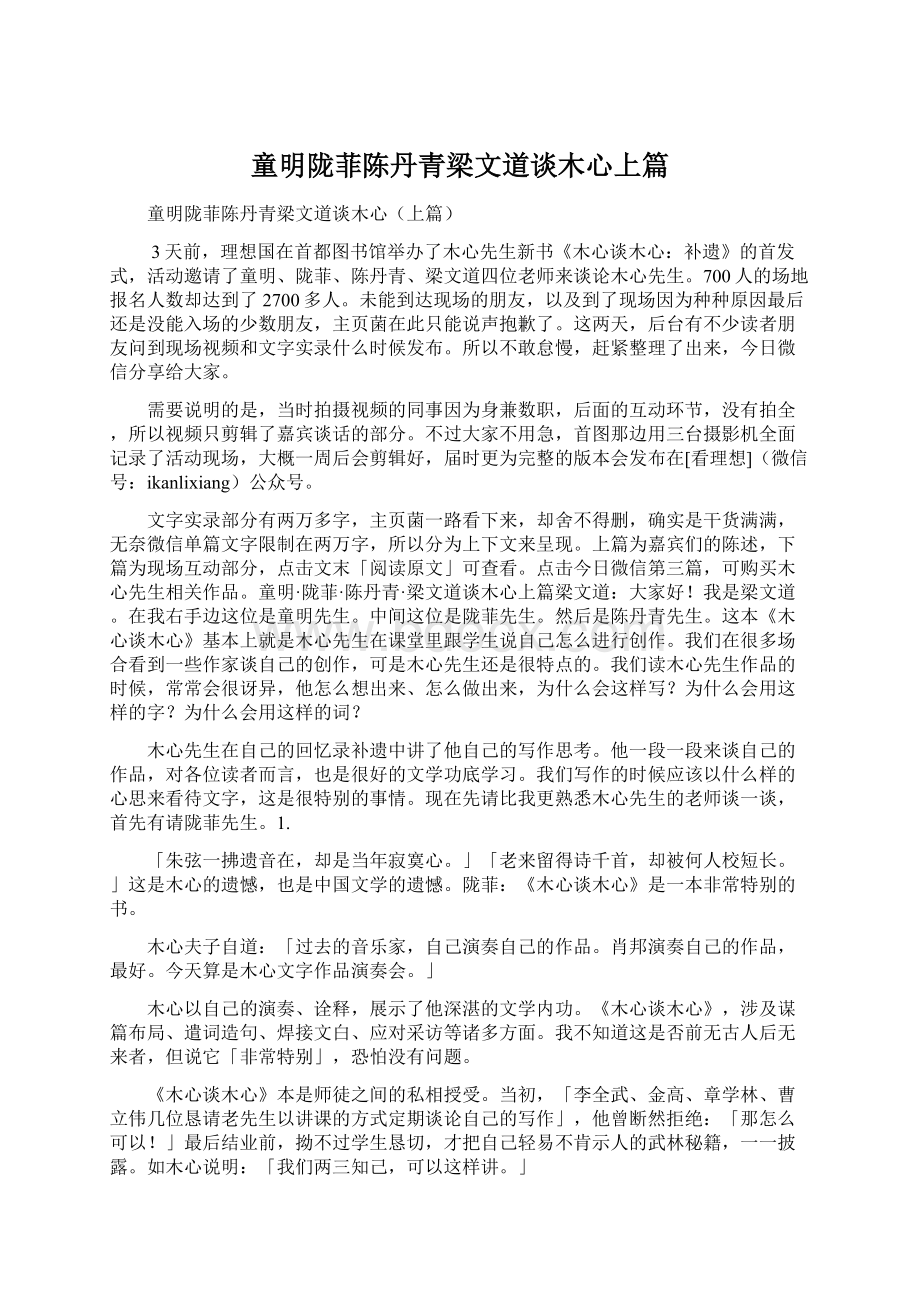
《木心谈木心》本是师徒之间的私相授受。
当初,「李全武、金高、章学林、曹立伟几位恳请老先生以讲课的方式定期谈论自己的写作」,他曾断然拒绝:
「那怎么可以!
」最后结业前,拗不过学生恳切,才把自己轻易不肯示人的武林秘籍,一一披露。
如木心说明:
「我们两三知己,可以这样讲。
」
陈丹青说它是「私房话里的私房话」,私房话公开,便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读者的维度,公众的维度。
从而,《木心谈木心》成为了解木心艺术的另外一个窗口,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窥见此中玄奥。
佛说:
「如以空拳诱小儿,示言有物令欢喜,开手拳空无所见,小儿于此复号啼。
如是诸佛难思议,善巧调伏众生类,了知法性无所有,假名安立示世间。
」这是一切宗教的大秘密,只有佛教揭开了这个谜底。
「空拳诳小儿」,是要「以此度众生」。
《文学回忆录》,主旨关涉「以此度众生」之道。
《木心谈木心》,揭秘如何「空拳诳小儿」之术。
道术不二,相反相成,道统御术,术彰明道。
这两本书,恰成双壁。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曾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名句传世,他的《论诗》说: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莫把金针度与人」是猫教老虎要留一手的意思。
《木心谈木心》,却是「要把金针度与人」。
木心曾说:
「脱尽八股,才能回到汉文化。
回到汉文化,才能现代化。
」与绝大多数大陆文人迥然不同,木心从新八股、党八股的泥沼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了自己,也一个字一个字地救出了汉语。
《木心谈木心》,金针度人,把他的写作秘诀,毫无保留传授给了学生,这是自救而救人。
人生、政治、文学、艺术,既有舞台,也有后台,后台总是不如舞台光鲜。
《木心谈木心》,把自己的「后台公开」,或许有人会略感失望,那是把后台当成了舞台。
其实,《木心谈木心》显豁的,是木心自救救人、自爱爱人的赤子之心。
《文学回忆录》,是识见木心的一扇窗。
《木心谈木心》,是识见木心的另一扇窗。
《文学回忆录》,是教学生如何读书。
读了《文学回忆录》,如果不读他讲过的书,收获到底有限。
《木心谈木心》,是教学生如何写作。
读了《木心谈木心》,如果不修炼文学内功,写不出好作品,也终归无益。
读书难,写作更难。
《木心谈木心》,敞开了他的文学练功房,记录了他作为文学家的心路轨迹。
西汉玄学家、辞赋大家、西蜀子云杨雄曾说:
「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已矣。
」其中「名誉以崇之」,涉及「成就」与「声名」的反馈互动关系。
木心生前,此反馈互动关系,始终没有进入理想的良性循环。
谢谢大家!
2.我说:
「木心先生,我读了你的书,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想跟你聊聊家常话。
」他看着我说:
「喔,那你说说家里都有什么人?
」梁文道:
我没想到陇菲先生说的这么短,这么精简。
接下来有请童明先生给我们讲讲他对这本书的看法。
陈丹青:
我插两句话。
这些年谈木心的场合,大家已经习惯是我这个家伙出来讲。
其实应该童明来讲。
我们两个和木心是将近三十年的老朋友。
可是童明在加州教书,不容易过来。
木心去世以后,他有课,也没法过来,他非常悲痛。
在悲痛时他不能做什么。
这回好不容易请他过来,由他谈谈他记忆中的木心和他对木心文学的看法。
木心在纽约,生活上的事情找我,交税啊、办杂事啊、进城啊,都找我。
文学上的事情,木心从来是找童明谈。
今天请他来谈木心,再合适不过了。
童明:
如果木心先生活着,知道有今天的盛况,晚上给他打一个电话,他会高兴死了。
他是个非常渴望读者却从来不肯在公众场合露面的人。
曾经联系过他在北京露面的机会,到最后还是取消了。
《木心谈木心》这个书名有意思,因为木心通常不肯谈自己。
木心不肯谈木心。
我跟他长期接触,翻译他的作品,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他,好几次都请他比较详细地写一下他的简历。
结果两个星期过去了,给木心打电话,木心说没写。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像写检查一样。
他不肯写。
我从头开始讲。
今天的主题是文学阅读,读木心,思考怎么阅读,真正的文学阅读是什么。
想把这个主题和我跟他交往的回忆片断结合起来。
先讲一下当时是怎么认识木心的。
在座的年轻朋友比较多,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
我是1981年去的纽约,在联合国做译员。
我到了联合国以后,认识了几个台湾的知识分子作家,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郭松棻。
郭松棻是七十年代保钓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博学多识。
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大陆这一代经过文革,是毁掉的一代。
虽然我自己的阅读量可能比别人多一点,但到了国外以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人文知识非常欠缺。
阅读量不够是一方面,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
怎么阅读文学,基本上不懂。
很多次跟郭谈到这个情况。
有一次他问我,你完整的读过《论语》吗?
我说没有。
《易经》呢?
没有。
《道德经》呢?
一问三不知,他说:
「那你还是中国人吗?
」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
从那以后一直在读书恶补。
我现在在加州州立大学英语系做教授,但是最近几年开了一门通识课,叫「古代东亚文学和现代世界」,和学生一起读《周易》、《论语》、《道德经》,还教禅宗、三国文化。
某种意义上,我是想弥补自己的欠缺,也是表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忏悔。
我和郭松棻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4年,我离开联合国去马萨诸塞大学念文学。
有一次回纽约看郭松棻,他说来了一个大人物,我以为来了一个政界的大人物。
他说不是,是一个作家,叫木心。
我说,比你厉害吗?
他说,比我厉害多了。
我看了木心刚出版的《散文一集》。
经郭松棻介绍,第一次和木心见面。
当时人比较多,也比较拘谨,两个人客套一下,没有建立主题。
回去再看他的书,更激动。
木心有首诗叫《那么,玫瑰是一个例外》。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木心是一个例外。
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状态来讲他是一个例外。
我读到木心很激动,阅读西方文学悟到的美学道理在他那里得到应证。
那个时候因为读书恶补,我还懂得一些。
第二次见木心,我坐在他旁边。
我说,「木心先生,我读了你的书,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想跟你聊聊家常话」。
他看着我说:
」我说,「有尼采、托斯陀耶夫斯基、福楼拜」。
大概从那一刻开始,到木心去世,我们就没停过交谈。
有时候在加州给木心打电话,一次打3个小时。
我们聊什么?
木心的话讲得很准确,我们聊文学,聊文学的家常话。
木心回到国内以后,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叫「文学一家人」。
这个思想是一致的。
就是从聊文学的家常话到文学一家人,这是一致的。
今天大家坐在这儿,我就感觉是好像木心还在,我们都是文学一家人中的成员。
木心对他的读者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
我先讲一下,文学一家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
当下有个后现代的理论术语,叫「想象共同体」。
大家虽然不在一起,经常不见面,甚至从来没见过面,但是我们在想象的世界里有共同的价值和追求,使我们成为共同体。
这跟「文学一家人」的概念是一样的。
木心有两句诗,一句是:
「如欲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
另一句,「我是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他期待的是一种理想的读者。
他也在时时打听大家怎么在阅读他。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体会和观点。
木心的文字很美,初次读你就觉得美。
那是美学本身的那种力量。
但是,它为什么美?
不仅仅是词法、句法美。
除此以外还有章法。
章法以外还有剑法。
他的章法变化很多,每一篇都不太一样。
看到他的词法和句法,还要看到他的章法。
还有剑法,剑法分三类:
花剑、重剑、佩剑。
佩剑是欧洲贵族的最爱,佐罗玩的那种。
木心写过一篇论剑的短文,他懂行文的剑术。
把他的文字联起来看,看得多了,就知道除了剑法以外,还有兵法,还有策略。
当然,这是做比喻,把文章跟战争联系在一起。
也可以用酿酒这样的比喻。
木心的文字是经过时间、历史、生活的历练,蒸馏多少次之后的酒,看起来透明无色,实际上非常浓烈。
再进一步讲,文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的艺术。
文字的艺术里面有品质、有情感教育。
最重要的可能还有两点: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这是我跟木心谈得最多的一个题目。
最好的例子,是把修辞思维和逻辑思维重新结合的尼采,成为西方思想史的转折点。
在中国的文化圈里,很少听人说修辞性思维,但木心经常讲修辞性思维。
修辞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是什么关系?
这里面很有学问。
另一点,文学的判断是美学判断。
这也是很大的话题。
所谓美学判断,有别于政治性判断,有别于道德伦理判断。
但是,它并不脱离政治,也不脱离道德伦理。
是特殊的判断。
康德写了三个批判,最后的一个批判「判断力批判」,讲的就是美学判断。
他认为,这是人的各种功能——逻辑、情感、直觉——综合在一起才会形成的判断。
美学判断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判断,它使我们形成惯性的判断悬置,让我们重新学会判断。
伟大的文学我们不断读,总有新的感悟。
木心也是坚持美学判断。
他很喜欢这个词。
我阅读木心获得的喜悦,和我后来接触到西方人对他的评价,感觉到他是多脉相承的一个人。
我们通常说某个作家和传统一脉相承。
木心除了跟中国古典文化一脉相承之外,而且还跟世界性的美学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他真的是多脉相承。
他说是「焊接」,焊接得很漂亮。
他是很会说话的。
他回到国内以后,记者采访他,他说自己是绍兴希腊人。
这并不是开玩笑。
他特别喜欢希腊,特别是希腊悲剧。
西方的两大文化力量就是希腊和希伯来。
希腊之力的美很伟大。
木心为什么说他是绍兴人?
大家知道他生在乌镇。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2002年左右,我到苏州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的课。
临行之前给木心先生打电话。
他说:
你注意一下有两种江南,一种是无骨江南,还有一种是有骨江南。
我在苏州待几个月,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木心先生,我只看到了无骨江南,好像没有找到有骨江南。
他说你这个感觉也许对。
不过你去绍兴了吗?
他说那就对了。
你知道绍兴是有硬骨头的江南。
是啊,鲁迅、秋瑾都是绍兴人。
所以,他说自己是绍兴希腊人,很有道理。
他看起来很温和,但读懂了他,他是有鲁迅那种风骨的。
我今天要谈到一些回忆,还有和他的访谈,当时的经历是怎样。
有机会还想讲一下我翻译他作品的一些回忆。
还是接着主题谈文学阅读。
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审美力削弱的时代。
木心有的时候会怀念十九世纪。
他说,十九世纪的人想象的二十世纪可不是今天这样的。
他有所指。
并不是说现在没有文学作品出现。
到处都是所谓「文学作品」。
恰恰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没有审美,或者缺乏审美。
文学要带我们进入一种兴奋的状态。
但现在的世界,现在的许多「文学」是离开了那种粗俗的、暴力的刺激,就无法进入兴奋状态。
如果你是靠着那些粗俗、暴力的刺激进入兴奋状态的,那不是艺术。
木心特别警惕、特别讨厌这种现象。
在《谈木心》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行文很用心。
他行文时很反对过分的华丽、滥情、炫耀。
他认为炫耀自己是俗。
俗不可耐。
我们常说,疾恶如仇。
木心是疾「俗」如仇,他是绝对不要俗的。
读他作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进入兴奋状态,你应该注意,他恰恰是「避免了粗俗的、暴力的刺激」。
说这句话的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
我跟木心讨论过这个事情。
木心先生在和我的信件来往中,还提到「故实原则」,就是用朴素故实的方法和看似非文学的素材来抒情,而不是用通常的那种浪漫无比的的抒情方法。
木心主张,诗句宜素(朴素),宜静阅。
他是避免高声,避免过于华丽的作者,但他的作品很有力量。
我翻译了他的小说《空房》。
西方人看他的作品有时更准确。
《纽约时报》评论他的时候有一句话:
「木心的素养,形成一种在遐想中低声吟咏的力量」(MuXincultivatesthewhisperingpowerofreverie)。
你们读木心的时候慢慢读。
这跟听音乐是一样的。
文学有很多种,音乐也有很多种,木心是古典音乐,是那种写法。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木心有很多情诗。
《木心诗选》很快也要出版了。
他有一首情诗深受大家喜爱,叫《芹香子》。
社会上普遍喜欢看的情诗都是现代生活的男女,许多人还要把自己摆进诗里。
当然,从爱情的经验讲这样也无可厚非。
木心也有他自己的经验,对男女情爱的经验。
但是,木心的情诗并不这样写,避免滥情落俗。
如果你习惯了一般的情诗,还不太习惯木心的情诗。
《芹香子》提到的那个情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男或女。
他是「从诗三百篇中褰裳涉水而来/髧彼两髦,一身古远的芹香/越陌度阡到我身边躺下/到我身边躺下已经是楚辞苍茫了」。
整个中国诗学都写进去了,这是何等的情诗。
木心真心喜爱《诗经》中的男女。
他特别喜欢《诗经》。
我们这代人读《诗经》很困难。
我这几年才慢慢读。
读多了就明白,《诗经》的那种简约是一种高贵。
木心作品的品质,也是一种高贵。
他是「贵族」,不是社会阶级意义上的贵族,是精神上的贵族(文革批判「精神贵族」)。
木心的话说得更准确。
他说他是「贵族」,不过是「贵而不族」的贵族。
木心的高贵,是于连代表的那种高贵。
于连是法国普通农民的儿子。
他在法国没落的社会贵族圈里沉浮,最后找到了平民的贵族品质。
木心非常喜欢司汤达,特别喜欢《红与黑》。
我们一起讲到一本都喜欢的书的时候,他总是非常兴奋。
再提一下章法。
评论木心作品的时候,章法经常被忽略。
木心的章法有很多。
我翻译的小说《空房》里面一共收了13篇。
每一篇的章法都不太一样。
比如《空房》这个短篇是典型的元小说。
中国作家里写元小说的很少。
他用元小说,思考文学的虚构是怎么回事,情节安排怎样避免滥情,而且和当时的抗战历史联系在一起。
虽然很短,非常精致。
还有一篇《SOS》很抽象,很像法国象征派的诗。
这一篇没有收进《空房》。
木心去世后,纽约地区有个文学杂志叫《布鲁克林铁轨》,主编找到我,说他很喜欢《空房》,问我手头还有没有译稿寄给他。
《SOS》2013年10月在这个杂志登出,11月就被提名「推车文学奖」(PushcartPrize),而且进入前五名。
我讲一个悖论,木心对我们现在的文学状态是个「例外」,但在世界性美学中却是「常态」。
西方人一读木心的作品就懂,也很喜欢。
《空房》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在网上收集各方面的意见。
有一个普通的网友读者说:
「我以前是不喜欢中国文学的,读过一些。
但是读了这本书以后,我知道我对中国文学有很深的偏见」。
他说他从此以后要读中国文学了。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木心真的是我们文化民族中的瑰宝。
当年在纽约,有朋友和他半开玩笑地说:
木心先生,你可真是国宝。
他说,「国」字就不要了吧。
郭松棻和木心两个人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我也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好朋友。
这件事情是要放在八十年代的情景里思考的。
你们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国家刚开放,我们出去了,木心也出去了。
他碰到了台湾的知识分子郭松棻。
这两个人拥抱的时候,代表的意义很多。
木心和郭松棻之间是互学互补的。
木心需要从他那里更多了解西方知识分子存在的状态,了解一些新的哲学和理论。
但是,郭松棻从木心那儿学了更多。
木心除了会写,能帮助郭松棻提高文学写作以外,他的领悟能力经常把我们带到现实之外的大话题。
这一点是非常迷人的。
说到章法,还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国内现在看到的乱象横生、道德沦丧,木心也写到。
再看一下《一车十八人》这个短篇,看起来很平淡,但充满了愤怒。
我在译这篇的时候觉得难译的,就是那里边那个科研单位的人物骂司机的时候,各种损人的、缺德的那种骂法。
他写《一车十八人》的时候有很多的愤怒。
可是,他按捺住愤怒一笔一笔交代。
他把中国的社会比成《红楼梦》,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小的《红楼梦》世界。
在章法上,木心很善于把不相干的相干起来了。
这也是西方非常重要的美学原则。
看起来是相反相悖的元素,有机地融冶为一体,而木心非常善于这样做。
谈到美学原则,还有一条很重要,我把它称为「他人原则」。
木心很长时间想写自己的传记。
当然,也不是光写自己的传记,把整个国家历史写进去,叫《瓷国回忆录》,计划提纲做了很多,最后还是没有动笔。
他在回国之前跟我说不准备写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找到一个新的美学原则,就是写他人,他人在我身上,我在他人身上。
他有一首诗叫《知与爱》,简明扼要说明了「他人原则」:
「我愿活在他人身上/我愿他人活在我身上/这是知/我曾经活在他人身上/他人曾经活在我身上/这是爱//雷奥纳多说:
知得愈多,爱得愈多/爱得愈多,知得愈多//知与爱永成正比」。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现在喜欢的木心的诗,跟我们现有的知识状态是有关系的。
我们大致喜欢他跟现实生活中发生互文的诗。
比如《从前慢》,当然是好诗。
但是,他还有大量的作品,特别是诗作,是和中国的古典文学发生互文的。
还有更大量的作品是和西方文学和文化发生互文的。
有的时候和东方西方都发生互文。
有一首诗叫《大卫》,东西方焊接得天衣无缝,那个「焊痕」非常漂亮。
一个作家,他的文字里有那么多内容,他懂得修辞性思维的重要是关键。
尼采是现代重提修辞或艺术思维的标志。
为了清理柏拉图传统逻辑思维的问题,尼采将诗和哲学重新联姻。
修辞思维让我们避免陷入逻辑思维形成的那些概念的陷阱。
木心经常对丹青他们说,这是陷阱,不要掉下去了。
木心《魏玛早春》的开头,写春天要来又不来,春寒的状态。
又讲到农舍、田野、月色、柳树。
觉得春天像一个人。
通常我们写抒情,到这儿就停了。
但是,他填一句,「但是,春天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
突然跳出了人类中心认识论的圈子。
这个不仅仅是用笔的巧妙,而是他的心思到了。
木心是一个经常思考大事的人,宇宙观、生命观,然后才有社会、政治、人生,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
时间的缘故,我最后讲一下我跟木心的第一次访谈。
我是1984年认识他,访谈的时候已经是1993年的夏天,也许是秋天。
他住的地方就是丹青写过的杰克逊高地。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到的,第二天、第三天两个整天跟木心在一起,第四天的早上离开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差不多是从早上九点起来就谈,我们也没出门。
木心早就准备了一些食品,如果缺什么,会打一个电话列一个食品单,叫别人买了送过来。
我们就没有离开那个房子。
有时候休息一下,接着聊,聊到晚上三、四点。
我走的那一天,木心说:
「你得走了,要不然我就虚脱了」。
我当时还年轻。
谈得很多很多。
我的问题的调查单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到了第三天晚上九点多了,我说,不行,要谈[问题单上]这些事了。
木心不愿意谈「正事」,他谈别的事的兴趣很大。
谈到的都是大问题,会谈到文革,谈到中国的历史上的人物。
我去年写过一篇关于木心对联的文章,那里边就谈到了几个历史人物,他后来又加了几个字,把近代的历史和中国的古代历史接起来了。
他后来给我的一个新版本的对联,历史的跨度又更长了。
这只是我们在中间茶歇的时候谈到的。
会谈到生命,尤其是一个观点,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经常回避的一个问题,生和死是紧密相关的。
他会谈到死亡。
因为自然界的生命是包括死亡的。
我也是从木心那儿学来的。
以前自己读到西方的诗,也会谈到死,但不太理解。
我还向他请教。
他就用《圣经》里的话讲这个。
当时拿起一个水果,这个水果是生,还是死?
它既是生,又是死,自然界是包括死的。
生死、宇宙。
谈到老子的《道德经》应该改一改了,因为现在的知识范围扩大了很多;
会谈到时空;
也会谈到西方的启蒙运动;
中国的五四。
好象没有不谈的事。
现在坐在这儿,多少有一点紧张,不可能很全面地呈现当时讲了什么。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非常神秘的事,这件事情对我和木心来讲是很隐私的事。
只有我和木心知道当时发生的情况。
木心跟丹青他们讲课的时候也转述过。
但是,转述和当时经历这件事情又不一样。
大概是当时谈的题目越来越大了,木心说我们讲得黑了起来。
英语有个词叫sublime,不是通常意义的美。
这种美里面有一种超自然力量的恐怖。
王国维称之为「壮美」,姑且如此吧。
那时,有一点sublime了。
十一点多,快到半夜的时分。
我讲一下那个房子的情况。
它像中文的「日」字一样,右边是狭长的走道,墙上贴一幅王羲之的书法。
房子分三节,从外面阶梯上来,进门是第一间,有书桌,算作书房。
再走过去,中间就是厨房。
最后一间是他的卧房。
我们谈话的时候是在前面的房间。
谈到半夜的时候,一只鸟叫了。
我强调一下,不是一群鸟,也不是两只鸟,是一只鸟。
我们可以分辨出来是一只鸟。
这个时候,它开始叫了。
叫的时候,木心很敏感,他说有点可怕,我要不要去看一下。
他就出去看了一下,我也跟着去了。
我没看清楚,他说是一只红胸鸟。
这只鸟应该是一只模仿鸟,它会学别的鸟叫。
我以后到了加州,还一直在调查这个事。
我们教授的同事中有人专门研究鸟,他说加州有一种模仿鸟,红胸,可以叫两三种调法。
但是,这只鸟,我们这样数下来,有七八种曲调,不光是独唱,而且还有和声,非常奇特,还有变奏。
变奏得非常巧妙。
最少有七八种叫法。
这是第一点奇特的地方。
这只鸟是疯掉了一样的叫。
我们从午夜一直讲到三点钟准备睡觉,这只鸟都在叫。
当木心睡到床上,我睡在地铺上,还继续聊的时候,这个鸟还在叫,大概到三点半左右,我们睡着了,这个鸟才不叫了。
一个神秘的事件。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事?
因为没有这个语境,我谈这个事好像没有意义。
因为木心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秘主义者,类似古波斯的诗人鲁米。
现代科学的讲法,是能解释的就是科学,但还有很多是解释不了的事情,不能说是非科学,也不能说是迷信。
我觉得艺术家的观察和思考,对于未知的、不可知的东西有一种崇敬。
这只红胸鸟好像是给我们伴奏,又像是参加我们的对话。
木心认为:
我们当时的谈话,「也许触及了生命的秘密,惊动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我先讲到这儿,丹青替我再讲讲。
3.我也不确定(出版)对不对,我不太相信一个作者能够改变读者——今天这么多读者坐在面前——可是我亲眼看到读者会改变作者。
陈丹青:
我第一次听你这样子讲木心。
你就好事做到底吧,19号还有一场,是上海书展,你来好不好?
也是跟这本书有关的发布会。
我能讲的,就是今天新出的《木心谈木心》和《文学回忆录》的关系。
在座知道木心先生的人有多少?
(现场三分之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童明陇菲陈 丹青 梁文道谈木 心上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雷雨》中的蘩漪人物形象分析 1.docx
《雷雨》中的蘩漪人物形象分析 1.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