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教育地理研究回顾与借鉴Word格式.docx
国外教育地理研究回顾与借鉴Word格式.docx
- 文档编号:17453151
- 上传时间:2022-12-01
- 格式:DOCX
- 页数:13
- 大小:31.33KB
国外教育地理研究回顾与借鉴Word格式.docx
《国外教育地理研究回顾与借鉴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外教育地理研究回顾与借鉴Word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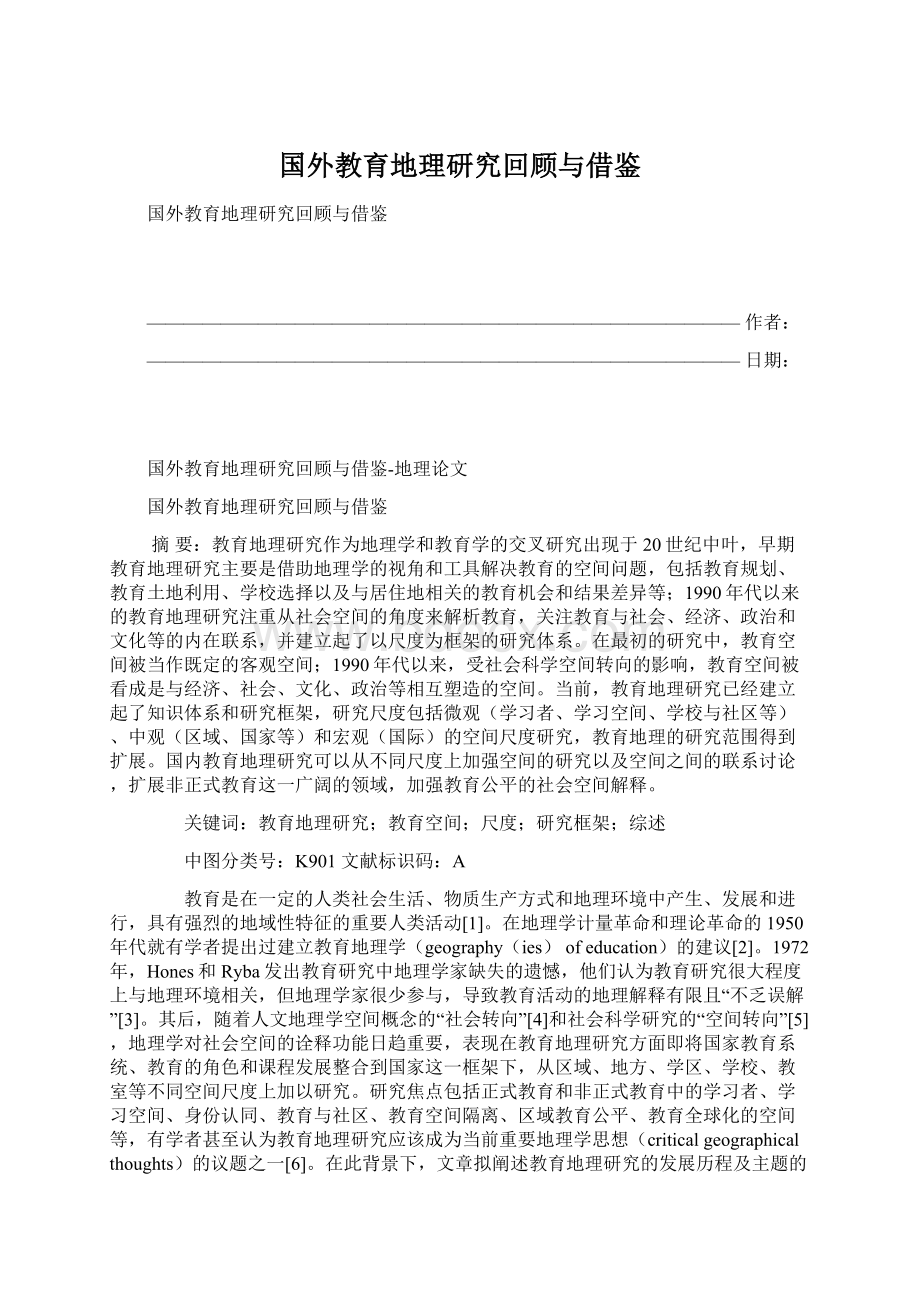
研究框架;
综述
中图分类号:
K901文献标识码:
A
教育是在一定的人类社会生活、物质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中产生、发展和进行,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的重要人类活动[1]。
在地理学计量革命和理论革命的195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建立教育地理学(geography(ies)ofeducation)的建议[2]。
1972年,Hones和Ryba发出教育研究中地理学家缺失的遗憾,他们认为教育研究很大程度上与地理环境相关,但地理学家很少参与,导致教育活动的地理解释有限且“不乏误解”[3]。
其后,随着人文地理学空间概念的“社会转向”[4]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5],地理学对社会空间的诠释功能日趋重要,表现在教育地理研究方面即将国家教育系统、教育的角色和课程发展整合到国家这一框架下,从区域、地方、学区、学校、教室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加以研究。
研究焦点包括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中的学习者、学习空间、身份认同、教育与社区、教育空间隔离、区域教育公平、教育全球化的空间等,有学者甚至认为教育地理研究应该成为当前重要地理学思想(criticalgeographicalthoughts)的议题之一[6]。
在此背景下,文章拟阐述教育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主题的扩展,并结合近20年来的教育地理研究进展,分析其当前研究的基本态势及对我国教育地理研究的一些启示。
1教育地理研究兴起和初步发展
1.1教育地理研究学科建构的主张
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分支学科建构兴盛,学者们纷纷呼吁重视地理学在教育研究中的作用,倡导建立教育地理学分支学科。
Eisen通过观察地理学发展的学科体系化态势呼吁建立教育地理学,认为教育地理学的建构可比拟于工业地理学、医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学科的建构[2]。
1968年Ryba列举了当时业已存在的教育地理研究议题,认为教育地理学研究范围广阔[7]。
在1972年于多伦多大学举行了国际地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GeographicalUnion,IGU)年会上Hones和Ryba提交了报告《为什么没有一门教育地理学?
》,指出在社会和文化地理领域中应用地理学研究教育现象的价值,例如界定学区边界、研究能力和成绩的区域差异以及教育机会和学校供给的区域差异问题,论文建议教育地理学的发展必须与教育学和地理学的当前趋势保持一致[3]。
由此,IGU在地理教育委员会中建立了教育地理工作组,Hones和Ryba被任命为该工作团体的联系秘书,在1973年~1981年间连续发表了5个公告,有力地推动了教育地理研究的发展,下面以其研究主题为视角来做介绍。
1.2早期教育地理研究的主题
(1)教育规划
早在1929年,Dudley就对学校的位置、学校所需面积、学校的最佳规模、上学距离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小学选址进行了实证分析[8]。
60年代,Yeates研究格兰特县高中腹地以确定空间有效距离,进而提出合理的边界建议[9]。
McNee则从地理学知识结构的层面来论述地理学对教育规划的潜在贡献,分析了地理学方法论和概念对教育规划的影响,强调直接观察和调查,认为“文化生态地理学”(cultural-ecologicalgeography)和“地理区位论”直接地与教育规划相关联[10]。
(2)教育土地利用
地理学者通过在不同尺度下研究以区域为单元的教育土地利用,从而发现教育土地利用的地区差异、教育土地利用与区域中动态人地关系的联系。
1949年,Philbrick对芝加哥市温内特卡和布里奇波特社区教育用地及其他用地例如休闲用地、居住地、工业用地的情况,讨论了教育用地使用紧张、受教育人口分布等问题[11]。
随后,Eisen归纳了当时教育土地利用的研究成果,认为虽然研究结果不同,但这些研究都表明在特定的区域中教育与人地关系其他要素交织在一起;
当前教育设施及功能揭示了教育的需求和问题,根据调查可以找到满意的发展模式。
(3)教育供给和结果的差异与学校选择
Robson应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桑德兰五个市中心平民区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态度、邻里的阶层构成与教育成绩的关系[12]。
Coates在《英国区域变化:
社会地理研究》一书中对个人收入、职业、移民人口、医疗服务、死亡率和教育等6个主题进行研究,其中教育方面主要研究英国教育供给和教育结果的差异,研究的内容包括:
不同形式私立学校的影响,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以及高等教育在地方教育行政区中的差异等[13]。
到1980年代,随着英国教育改革实施学校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教育地理研究形成了比较典型的研究方向,即学校选择。
Bondi等著《教育与社会:
政治、社会和教育地理研究》首次在标题中出现教育地理一词,该书中包含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教育地理问题,例如学校的重组、城市间家长选择学校的比较、学校的影响范围、邻里问题和城市内成绩差异等[14]。
另外,Bradford从区域的尺度研究学校选择,发现家长的学校选择在空间上并不均衡,城市的选择面多于乡村;
同时,他从地方的尺度研究学生居住环境对成绩的影响,结合二者发现居住环境影响学校的选择和学生成绩[15]。
学校选择暗含空间性,吸引地理学家从不同的方向去研究,使得这一研究主题一直得以持续。
Ball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学校选择,认为教育市场的选择与社会阶层差异有系统的关联并且再生产阶层不平等[16]。
Griffin关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的三个教育行政区中公立中学选择政策的调整[17],研究发现在入学问题上三个国家都有相似性,它们是:
地方层面的政策交互增强、高中学生数的变化、社会隔离的存在、招生筹资机制差异、地方利益群体对公共教育的不同态度、空间管理的意义等。
在Griffin的研究中采用了地方、区域和国家的尺度来分析。
总体而言,教育地理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是呼吁建构一门新的研究领域,指出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应用了地理学的视角、工具及尺度分析的方法解决教育问题,诸如教育规划、教育土地利用、学校选择以及与居住地相关的教育结果差异等,这些研究主题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教育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
然而这些研究中空间概念还较少提及,尔后,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教育地理研究的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
2当前教育地理研究进展
空间是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从1970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进入了从空间分析到社会理论的演化阶段,空间的社会性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18]。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主要是资本、权利和阶层与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空间成了介质、产物及过程。
空间不是一个静态的、容器的或反映相互关系的绝对和相对空间概念,而反映了更多的关系和过程[19]。
空间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被充分揭露出来,由于其对现实世界毋庸置疑的解释力,空间的重大意义被人文社会科学界普遍接受,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空间相关的领域大量进入文化社会学科研究的主题,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20]。
教育地理研究也受此影响,走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2.1教育地理学理论构建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地理学的知识体系一直是学者思考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理学逐渐受到公共服务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以及政治地理学的复兴,研究者关注公共财政地理和区域劳动力市场,Bradford思考教育地理学在地理学中的位置,认为教育学与地理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劳动力市场、住房市场和政策影响上存在关联。
其后,Taylor对教育地理学进行了知识体系建构(图1)[21],他看到了空间转向与地理学对社会、人文学科的交互式影响,认为“地理学科对教育领域的贡献是复杂的,因为它们都基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主流社会科学的贡献”。
这种跨学科的思想同样得到Brock的支持,Brock认为教育学和地理学都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教育的本质是传播,地理学的本质是空间,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必然包含传播的空间维度,例如个别指导、教室、网络等空间,因此二者之间存在本质的紧密联系[22]。
教育空间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空间,是对社会空间的再空间化,形成独特的教育空间;
但同时,教育空间也在塑造新的社会空间[23]。
1990年,Bradford区分了两种教育地理研究取向,其一,大多数研究者把教育看作研究的对象,教育如何促进政治、社会、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是研究者的兴趣所在;
其二,少数研究者则把教育作为研究的主体,从经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理解教育的变化。
这两个视角都有利于理解教育与其他系统之间的联系。
Thiem以Bradford的思想为基础构建教育地理学的研究框架,把教育地理研究分为两个方向:
其一,教育本身构成研究的对象,研究教育供给、消费以及学校产出的空间变化;
其二,研究与教育相关的“外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空间变化过程[6],她把这种区分称之为内向和外向分析(inward-andoutward-lookinganalyses)框架。
其中内向的研究视角包括不同国家义务教育系统分布问题、空间层面上的学校选择、不平等教育供给的政治地理结构等。
这些内容与教育地理研究初期的主题一致,也与《人文地理学词典》对教育地理学的定义一致[24],这是把教育空间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社会空间的独立空间的研究。
但Thiem认为这些并没有包含教育地理研究的全部可能性,尤其是忽视了教育的结构性能(constitutiveproperties)——教育机构和实践如何引起教育之外的变化。
因此教育地理研究还应包括外向分析视角,即教育地理应该着重讨论教育如何塑造空间,或促进地理变化,她把教育地理研究置于文化、社会、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地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联系之中,解析社会文化的变化对教育空间结构的影响。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兴起也对教育地理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文主义地理学主张尊重个人的主观性、意识性和主体性,反对把人类作为物质对待;
重视人与环境间相互作用,认为人的行为受制于主体的感知环境。
其思考方式扩展了地理学的空间概念,除客观空间以外,人文主义更强调主观空间、强调“从主体看空间”的人文主义新视角[25]。
受此影响,教育地理研究也同样开始关注从个体的层面研究儿童、青少年与空间、地方之间的关系。
Holloway在赞同Thiem提出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补充了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教育地理研究,强调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在未来教育地理研究中的地位[26]。
作者认为Thiem把过去的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视角是排除了关于学校设计、学校空间中社会差别的(再)生产以及家庭和教育空间之间的联系等方面的研究,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需要在内向和外向教育地理学视角中关注他们当前和未来的生活世界。
可见,由于“空间转向”的影响,教育地理研究从传统的物质空间(学校分布、教育供给和消费差异)发展到非物质的空间(个体空间、学习空间、社会空间);
不仅研究教育内向的独特空间,更加注意到教育空间对社会空间的塑造。
实际上,1990年代以后的教育地理,其关键的概念是教育、空间、权利,这便是所谓的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27]。
2.2当前教育地理研究的主要议题
从早期教育地理研究开始,研究者就注意到了研究的尺度问题,无论是Hones还是Ryba,都认为研究的层次包括地方、区域、国家、国际。
与早期研究者不同的是当前研究尺度进一步延伸,例如,Taylor在微观尺度上将研究对象分为学习者、学习空间、学校与社区;
Brock也看到了教育地理尺度的意义,包含从全球、区域、国家、国家内、社区到个体的空间尺度。
事实上,以上不同空间尺度在近年都有较多研究,本节基于Taylor研究尺度的划分,阐释不同尺度下的研究内容。
2.2.1微观尺度
(1)学习者
随着当前对儿童的关注及儿童地理的发展(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IBG)有儿童、青年和家庭地理学“GeographiesofChildren,YouthandFamilies”工作组),研究者开始关心在教育消费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声音和想法,Holloway提出应对儿童的经验及经验加工做深入研究。
这样的研究已经起步,Reay研究在低收入水平地区的儿童在小学到中学过渡时期的经验,包括研究儿童关于不想去被分派的当地“妖魔”中学的谈论方式,以及当被送到那里之后他们如何自我解释和表达该学校[28]。
一般而言,成人对“正常”和“异样”童年的理解会影响教育供给和消费的塑造,例如Vanderbeck从儿童的角度研究半游牧传统的少数民族儿童的权利和入学权力以及这些儿童的社会排斥和融入[29]。
在学习者尺度上,除了对中小学生的研究,也有关于大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住房选择的研究。
大学住校生活是学生从青少年转变为成人的重要阶段,那些在读书期间依然住在父母家的学生要面临减少高等教育中的机会和失去与“真实”学生生活相联系的独立性等不利处境[26]。
大学生的居住路线(housingroute)一般为离开父母的家(例如宿舍生活)、在私人住所租住、毕业后有自己的住所。
与那些没有离开家庭的年轻人相比这一居住路线提高了房屋入住率和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30]。
居住状态主要影响学生非学业的方面,居住状态是学生成功适应大学生活的主要因素,离家居住的学生更容易脱离家庭背景融入学校生活中去[31]。
这与过去关心大学生的学业以及高等教育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有明显区别,研究更加关心学生非学业方面的生活和经验。
(2)学习空间
学习空间主要包含学校和家庭这两个主要的空间地点和社会实践地点。
在学校空间内,Schneider发现学校的设施影响学习,学校的空间配置例如声音、温度、光线、空气质量都会影响学生和教师的表现[32]。
此外,学校围墙内存在着“隐藏地理”(hiddengeographies):
一些微观空间的研究。
Ingen研究学校中的种族化地理(racializedgeographies)问题,采用深度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加拿大四所高中的土著居民学生,研究发现这些学生以户外抽烟区的形式构成一个集体空间,这一空间与问题学生项目室的入口相邻[33]。
法国思想家福柯通过空间认识权利与知识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关系,空间是权利、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18]。
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教育地理也开始研究学习空间中的权利——空间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再)生产。
研究者们看到了学校课程尤其是非正式课程构建的学习空间对公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Holloway提出需要去研究社会差别在正式课程的设计、传递和吸收,以及他们通过在学校和其他教育空间非正式课程的(再)生产,而这需要关注阶层、信仰、性别、种族等更广的范围。
在正式课程层面,Collins追踪了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差异,这种差异集中在合适课本的争论上,研究发现一些家长的宗教观念会影响公立学校的课程,从而影响到学生[34]。
信息技术课程对于学生融入现代社会有重要作用,Valentine研究学校信息通信技术(ICT)课程与社会排斥,发现政府政策(导致硬件配置的差异)、学校对ICT的理解以及同伴文化对于学生掌握信息技术有重要影响[35]。
而非正式课程塑造的空间也同样会影响儿童的身份认同,例如Thomas分析了美国南部高中的种族隔离,影响女孩日常空间活动(她们在午饭时与谁一起坐,她们如何谈论彼此等)的是种族的社会差异、身份认同和空间[36]。
在学校内,除了学校环境外,行政管理同样是非正式课程的一部分。
Leeuw研究1861年~1984年间加拿大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印第安居民区学校,她研究了政策和学校员工的工作对年轻人的影响。
在这里,原住民的年轻人远离他们的父母以使他们割断与传统之间的联系,同化他们使他们服从加拿大社会统治[37]。
近年来对于学习空间的理解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学校地点,研究者不仅关心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而且关心发生在学校之外的学习,例如在家庭中的学习。
Duncan认为家庭中教和学是形成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家庭地理(geographyofhome,例如与兄弟姐妹之间或与父母)的重要方式[38]。
在家上学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在家上学的地理特征是活动的综合,在家里的每日活动和家外的活动使家庭成为多来源、可伸展的、可渗透的空间[39]。
除此之外,校外的学习空间还包括在学前托儿所(pre-schoolnurseries)[40]、儿童上学路程中的经历[41]和课外俱乐部(after-schoolclubs)[42]等场所,这进一步加深了对教育空间的理解。
可见,对于学习空间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包含不同地点及微观空间,同时也关注社会差异在正式课程和非正式课程所形成的学习空间中的表现。
(3)学校与社区
在学校与社区尺度上,学校作为聚集点和社会网络节点,是当地社会和政治的中心,学校形成居民无形的地方感和归属感。
Witten描述了在新西兰低收入地区小学的关闭如何损坏当地信息网络和精神支持,他们认为学校是周边社区兴旺和凝聚力的关键,学校是社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43]。
然而,由于社区存在基于阶层和种族的居住地差异和隔离,这会产生教育供给的差异,并且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可以在结果上产生显著的差别[44]。
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管理系统对学区的划分使得学生几乎都是就近入学,受教育机会主要与家庭居住地选择有关,这加强了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分区可以使学校反映或加强业已存在的依据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区分的居住隔离模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争相进入所期望的学校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卖点,尤其是在高中阶段[45]。
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生在大学城学习期间的生活方式和对当地的影响开始受到重视,目前的研究关注学校和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重要转变。
在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快速扩张的大学中由学生组成的短暂居住居民群体不断增多,对于长期居住在此地的居民产生了负面影响[46]。
在房地产市场,学生经常超出当地居民群体,这一过程被视为类似于高档化(gentrification)的过程,学生的生活方式分化和取代了低收入群体的空间[47]。
Smith长期关注学绅化(studentification)过程,学生涌入到特定的邻里社区导致了城市与大学之间关系的恶化,学绅化降低了群体之间正面的和利于交互的机会,增加了基于生活方式和人生历程差异的群体分离,以及不同层次的经济资本分离[48]。
2.2.2中观尺度
教育地理研究在中观尺度上主要包括区域和国家尺度,在区域尺度上的研究包括:
1)地方教育部门的政策地理。
Radnor通过研究4个不同地方教育局的规模、政策管理、位置和历史,以探究权力分配改变后学校和地方教育局之间出现的新关系形式以及地方教育局新的组织文化和实践。
研究发现当前地方教育局与学校呈现多样的“合作关系”,这与地方当局的政策管理和历史、组织文化和规模相关[49]。
Lauglo研究了地方分权的形式对教育管理权的分配和学校评价的影响[50]。
Johnston等研究英格兰学校的种族隔离程度,比较这一隔离是否比居住地隔离更强。
研究表明比起邻里,学校的隔离更强,尤其是在小学和有种族群体的学校,相当大的影响来自于教育政策。
这是一个区域性层次的比较研究并且包含了农村和城市的变化[51]。
2)基于地方尺度的成绩差异研究。
Byrne研究地方教育局的政策对教育成绩的影响,认为在教育社会学中地方政策的影响被忽视,政策这一变量对成绩有主要决定作用;
对地方教育政策类型的追踪可以解释教育成就的多样模式[52]。
地方学区影响学习的方式是间接通过教师在学校里的协作和提供的教学质量来形成的,学校间学习网络的发展、教学与学习之间有积极的联系[53]。
3)区域教育公平。
Taylor研究英格兰和威尔士新教育市场选择和多样化的地理,通过学校供给多样化和家长选择这两个关键因素来表明英国教育市场的不均衡发展,研究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等教育市场并非均衡,不仅表现在家长能选择的学校类型上,也表现在家长作为消费者对提供的新教育市场的应对上[54]。
在国家尺度上的分析主要来自英国的研究者,这与其政治体制有关,Brock分析了18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校供给的社会和空间差异[55]。
另外,自从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策下放后对国家政策的发展以及对教育的“内部国际”(homeinternational)分析重新成为研究兴趣。
权力下放前、后教育政策发展的变化具有局限性,在教育政策延续上公民社会组织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56]。
采用低于国家水平尺度的“内部国际”视角的比较可让政策和教育结果的联系研究更清晰,从而更容易理解当前英国复杂的教育结构[57,58]。
2.2.3宏观尺度
全球化的发展使教育空间进一步扩张,教育全球化的空间研究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有学者把空间分析的方法运用到教育全球化研究中,Robertson通过两个方面来打开全球化与教育的新思路:
其一,空间是社会生产;
其二,尺度的概念有助于思考社会空间组织的差异[59]。
实际上,Lingard已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场域(socialfield)概念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政策循环[60]。
在教育全球化的过程和影响方面,Ashton研究国际层面的教育培训系统的发展模式,多角度地深入调查了当代经济和教育培训系统之间的连接,发现教育在当代已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经济增长点之一[61]。
Epstein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内在的空间、历史和经济的联系,研究内容包括大学的生产和再生产、知识供给、需求及跨国学术流,强调知识和权利的相互关系,关注空间不平衡的出现、知识地理[62],研究采用了明显的跨学科视角。
在国际尺度上研究大学生的迁移是一个重要方面:
学生如何影响“发送”和“接收”的社会,他们建立起什么样的跨国网络以及学生迁移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
Waters研究迅速发展的教育国际化对社会和空间的影响,他们以香港为研究区,一方面,东亚的上层中产阶级通过获得“西方教育”以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在“学生发送”社会产生了新的社会排斥地理。
另一方面,加拿大的中小学得以利用国际化的利益消除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当地的社会再生产。
Waters据此认为,教育国际化转变了社会再生产的尺度[63]。
其后他们进一步对东亚、欧洲和英国学生的流动做了研究,以学生的视角研究留学生的学习动机、目标和经历,指出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存在区域选择的问题,形成高等教育在国际层面上的区域聚集效应[64]。
分析如上不同尺度的研究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不同尺度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尺度之间并不互斥或独立,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国外 教育 地理 研究 回顾 借鉴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