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端之心与人性本善兼论以《孟子》为人性向善论者的理论误区Word文档格式.docx
四端之心与人性本善兼论以《孟子》为人性向善论者的理论误区Word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17425103
- 上传时间:2022-12-01
- 格式:DOCX
- 页数:6
- 大小:24.24KB
四端之心与人性本善兼论以《孟子》为人性向善论者的理论误区Word文档格式.docx
《四端之心与人性本善兼论以《孟子》为人性向善论者的理论误区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四端之心与人性本善兼论以《孟子》为人性向善论者的理论误区Word文档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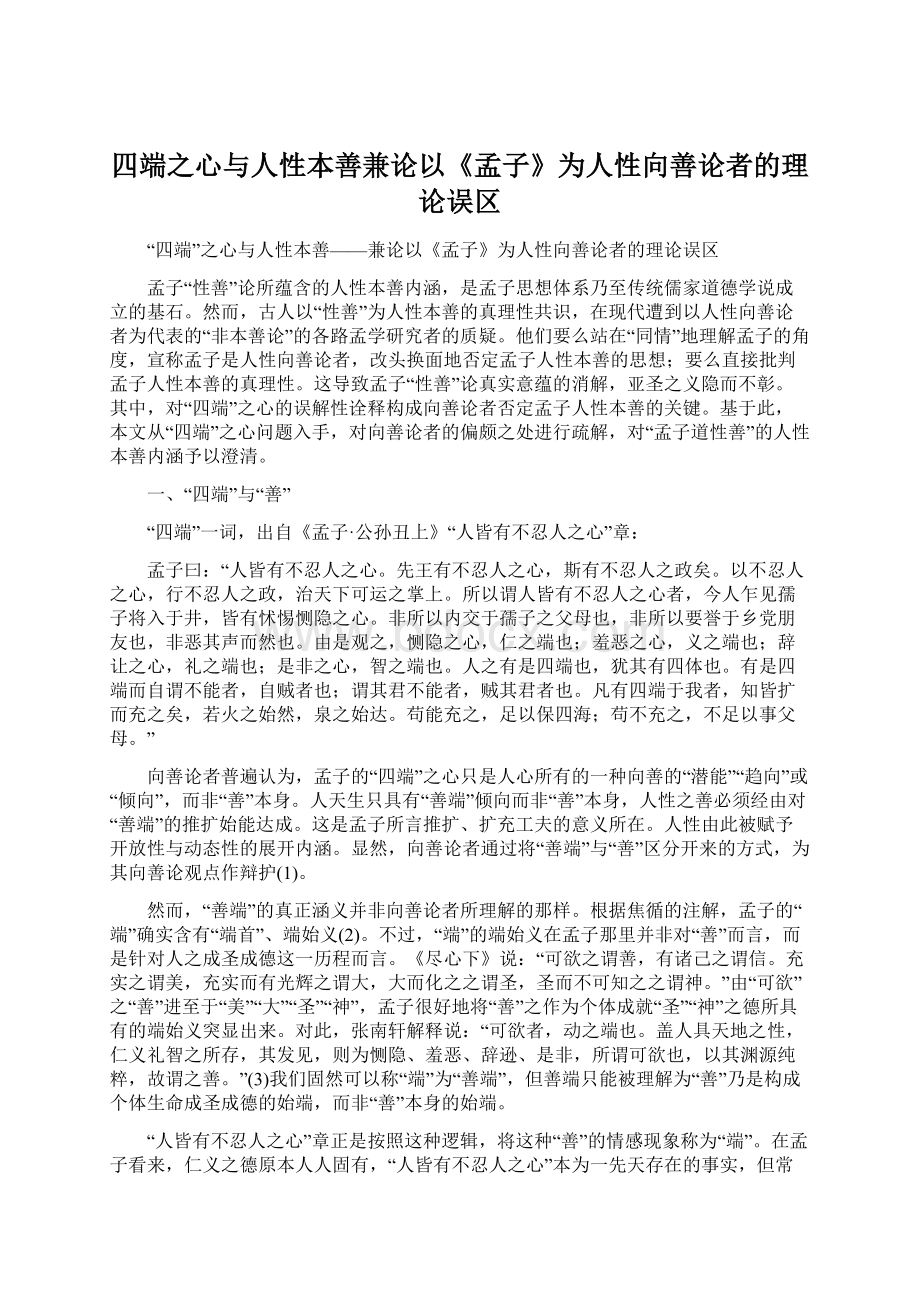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
向善论者普遍认为,孟子的“四端”之心只是人心所有的一种向善的“潜能”“趋向”或“倾向”,而非“善”本身。
人天生只具有“善端”倾向而非“善”本身,人性之善必须经由对“善端”的推扩始能达成。
这是孟子所言推扩、扩充工夫的意义所在。
人性由此被赋予开放性与动态性的展开内涵。
显然,向善论者通过将“善端”与“善”区分开来的方式,为其向善论观点作辩护
(1)。
然而,“善端”的真正涵义并非向善论者所理解的那样。
根据焦循的注解,孟子的“端”确实含有“端首”、端始义
(2)。
不过,“端”的端始义在孟子那里并非对“善”而言,而是针对人之成圣成德这一历程而言。
《尽心下》说: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由“可欲”之“善”进至于“美”“大”“圣”“神”,孟子很好地将“善”之作为个体成就“圣”“神”之德所具有的端始义突显出来。
对此,张南轩解释说:
“可欲者,动之端也。
盖人具天地之性,仁义礼智之所存,其发见,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所谓可欲也,以其渊源纯粹,故谓之善。
”(3)我们固然可以称“端”为“善端”,但善端只能被理解为“善”乃是构成个体生命成圣成德的始端,而非“善”本身的始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正是按照这种逻辑,将这种“善”的情感现象称为“端”。
在孟子看来,仁义之德原本人人固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本为一先天存在的事实,但常人因后天习气的遮蔽,往往会贼害其心,造成“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尽心上》),无法意识到这一事实本身。
为了使人对这一先天事实有所自觉,孟子始举人之“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怵惕恻隐”这一排除思虑计较而为人人所同具的本能性情感反应,来点明不忍恻隐之心为人所本有。
因这种特定的“不忍”恻隐之心乃是一排除思虑计较的本能性直感,故而它必然是人之最为“初始”的“可欲”之“善”。
《尽心上》一方面讲“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另一方面又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
孟子之所以用“不欲”与“不忍”的相互替换来讲“仁”,正是基于“不忍”之心与“可欲”之善的此一内在关联性。
在孟子那里,这种不忍之“善”之所以被称为“端”,恰恰因它是作为成就“仁义礼智”之德的初始情态而说的。
不忍人之心虽为人所本有,然而它在吾人那里常因习气的遮蔽而表现为一忽明忽暗的本能性乍现,它常常是转瞬即逝的。
后儒常说“初念为圣贤,转念为禽兽”即是此义。
因此,孟子在本章最后强调说,吾人必须以此忽明忽暗之乍现的“四端”之“善”为出发点,“扩而充之”,始能真正发明恢复起不忍人之心的全体大用,成就“足以保四海”的“圣”“神”德性人格。
在此意义上,“扩而充之”的工夫,就必然展现为孟子时常提起的“孳孳为善”(《尽心上》)、“乐善不倦”(《告子上》)的动态生命实现历程。
事实上,以“善”为“端”而进至成圣成德这一动态生命实现的观念,并非孟子凭空独创,它是在从孔子到子思子(及其门人)再到孟子的学脉承续关系中逐步确立的。
孔子讲“举善而教不能”(《论语·
为政》),又讲“嘉善而矜不能”(《论语·
子张》)。
虽然多落在王道政治的层面以言“善”,然而,其背后实蕴含成就君子之“德”或君子之“道”的理念内涵。
孔子屡言“志道”“谋道”“求道”“闻道”,即说明了这一点(4)。
在子思及其门人那里,由扩充“善”“端”以成就君子之“德”的理论进路更为明显。
郭店简《五行》篇讲“德之行,五和胃(谓)之德;
四行和,胃(谓)之善。
善,人道也;
德,天道也”;
又讲“能进端,能终(充)端305,则为君子耳矣。
弗能进,各各止于其里”。
这里的“四行”指“仁义礼智”,而“五和”指“仁义礼智圣”之“和”一。
前者是人道之善,后者是天道之德。
这两句话充分表明五行之“德”并非外在于四行之“善”,“圣”亦并非在“仁义礼智”之上所别有的一“德”。
五行之“圣”“德”,恰恰只是四行之“善”的“充”其极,“圣”“德”只是吾人在“能进”四行之“善”“端”这一动态生命历程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人格境界。
由此,“善”之于“德”就具有“端”始的意义。
孟子由扩充“可欲”之“善”“端”而终至于“圣”“神”之境的讲法,与这种观念一脉相承。
显然,孟子以“善”为“端”的讲法,是与从孔子中经思孟学派再到孟子,“善”的规定性被逐渐内转——其政治向度被弱化,而心性层面的本原性意义被突显——这一致思脉理是内在关联的。
二、动态人性论的内涵
由此而言,“四端”之“端”确实表明孟子的人性论具有动态的、开放的内涵。
然而,这个动态性和开放性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向善论者所讲的人性必须经历一个从未完成状态到完成状态的时间过程,而首先是指人性内在包含着一个动态的先天结构。
换句话说,人性的动态性和开放性,首先是对人之先天存在方式的描述,而非仅是对人在不同时空中的经验状态的描述。
因为人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个和未完成状态相区分的完成状态,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动态的、开放的、有待完成的。
邹化政对此颇有见地:
“人性,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以其在既定高度的条件总和中展开自身的现实性为基础的潜在性、理想性,所以人性有待于实现,人也有待于实现。
”(5)孟子由“可欲”之善这个动之“端”充扩而来的“圣”“神”之境,不但不是一个在时间意义上的人性完成状态;
相反,它是一种最具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神妙“不可知之”的待完成状态。
其实,《五行》篇早在孟子之前就以“君子之为德”的无限敞开性来讲人性的这种动态内涵:
“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也,有与终也。
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186也,无与终也。
”“君子之为德”之所以“无与终”,是与“君子之为善”“有与终”对比而言的。
但“为德”并非外于“为善”所别有的一个过程,它本质上就是一个为善不息的动态结构。
以人所本有的善为出发点,为善不息,善善不断,始能成就君子之德。
反之,君子之德的成就,在任何时候亦必须是一个为善不息、善善不断、无所终止而有待实现的过程。
正是《五行》篇这一思想,直接启发孟子以人的先天存在结构为人性,又以人性为出发点来讲扩充善端以成德成圣的义理进路。
“端始”是指人性自我实现的那种“善”的现实基础,它所开启的是一成圣成德的现实起点,而不是指人类生而即有的某种本能性的行为,即使这种本能行为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
这个现实起点的内容,即是儒家所讲的“情”。
《礼记·
乐记》讲“报情反始”,就表明“情”是人之本始。
同样,郭店简《性自命出》讲: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道始于情”正是说人道在现实上本乎人情,“情”是成就人道以顺性命之正的现实基础和起点,所以后文接着说“始者近情”。
孟子所讲“四端”的具体内容正是指“情”。
孟子主张在人情上见人性: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
”(《告子上》)可见,由“情”以成性(成圣成德),通“情”而达理(6)的动态人性论,构成思孟学派的基本致思进路。
这个由人“情”之显以成“圣”成“德”的动态人性结构,自然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
而是以“善”之内容贯穿始终为其内在基础的。
孟子由“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之“情”善以言性善的说法,即说明了这一点。
从“善”的先天内容,而非从经验形式上理解人性的动态内涵,就构成孟子解读古人“生之谓性”说的首要前提。
孟子并不反对“生之谓性”(《告子上》)这一动态人性论的讲法(7),他真正反对的是告子那种经验论式的“生之谓性”论。
这种理论表面看来坚持的是一种动态开放的人性论,实质上因取消“性”的先天固有的“善”性内容,必然导致其所谓动态开放之“生”沦为一种经验性的盲目无常流变。
自然而然,人“性”因此失去人之为人的超越奠基义,使“人”沦为一虚无的存在。
“生之谓性”所指向的是对一物之为一物内在根据的奠基与完成,它必然包含有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具体“类”性内容,而不能仅仅是一种经验上的生长形式。
孟子指出,如果像告子那样仅仅从经验形式上理解“生”,就势必会得出“犬之性,犹牛之性;
牛之性,犹人之性”的荒谬结论。
所以,“生之谓性”是说一物将其本有内容展开、实现出来的这个内在奠基过程叫作“性”。
在此意义上,性的内容必然是“我固有之”,而非外铄而来。
人性之“生”的动态性,作为人性自我展开、自我完成的内在环节,意味着这个“生”只是向着人性自身回归、为它自身奠基的复归运动。
从人性的内容看,这就是不断回复到原初本有的可欲之“善”的运动。
郭店简《性自命出》所说的“反善复始”,正是对这一原理的精准描述。
所以,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
“赤子之心”当然不是从经验形式上说,而是从它的先天固有内容上来说的。
小孩终究要长大,大人之心不可能在经验形式上同于小孩。
孟子在此是说,真正的大人能够像赤子一样,不以“凿智”戕害本心,从而能够保有他本有的“善”性内容。
我们现在常说的永葆初心或不忘初心,就是这个道理。
由此,人性之“生”实为一回归其先天之“善”的归“本”运动:
“原泉混混,不舍昼夜。
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
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闲雨集,沟浍皆盈;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离娄下》)人的成长过程,即是不断回到自己,不断回归自身本性的过程。
人一旦超出人性的内在规定而“动”,脱离开人性这个“本”而行事,就是“反其本”(《梁惠王上》)或“失其本”(《告子上》),就会造成对人性本有之善的遮蔽而“违禽兽不远”(《告子上》)。
由此,人性向善论(尤其是“天然趋向”说)在形式上同告子的人性白板论虽有所差异,然而就其否认先天本善为人性之内容,否认人性之“本”,以经验论的思维理解人性的动态开放性来说,实则并无不同(8)。
可见,孟子以“善”为“端”而扩充成德的人性本善论,不但没有否定人性所具有的动态开放内涵,恰恰相反,是同其动态的人性观相互证成的。
这正是孟子要以心善言性善(9),并落到心性论(包含性情论)这一整体性的动态论域中讲人性的内在缘由。
三、整体人性论的进路
西方哲学论人性,重在以要素分析的方式对人性进行规定。
亚里斯多德以植物灵魂、感觉灵魂、理性灵魂这样一个三层等级序列来理解人的灵魂。
这种以要素分解方式所理解的人性,不但是“形式”的,也是“静”态的人性论。
诸要素之间因相互排斥、相互独立而无法形成一个内在的有机整体,导致每一要素都只是一种现成的“静态”质素,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
由此,人性与现实的道德之善就没有必然的关联。
亚里士多德以习惯的养成和理智的引导来说明人的德性成就,就说明了这一点。
与此相关,向善论者往往会借用要素分析论的方法来说明孟子的人性观念。
葛瑞汉(A.C.Graham)就认为,孟子的人性理论,是在预设人的“道德倾向”高于“感官倾向”的前提下,来解决人性这两个方面的冲突(10)。
冯友兰在评述孟子思想时也说,人有一个生物本性、一个道德本性,人的本质在于他的道德性(11)以要素分析法来理解孟子的人性观点,在解释孟子的身心观与人禽之辨等理论时都会遇到很多困难(12)。
区别于要素分析论的讲法,孟子采用整体论或者说内在关系论的方式来讲人性。
在孟子看来,人的感性和理性、道德与情欲、身与心、气与志等,都是内在关联的整体。
《尽心上》曰: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公孙丑上》曰:
“夫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
”这都能证明人性诸要素是内在关联的整体。
这种整体论决定了不同于要素分析论从形式上去讲人性,孟子是从内容上去讲人性。
一方面,这克服以某种现成的“静态”质素为人性的缺陷,将人性诸要素理解为一个动态关联的整体(13);
另一方面,诸要素在这种动态关联中,破除了它们在形式上的抽象对立,使人性具有真实的内容(14)。
这种整体论(或内在关系论)的致思进路,赋予孟子所讲的人性不仅仅是动态的,而必然是一涵摄“动”与“定”、统括先天与后天的存在。
换句话说,动态人性之成立,必以“性”的超越常“定”之义为其归依。
孟子以人性之“动”为一返“本”运动,又批评告子脱离开人性之“定”“本”而言“生”的“生之谓性”论,都说明了这一原理。
所以,孟子在“牛山之木”章以“苟得其养,无物不长;
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来揭示人性“动”态内涵的同时,必然以“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来讲人性之“定”。
孟子人性论的这种“动”“定”关系,落实于他以心著性的心性论论域之中(15)。
相对“性”的先验性而言,“心”更具有经验活动的特征。
孟子引孔子之言论心说:
“孔子曰:
‘操则存,舍则亡;
出入无时,莫知其乡。
’惟心之谓与?
”(《告子上》)然而,心的经验活动因本原于性,所以它的活动不是盲目的任意流变,而是始终以“性”的先天“本”“善”内容为其“定”“本”和归依的。
操存舍亡之说,正是以心是否失去“性”这个定本为依据。
这个直接呈现性之本善内容的心,即是孟子说的“本心”。
所以,心性作为一内在整体,二者构成一种互证互成的关系:
“心”以“性”为先天超越之根据,人心有其本然之善与主宰定向,所以孟子讲“大行不加”“穷居不损”;
“性”以“心”为经验显现之落实,人性本善并非悬设而为一真实存在,所以孟子讲尽心知性、知性知天。
由此进路,迥异于亚氏的伦理学,孟子哲学系统中的人性与现实的道德之善,也就存在着必然的关联。
可见,孟子的人性本善论,并不是一套建立在猜想、假设或经验类比之上的理论;
相反,它是在心性论这一论域中所构成的一套逻辑严密的整体系统。
从心以性为“定”“本”和超越之根据的意义上讲,“性”在孟子思想中本来就有“体”性的内涵,尽管孟子没有提出“本体”或“定体”等概念。
宋明儒正是顺遂孟子“定”“本”的讲法,才把“体”称为“本体”或“定体”(16)。
宋明儒以体用架构所建构的理学体系,归根结底只是对孟子人性思想应有之义的发明。
所以是否用体用架构来讲心性,并不构成孟子与宋明儒的本质区别,因为二者是“同出而异名”(《道德经·
一章》)的。
无论是孟子还是朱子等宋明儒,他们所讲的人性都是一先天统摄后天、先验统摄经验、“动”“定”一体的整体系统(17)。
此即大《易》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
乾·
文言》)。
向善论者认为孟子以经验论的方式讲人性,朱子等宋明儒以先验论的方式讲人性,宋明儒的天理本体对于孟子来说乃是一本无必要的空洞预设。
这些说法都是值得再商榷的。
四、“端始”与“端绪”的内在一致性
关于“端”字,《说文·
耑部》说:
“耑,物初生之题也。
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
凡耑之属皆从耑。
”段玉裁注解说:
“古发端字作此,今则‘端’行而‘耑’废。
”对此,有学者指出,孟子的“端”是由“耑”演变而来,它“自含本根与萌芽两义”(18)。
这一论断很有见地,一方面它表明本根与萌芽在时空发生论的意义上具有同步性,另一方面它暗含着本根乃是萌芽作为现实存在的逻辑前提。
前一方面侧重本根与萌芽在现实上的内在统一性,如《论语·
学而》所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的“本”,其实就有萌芽之义。
后一方面则侧重本根与萌芽在逻辑上的先后区分性,如郭店简《性自命出》所讲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即是在强调由天到命、由命到性、由性到情的一个逻辑秩序。
后来宋儒常讲的理先气后、体先用后等,即属于这种讲法。
朱子以端绪义训端即属于逻辑分析的讲法(19)。
“耑”的“下象其根”那部分由于深埋地下,是不可闻不可见的,它只能通过“上象生形”的那部分端绪始能有所显现,所以朱子说“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
在此意义上,端绪之显现乃是以在中之物这一“根”“本”为其逻辑前提的。
朱子的这种讲法实质上是对“萌芽”之为“萌芽”所固有的先天结构的一种分析说明,是对萌芽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揭示。
这种讲法不但不与发生论的讲法相矛盾,相反,它是对本根与萌芽在现实中为何能够同步发生之原因的深层揭示。
所以,“端”不仅具有端始义,同时亦有端绪义,二者归根结底是相通的。
李景林对此独具只眼地评述说:
“‘端’有端绪义,又有始端义。
端绪义,言其为情之缘境当下发见;
始端义,言其为扩充而成德之初始情态。
”(20)
所以,是立足于现实还是立足于逻辑来讲性情关系,就决定着对“端”的具体含义的理解。
从现实上讲,情感是在先的。
情感作为人的原初存在方式,是成就人性、成圣成德的“端始”或萌芽。
人的现实性须以情感为开端始能达成。
上文“始者近情”之说,即依此而言。
这是由表及里、由显入隐、自“动”而“定”、由经验到先验、因用以著体的讲法。
然而若从逻辑上讲,人性是在先的。
人性作为人情的内在基础和可能根据,惟有在人情这一终极环节始能得到具体的显现和落实,因而人情是人性的呈露“端绪”。
上文“情生于性”即由此而言。
这是由本及末、自内而外、自“定”而“动”、由先验到经验、由体以达用的讲法。
当然,这两种讲法是相互涵摄的。
它们是一来一往、一逝一反(21)的关系。
就每一个思想系统之为真理而言,它必然包含此二义于自身之内。
用黑格尔的话说,无论是从现实出发,还是从理性(逻辑)出发,真理最终要达成二者的和解。
孟子一方面讲尽心知性知天(22),立于人情之“端始”而通达性与天道;
另一方面在论证人性本善时又引《诗》与孔子之言说。
“《诗》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孔子曰:
‘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告子上》)天道降而为“秉夷”之性,人性发而为人情之好恶。
这是本乎性与天道而言人情发显之“端绪”。
可见,无论是以“端绪”还是以“端始”来解“端”,二者皆不能否认性与情,“端”与“本”在现实中的同步发生性。
换句话说,“端绪”或“端始”只是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端”与“本”作为一内在关联整体所进行的揭示。
因为真正的现实之物,是同时包含隐与显、“定”与“动”、体与用、先验与经验于自身之内的“大全”。
在此意义上,“端”即是“本”。
孙奭以“端本”来解孟子的“端”,道理即在于此(23)。
“端”与“本”的同步发生,使孟子的善端论与本善论、充端说与复本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从现实上说,任一始“端”都是人之“本”“根”,因为所谓“本”“根”必然是要在它活生生的端绪呈现中才成为本根的,没有端绪呈现的僵死之物不能是“本”“根”。
所以,人性作为人之“本”“根”,必然要伴随着人的成长历程而显现为不同的端绪或萌芽。
因而,“端”并不是人初生之顷的某种普遍本能,而是人性之“本”在不同境遇下的随时显现。
而作为“本”“根”,“端”必然不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消失。
孟子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
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尽心上》)“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是人所本有的,但这个“本”并不是僵死的,而是在“及其长也”的生命存在历程中经由“亲亲”“敬长”之“端”而随时显现的。
所以,基于本真情感所直接显现的良知良能,既可说是人之“端”,又可说是人之“本”。
充扩善端,即是回复与实现人性之本。
“充端”说与“复本”说作为一相互关联的内在整体,共同构成孟子的人性本善论。
综上所论,孟子的“四端”说是其证成人性本善理论的关键环节。
“端”的端始义,重在强调人性乃是以“可欲”之“善”为“端”进至于成圣成德的动态生命实现历程。
“四端”之心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其内容不是指某种现成的质素,乃是指成就圣神之德的初始情态。
由“情”以成性,通“情”而达理,构成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进路。
由人“情”之动以成圣成德的动态人性结构因原初的“可欲”之“善”贯彻始终为其内在基础,故扩充善端的人性动态生成过程实与“反善复始”的人性奠基归本过程合而为一。
这为孟子批判告子离“本”而言“生”的“生之谓性”论及落到心性论这一整体论域中来讲人性奠定了基础。
区别于要素分析论与经验论的思维方式,孟子采用整体论的方式讲人性。
心性一体的整体进路赋予孟子的人性观念具有涵摄“动”与“定”、统括先天与后天的真理性特质。
在此基础上,立足于现实之端始义与立足于逻辑之端绪义以训“端”的两条致思进路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端”与“本”在现实上具有同步发生性。
总之,孟子的“四端”说与本善论是内在关联的整体。
“孟子道性善”实为人性本善,而非人性向善。
后儒《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开篇六字诚可明孟子之义!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孟子 四端 人性本善 为人 性向 论者 理论 误区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如何打造酒店企业文化2刘田江doc.docx
如何打造酒店企业文化2刘田江doc.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