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Word文档格式.docx
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Word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17255389
- 上传时间:2022-11-29
- 格式:DOCX
- 页数:7
- 大小:24.34KB
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Word文档格式.docx
《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核心文献看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一般特色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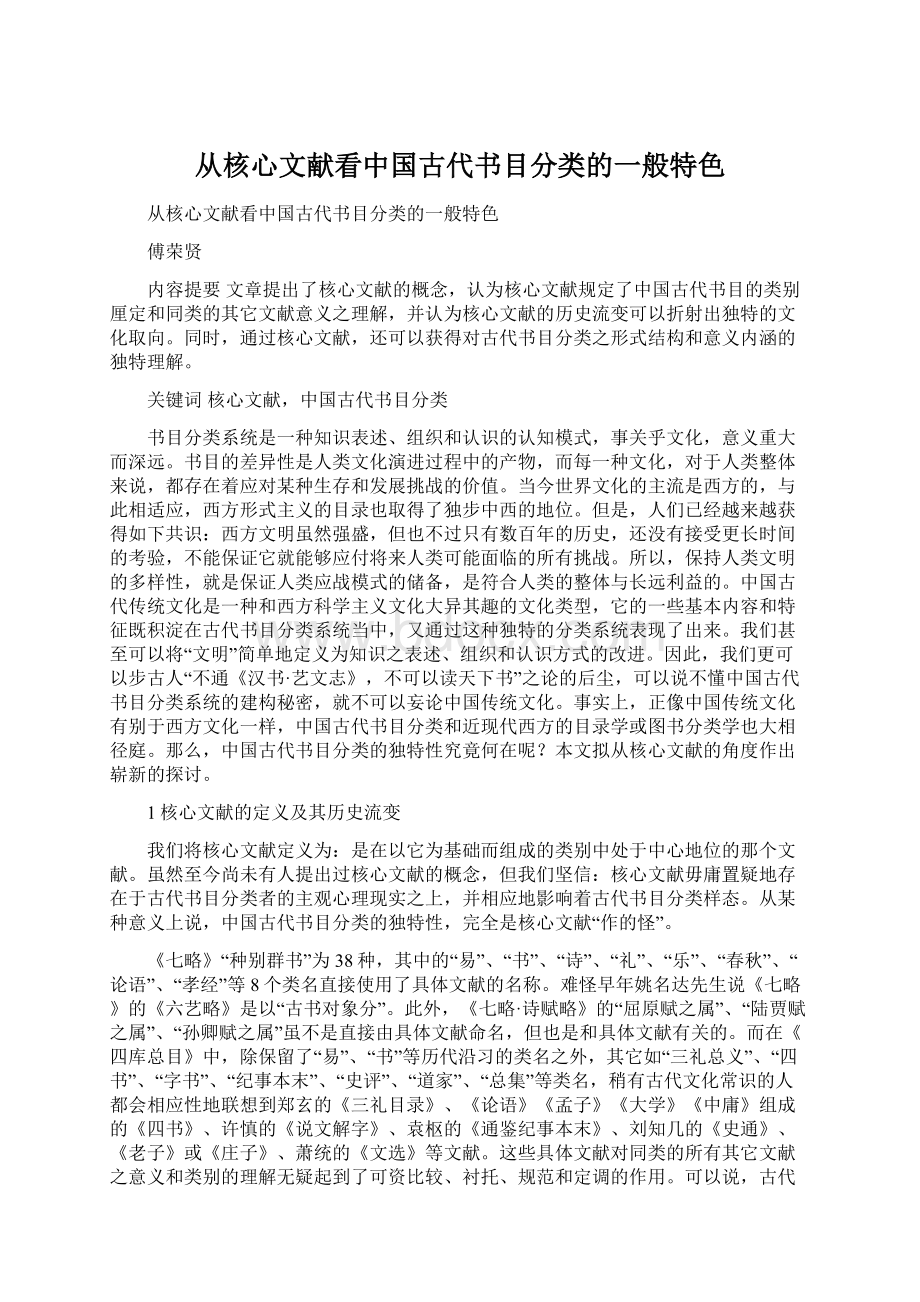
核心文献毋庸置疑地存在于古代书目分类者的主观心理现实之上,并相应地影响着古代书目分类样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独特性,完全是核心文献“作的怪”。
《七略》“种别群书”为38种,其中的“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等8个类名直接使用了具体文献的名称。
难怪早年姚名达先生说《七略》的《六艺略》是以“古书对象分”。
此外,《七略·
诗赋略》的“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虽不是直接由具体文献命名,但也是和具体文献有关的。
而在《四库总目》中,除保留了“易”、“书”等历代沿习的类名之外,其它如“三礼总义”、“四书”、“字书”、“纪事本末”、“史评”、“道家”、“总集”等类名,稍有古代文化常识的人都会相应性地联想到郑玄的《三礼目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组成的《四书》、许慎的《说文解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刘知几的《史通》、《老子》或《庄子》、萧统的《文选》等文献。
这些具体文献对同类的所有其它文献之意义和类别的理解无疑起到了可资比较、衬托、规范和定调的作用。
可以说,古代书目系统的所有类别之厘定,都是和某一个或几个核心文献密切相关的,只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并不十分明显而已。
《四库总目·
凡例》总结说:
“文章流别,历代增新。
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
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
核心文献始终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特征去吸附其它相关文献以组成类列,进而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辐射性网络。
“《东都事略》之属不可入正史而亦不可入杂史者,从《宋史》例立‘别史’一门。
香谱、鹰谱之属,旧志无所附丽,强入农家。
今从尤袤《遂初堂书目》例,立谱录一门。
”[1]可见,核心文献总是代表一种意义和类例特征,限制和驾驭同类的所有其它文献的意义理解;
并可以十分鲜明地将该类文献与其它类别的文献区别开来。
但是,核心文献并不是现成的和自明的,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的不同目录学家会有不同的核心文献观,从而相应地呈现出独特的分类学样态,并进而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
例如《总目·
诗文评类》小序云: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
建安、黄初,体裁渐备。
故文论之说出焉。
《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
《总目》遂以刘勰的《文心雕龙》列于该类之首,成为核心文献。
其它所有“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的文献悉置该类下。
而此前,《文心》等文献“《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文心》乃是作为普通文献,接受其它核心文献——如《隋志》“总集类”的虞挚《文章流别集》——的规范。
方孝岳先生说:
“虞挚的《流别》,既然已经失传,我们就以昭明太子的《文选》为编‘总集’的正式祖师。
……凡是选录诗文的人,都是批评家,何况《文选》一书,在总集一类中,真是所谓‘日月丽天,江河行地’。
那么,他做书的目的,去取的标准,和所有分门别类的义例,岂不是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中,应该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么?
”[2]确实,总集对收入的作品必有所选择,因而涉及文学观;
对文体必有所区分,因而涉及文体分类的具体意见。
总集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密切相关。
所以《隋志》等将《文心》一类著作收入“总集”并非“体例不淳”,而只是理解问题的角度和分类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文心》从普通文献上升为核心文献的过程,也是“诗文评类”从“总集类”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同时还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或学科被广泛认可的过程。
显然,通过对核心文献之历史流变的揭示,可以折射出特定时代的文化取向。
试再举一例。
《汉志·
易类》类首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颜师古注曰:
“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由此可见,汉代人心目中的《易经》是包括《十翼》的。
换言之,《十翼》已经由“传”的附庸身份上升为“经”,地位与上、下篇《易经》同等。
同时还表明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今文易学”的突出地位。
而到了《四库总目》,由于“其编次先后……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3],首先著录了“旧本题卜子夏撰”、“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的《子夏易传》,但该类真正的核心文献是“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十卷。
事实上,该书从唐代始就成了对《周易》十二篇经传作解说的统一答案,以期藉此统一思想、巩固封建专治政权。
可见,核心文献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核心文献的变更不仅导致类例的相应性变更,而且还是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
核心文献确定类名和类别,它可以作为同一区别特征驾驭若干不同的文献,突出它支配其它文献义类的类例特征。
但是,核心文献和其它文献之间的这种决定关系并非单向度的。
事实上,正像《文心》在《隋志》是普通文献,而到了《四库》由于“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被称为“诗文评”的文学批评著作大增而成了核心文献一样,核心文献之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同类的其它普通文献共同推动的。
正是由于普通文献在数量上的增加,使得古代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不能回避或无视它们的现实存在,从而在主观心理现实之上确立了核心文献、进而确立了相应的分类类别,然后再反过来由核心文献统摄、规范其它普通文献。
再如《汉志》春秋类中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按即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而该类的核心文献是《春秋》。
到了《隋志》,《史记》则成了整个“史部”的核心文献。
诚如阮孝绪《七录序》云:
“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
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
总之,众多普通文献是核心文献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者不仅规定了分类类表的厘定并成为同类文献的代表;
而且,核心文献的变化也成了深层文化旨趣的镜像,可以让我们从分类表层样态探知深层文化意蕴。
这样,核心文献便可以成为打开古代书目分类系统建构秘密的钥匙。
核心文献如此重要,以致于它们不仅是古人构筑类别、逐层扩展、形成书目分类系统的关键;
同时也是今人研究古代书目系统的一个全新视角。
中国古代书目是结合具体藏书的分类系统——即便如郑樵《通志·
艺文略》立志“记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兼记了“古今有无”的图书,那些“曾有”的图书也还是具体的——它不像现代分类(如《中图法》)那样,预先设计一套独立的分类表系统、并准备面向未来可能出现的文献。
而在同一类的若干文献中存在一个或几个核心文献,作为该类的正式成员,限制并驾驭同类文献的意义范围和意义识读。
作为古代文化之表述和组织的认知模式,古代书目分类系统是意义内涵和形式结构的有机统一。
从核心文献出发,可以获得对书目系统上述两个层次的全新理解。
2从核心文献看古代书目的形式结构
现代分类体系(如DDC、CC、《中图法》等等)是以学科属性和形式逻辑为两翼构筑的纯粹符号系统。
众多类名及其相互关系的确立是以学术分科和形式逻辑为圭臬的。
整个分类表系统则以类名及其关系为基础而得以建构。
所有类别及整个类表从不必然地和某个具体文献紧密相连,而是以高度的符号抽象性,随时准备类分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文献。
正是由于现代分类是相对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它超越了具体文献的羁绊,因而可以作类号、类名的自组织,成就其符号抽象性。
表现在分类系统的形式结构上,是其相对谨严的等级谱系结构或分面组配结构。
其相应的基本原则则是类名概念的概括与划分或分析与综合,内在思维机制是从类表之一般到文献之个别。
中国古代分类是结合具体文献的,类名所代表的每一类文献都始终存在一个核心文献,这决定了古代分类体系的独特的生成机制。
没有核心文献就不能确立相应的类别,数量更为庞大的文献就难以组织起来。
而和类名、类号(古代分类表中,类名兼起类号的作用)相比,任何文献都是具体的,核心文献也不例外。
这使得执着于核心文献的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的分类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显得具体、可感,内在思维机制是从核心文献之个别到普通文献之个别。
这种以具体核心文献为焦点的分类作业,使得类表系统缺乏严格形式逻辑的约束,其形式结构也不是等级谱系式的,而是以线性次序为基础的结构模式。
首先,古代分类的类名之间——如“经部”和《易》、《书》——虽有等级之分,但古代分类最多限于三位类,并且第一级的“经史子集”只是一种概略性的模糊范畴,既不代表学科或专业,也不是事物或主题的指称。
尤其是,作为上位类名的“经史子集”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安置文献的职能,古代分类体系中没有一本文献是直接安置在“经史子集”等上位类名之下的。
事实上,古代分类中的任何一个完整的类系,如《四库总目》中包含三级类的一个类系:
子部——[天文算法(推步、算书)],只有最下位类(推步、算书)具有安置文献的职能。
如《总目》中,《周髀算经》入“推步”类、《九章算术》入“算书”类等等。
古代分类中,由核心文献确立类别,因而类名从来都不是自足的,甚至也不是自省的(所以,宋王尧臣的《崇文总目》等书目甚至不明确标出“经史子集”等上位类名;
《汉志》也不提供具体类名,而只是在每一类的最后总结说:
凡诗几家几卷;
凡六艺几家几篇等等)。
因而古代分类中被类分的文献并不像类名那样按照等级或从属等逻辑关系来处理,亦即,文献主题并不作逻辑类项的划分。
因此,古代分类不可能是等级几何式的结构模式。
我们认为古代分类是以线性次序为基础的结构模式。
文献和文献之间相互联系的最基本、最有力的方式就是次序。
所以《四库总目·
凡例》中有“至其编次先后”的讨论;
章学诚: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书;
墨家祖墨翟而先有尹佚、田球之书,此岂著录诸家穷源之论耶”?
[4]等等都非常重视分类中“次序”的讨论。
现代分类中使用种次号作为图书到达图书馆的先后次序依据,同一著者的图书不能集中在一起也在所不惜。
这在古代分类中是不可想象的。
因为在同一类中,存在核心文献,它和同一类的其它文献成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必须通过“次序”显示出这种不平等性。
总之,次序构成了传统分类中文献组织的一种“能”,藉此,所有文献在线性体系中得以定位。
文献的表述、组织和认识都离不开“次序”这个最根本的依据。
次序是表述和理解文献的重要手段,次序不同,文献的意义定位和功能理解也就有别。
凡例》云:
“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
如儒家类明曹端《太极图述解》以注周子之书,则列于《张子全书》前。
国朝李光地注解《正蒙》以注张子之书,则列于《二程遗书》前是也。
他如《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之类,亦同此,以便参考。
至于汪晫所辑之《曾子》、《子思子》则仍列于宋。
吕柟所辑之《周子钞释》诸书,则仍列于明。
盖虽裒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
与因原书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
”而就总体而言,《四库总目》的分类次序原则是“《汉书·
艺文志》以高帝文帝所撰杂置诸臣之中,殊为非体。
《隋书·
经籍志》以帝王各冠其本代,于义为允,今从其例。
其余概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
或据所往来倡和之人为次。
无可考者,则附本代之末”。
[5]所以,次序发挥着区别文献意义的作用。
恰当的顺序排列,是组织文献的保证,是文献单元组织的一个重要手段。
而“次序”之如此重要,正是由核心文献在古代分类之类别厘定中的核心地位确立的。
3从核心文献看古代书目的意义内涵
首先,从类名来看。
现代分类的类名是类目的名称,类名规定类目的含义和内容范围,既可以表达学科或专业,也可以表达事物及其方面。
体系分类法类名的涵义,除大类类名之外,大多要受其上位类、下位类以至相关类的限定。
因此,现代分类类名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内在逻辑性,分类号的配套使用使得其逻辑性达到极致,整个类表因此而显示出极强的高度符号化和抽象性。
古代分类中,类名是由核心文献确立的。
因此,古代分类中虽然存在概念化的类名,但文献分类编码的思维起点并非抽象化倾向的类名而是可以引起丰富联想的、有直观表象倾向的核心文献。
当现代分类的类名结合类号进一步抽象化、符号化的时候;
古代分类的类名则结合具体的核心文献进一步具象化、感性化。
从个别的核心文献来观察思考,进而从具体文献之间去观察其秩序和关系以建立分类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分类体系建构的基本秘密。
古代分类总是在核心文献之具象的基础上另加类名来标指一类文献,而不是像现代分类那样从类名一般出发来给文献个别加以编码。
所以,古代分类的类名往往并不是学术分科或逻辑信念意义上的——即便如大声疾呼“书以学类”的郑樵,其《艺文略》也没有给具体类名以严格的逻辑界定[6]——因此,类名作为类目名称的抽象性总是大打折扣。
或者说,人们即使对类名的抽象本质不甚了然,但却能通过具体的核心文献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其丰富内涵,并获得生发联想的巨大空间。
从而使得整个分类类表免除了许多额外赋予的规矩。
现代分类中的标记规则、标引深度、标识专指度与标引专指性规则、标引一致性、词汇控制、点序列原则、多重列类法、多重属分关系、分段标记制、仿分、分类标引规则、分类特殊规则、复分规则、混合标记和单纯标记规则、兼容性原则、借号规则、空号规则、类链规则、配置原则、起讫标记制、亲缘序列规则、适应性原则、术语使用规则,同类号规则、稳定性原则等等其功能都是描述性的,观察角度是固定的,表达是精确的。
但这些规则多不构成古代分类的约束标准,因而也不被视为学术课题加以专门讨论。
古代分类中,即使有一些规则,其规则的控制能力也很弱,如果有必要,规则就会让步。
古代分类从具体的文献着眼,因此,类名表达往往言简意赅,蕴藏着丰富的语义感受,由此组合的分类表系统也成为可感之具象系统。
从核心文献入手,在组织文献的过程中,更多地交待感受,并力争引起分类解码者的共鸣,实现检索目的。
抽象化的类号因而显得多余。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书目分类史上,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和东晋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使用干支类号的两部书目。
“自宋以后,始无复有以甲乙分部者矣”[7]。
所以,即使是在典籍事业十分发达的清代,人们对标识四部图书的“甲乙丙丁”诸符号也很不了解。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俞樾《古书疑义·
寓名例》等都要强调指出:
甲乙丙丁不是事物之名,而是借用的符号。
事实上,正是由于具体的核心文献的存在,才使得古代书目分类采取了无比坚定地排斥抽象化标识符号的做法。
其次,就文献及其关系而言。
现代分类中的文献类分是通过类名(及类号)所表示的类别来实现的。
类别化是判定一个特定文献是或不是某一具体类别的能力。
没有类别化,我们将永远无法对众多文献进行有效地组织。
而这里所谓的类别是由必要和充分特征联合定义的,其特征是二分的:
第一,类别有明确的边界;
第二,同一类别内的所有文献地位相等。
这两个特征其实就是逻辑学的特征。
但是在古代书目分类中,由于核心文献的存在,导致几乎所有的类名都不可能显示出必要和充分的标准;
同一类的文献成员之间的地位也不相等。
核心文献具有特殊地位,规定着类名的产生和更迭,被视为该类别的最理所当然的正式成员,其它非焦点的普通文献则根据与核心文献的关联程度和相似程度而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非正式成员地位,从而无法确保其逻辑平等性原则。
古代书目分类体系作为文献表述、组织和认识的认知模式,其最终目的是阐明具体文献的认知过程。
当我们通过文献类例(提要和小序等文字性成分是配合“哑巴”类例发挥功能的)来知解文献时,必须考虑类别有核心和边缘这个事实。
事实上,一个普通文献赖以得到知解,正是依赖另一个作为类别焦点的核心文献而实现的。
在观察一个普通文献时,尽管它更像是从属于某个有着众所周知内涵的类名,但它的具体内涵其实是根据它和核心文献之关联性的“具体程度”而获得的。
选用一个类名,只是表明分类编码者为某种表达目的而构造其概念内涵,本质上并不必然地有助于具体文献之意义的理解。
一个文献赖以得到整序和解释,是依赖另一个作为类别核心的核心文献实现的。
无限文献则通过映射到有限核心文献上实现整序和理解。
同一类的文献都可以通过核心文献为焦点建立一定的联系,进而衬托其意义。
核心文献是具体的,这避免了现代分类在类名和类号之抽象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类别稳固化或曰僵固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某文献识读的误导。
中国古代分类系统不致力于精确地表述规则、没有非此即彼的、冷静的客观分类原则;
相反,它本质上不把文献的客观物理特征和学科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涵的主体意识出发,按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文献以某种意义。
而正是具体的核心文献的存在,才使这种主客一致、物我相谐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
古代分类以核心文献为参照,经历了由具体观念到关系观念的价值转移,它不至于像现代分类那样进入严格逻辑化的等级谱系或分面分类结构中增加或减少文献的固有意义。
因为古代分类系统不是明白确切的概念和判断,而是借助于核心文献以引起丰富联想的直观表象。
它的思维过程往往是跳跃的、多向的和随机的。
不是在推理中得出结论,而是在具象的排列中悄悄展开抽象过程,体现结论,使思维的抽象运动形象可感,并伴有情感的波动。
总之,核心文献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书目系统中类别的厘定,而且决定了文献的整序和理解。
后者则决定了文献整序和理解的具象性,把想象、情感和理解诸因素引向“关系”观念而不是引向某个抽象、确切的东西。
4结语
和建立独立的分类表系统、并借助于类名、类号显示符号抽象性的现代分类不同,古代分类是面向具体文献的。
在所有具体文献中,存在一些核心文献,它们构成了古代分类的生机机制,分类类别及其整个类表的编码都是围绕核心文献这个中心而展开的。
以核心文献为基础,从个别化的核心文献来观察思考,进而从若干具体文献之间去观察其秩序和关系以构建类别,进而成就分类体系。
只要某个文献在分类编码者的主观心理现实之上取得核心文献地位,就可以确立相应的类别,并统领同类的其它文献。
抓住了核心文献的概念就可以在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书目分类现象中找到内在联系,进而为古代书目系统的生成指明陈述的方向;
并建立一种有说服力的系统结构规则。
参考文献:
[1][3][5]四库提要·
凡例[M].
[2]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M],上海:
三联书店,1986年.63.
[4]校雠通义·
卷一[M].
[6]傅荣贤.郑樵目录学思想的理论背景[J].福建图书馆学刊,1997,
(1).
[7]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目录类例之沿革[M],成都:
巴蜀书社,1991.
傅荣贤:
江苏盐城师院图书馆。
转自《四川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5期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核心 文献 中国 古代 书目 分类 一般 特色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如何打造酒店企业文化2刘田江doc.docx
如何打造酒店企业文化2刘田江doc.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