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
论文: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
- 文档编号:1676823
- 上传时间:2022-10-23
- 格式:DOC
- 页数:13
- 大小:45KB
论文: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
《论文: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文: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doc(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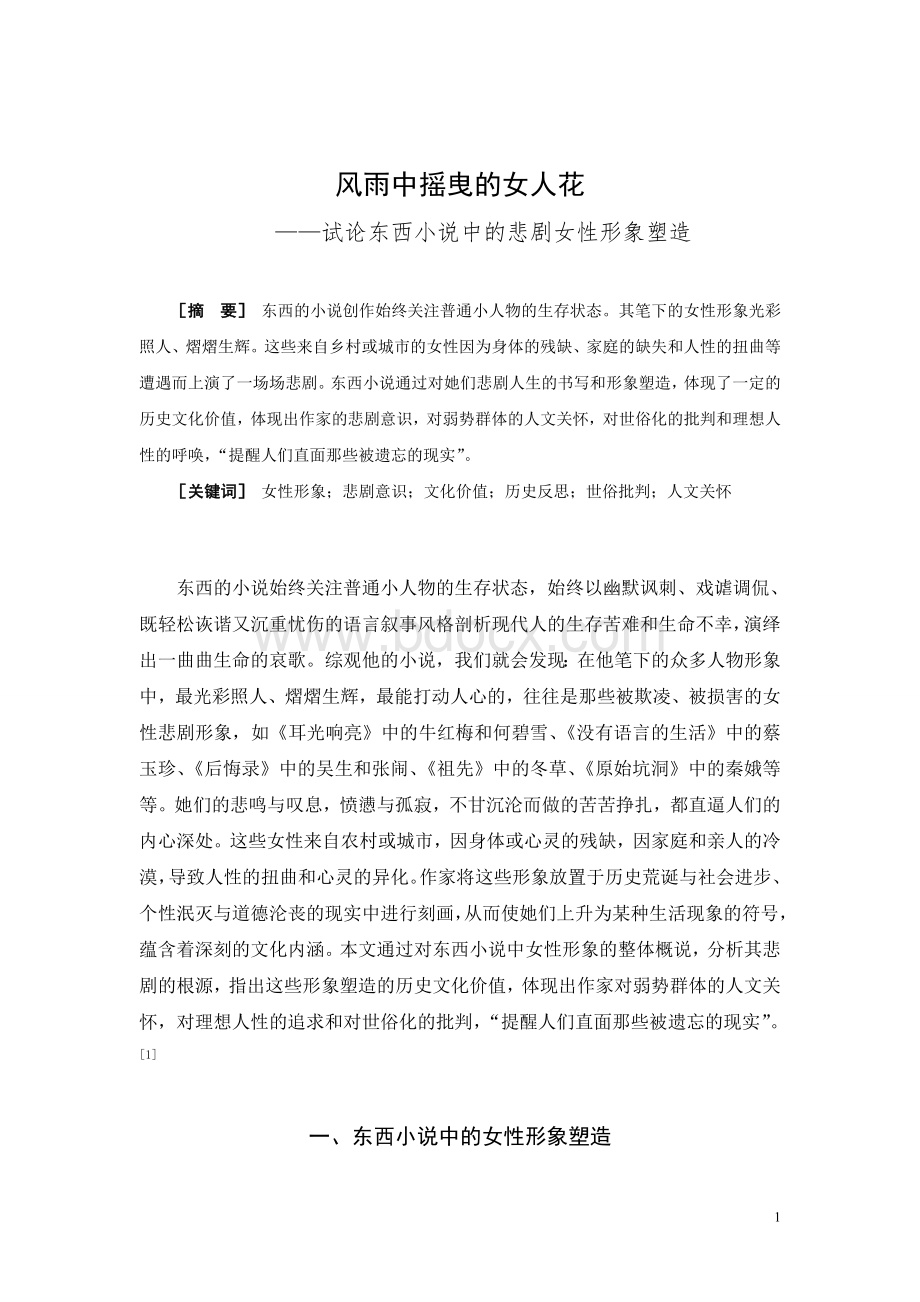
风雨中摇曳的女人花
——试论东西小说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塑造
[摘 要]东西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这些来自乡村或城市的女性因为身体的残缺、家庭的缺失和人性的扭曲等遭遇而上演了一场场悲剧。
东西小说通过对她们悲剧人生的书写和形象塑造,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作家的悲剧意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世俗化的批判和理想人性的呼唤,“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
[关键词]女性形象;悲剧意识;文化价值;历史反思;世俗批判;人文关怀
东西的小说始终关注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始终以幽默讽刺、戏谑调侃、既轻松诙谐又沉重忧伤的语言叙事风格剖析现代人的生存苦难和生命不幸,演绎出一曲曲生命的哀歌。
综观他的小说,我们就会发现:
在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熠熠生辉,最能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被欺凌、被损害的女性悲剧形象,如《耳光响亮》中的牛红梅和何碧雪、《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蔡玉珍、《后悔录》中的吴生和张闹、《祖先》中的冬草、《原始坑洞》中的秦娥等等。
她们的悲鸣与叹息,愤懑与孤寂,不甘沉沦而做的苦苦挣扎,都直逼人们的内心深处。
这些女性来自农村或城市,因身体或心灵的残缺,因家庭和亲人的冷漠,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异化。
作家将这些形象放置于历史荒诞与社会进步、个性泯灭与道德沦丧的现实中进行刻画,从而使她们上升为某种生活现象的符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本文通过对东西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概说,分析其悲剧的根源,指出这些形象塑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出作家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对世俗化的批判,“提醒人们直面那些被遗忘的现实”。
[1]
一、东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古今中外,一致地把女性比作花,可惜的是由于现实生活中无情风雨的摧残,本应盛开的花却往往早早地飘零、枯萎、凋谢了。
东西从生活出发,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提取素材,描摹女性的悲哀与挣扎,以一个作家的独特见地挖掘蕴藏在女性身上的巨大力量。
东西的创作经历横跨乡村和城市两大“部落”,不仅将笔触聚焦在自己熟悉的乡土记忆中的农村女性,也瞄准了游弋在城市边缘的“都市女性”(并未真正融入到都市大潮流中)。
作家轮番在这两片净土上耕耘,不断创造出处于弱势地位的生命之花。
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不管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些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中真实可信的形象,历史跨度大致锁定在上世纪60年代至社会急遽转型时期,但也有几个形象是置身于解放以前,如《祖先》里的冬草和竹芝、《白荷》里的白荷、《相貌》里的云秀、《断崖》里的盘四妹等。
作家对她们并没有浓墨重彩,只是以拉家常式的笔法,使人物的主要特征凸显,女性形象便呼之欲出。
(一)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
叙事主体与文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作家在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追求、理想等主观因素融进作品。
对生于桂西北农村并从小深谙农村生活的东西而言,乡土记忆没有理由地成为其仰仗的文学资源。
作家对贫苦有着深刻的体验,“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贫苦疾病是家常便饭”。
[2]他非常重视题材与作家自身之间的亲密性,于小说中极力描摹与控诉苦难,于苦难叙述中对在贫困生存环境下和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的经历极力渲染,对土地和祖辈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审视。
《祖先》中桂平巨贾冬铁甫的女儿冬草,“为了爱情”,怀着一颗良德之心,辛辛苦苦把丈夫光寿的灵柩护送到乡——一棵枫,却被光寿的原配竹芝拘留下来,供给村里的男人淫辱以换取水田,后来又被迫嫁给一个丑陋无比的男人扁担。
在这个物质生活贫困、人们素质不高的地方,冬草就这样先是充满屈辱然后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最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妇人。
通过这妇人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乡土的力量和人物的忍辱负重精神。
乡土的强大力量溶解了一切,无情地塑造着生活在它怀抱里的人的历史,而人在其中无可奈何却顽强挣扎。
小说中的另一女性竹芝的命运更加悲惨,水田被儿子见远嫖光后只能靠磨魔芋、吃魔芋度日。
死后就因为一对玉镯,她的坟墓当夜被人挖开,尸体被狗撕咬成无数块。
两个女人的遭遇都很特殊,却包含着普遍的意义:
命运难以抗拒,为了生存,先辈们不得不负重挣扎,在命运之途上苦苦跋涉。
《目光愈拉愈长》的农村妇女刘井,命运也如冬草一般悲惨。
她的不幸,来自好吃懒做的酒鬼丈夫马男方的无端猜疑和伤害,来自丈夫的妹妹马红英竟然拐卖自己侄子的丑恶行径,来自儿子马一定的丢失和出走。
灾难纷至沓来,给这个无助的农村妇女一次又一次打击和伤害。
她想反抗,想逃离苦海,要与丈夫离婚却不被允许;思儿心切却只能将目光拉长,想象儿子过上好日子的情景。
此时,我们不得不折服于这种女性抗争命运呈现的生存奇观和背后蕴蓄的原始伟力。
刘井也因此名副其实地成了当代乡村苦难女性的代言人。
(二)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
改革开放后,城市以其未曾料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改变着、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步入城市后的东西以独特的视角揭示转型时期现代都市女性的心态和生活相。
她们游走在都市,贪婪地攫取着,肆意地放纵着,疯狂地享乐着,传统的道德素质已被堂而皇之地放弃。
她们或被生活所迫,或为利益所诱,从而通过征服男人实现对金钱的占有欲并乐此不彼。
《美丽金边的衣裳》里的希光兰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以青春和美貌作为资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接近幸福的筹码,以“玩爱”的方式心安理得地放纵自己。
她玩弄、勾引、调戏着男人也被男人玩弄、勾引、调戏着。
她是盛开在都市里的罂粟花,美丽而淫邪。
希光兰是一个沉溺于物质享乐的现代都市女性,但她对于人生、都市生活和自己并没有清楚地认识。
换言之,她只是一个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个大潮流中。
这正是东西的本意:
不是展现种种光怪陆离的城里人生活,而是否定城市生活的虚假繁荣,进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与灵魂。
现代文明城市五彩缤纷的生活同样诱惑着乡间纯真的少女。
她们试图逃离贫穷的土地,企图摆脱沉重劳动的束缚,跻身一直存在于幻想中的自由、文明的现代都市生活。
《勾引》中从高高的玉兰山被勾引到城市餐馆打工的十七个少女,《美丽金边的衣裳》中的李月月、崔英,无论是本不知情的身不由己,还是本就清醒的心甘情愿,她们的盲目及其健康饱满的身体已成为现代化盛宴一道可口的佳肴。
她们将自己的青春叠成一叶扁舟放逐于高度物化、欲化的世俗大海之上,没有人在意它起于何处,更没有人思考它将飘向何方。
因此,不管她们怎么努力,都只能沦落在城市的边缘,成为城市“飘族”的一员。
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物及其行动统统看作作者意图的不同侧面在文本中的影射,那么这些女性的空虚体验无疑是作家对世俗生活的强烈焦灼和深深迷茫。
东西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女性世界。
无论是苦难中挣扎的乡村女性,还是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女性,她们都处于卑微的地位,被苦难和欲望压得喘不过气来,看不到希望。
迫于生活的无奈,她们的灵魂早已罩上了陈腐世界的阴影。
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败落和人性的卑琐,见证了人在苦难面前、在物质面前的卑微屈膝和渺小。
二、东西小说中女性形象悲剧分析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东西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真诚直面当下的生活本质、人的灵魂和人类面临的困境等诸多问题,着意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以悲剧的形式去展示生命的不幸、生活的苦难和生存的艰辛。
正如他所说的,“我是一个悲剧的鼓吹者,所以我常常写悲剧,这使许多读者认为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其实悲剧意识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童年一睁开眼睛就没有喜剧的舞台,所以悲剧就深入骨髓无可救药。
”[3]正是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他所描绘的女性形象的遭遇汇成了一幅幅生存的悲剧画面。
(一)身体的残缺
有人将东西的创作称为“身体写作”或“器官写作”,因为“东西的小说总是专注于对人的感觉器官的感觉”,[4]塑造人物也倾向于“由于身体器官的残缺造成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困境,由此对人物的命运所造成的影响”。
[5]东西极力写作平凡女性身体的残缺,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或是同情,而是向人们诉说现代女性的一种人生遭遇,直问人心:
在讲求人人平等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真正做到人人平等了吗?
无数的女性还是因为身体的残缺而受到歧视、凌辱、虐待,努力追求生活上的完美却遥不可及。
《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的哑巴蔡玉珍为生存来到偏远山村推销毛笔,阴差阳错地与瞎子王老柄、聋子王家宽成为一家,在本就贫困的农村背景下举步维艰的生活,以残疾之躯承受着外人强加的伤害和因没有语言而沟通失效带来的困顿。
但是,当她与父子俩齐心协力抓强奸犯时,那种“语言”上的对话不得不令人折服于这种沟通方式呈现的生存奇观。
蔡玉珍生活在这样一个由聋哑瞎组成的特殊家庭里,她的生存悲剧在于拥有真理而不能言说,取而代之的是欺辱和歧视。
她的遭遇揭示了现代社会人性道德的急速下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伤害。
《迈出时间的门槛》里的祖英妈和《经过》里的刘水的遭遇更加不幸。
由于穷乡僻壤的原始和闭塞及历史行进脚步的滞后,祖英妈与命运搏斗却造成了悲剧。
她试图用火枪阻止丈夫的不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由于历史的捉弄而成了枪下的牺牲品。
瘫痪后的祖英妈已无力管制丈夫和寡妇的野合,无法忍受而不得不离婚,改嫁给远村的一个傻子。
得不治之症的刘水,远道而来向一个私人医生求医。
没想到,她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无法走出去,被围困在这个大门紧闭的诊所里,成为医生及其儿子肉欲的对象,任受摆布,想逃却无法逃脱,最后忧郁而死。
求医治病是为了走出人生困境,但却走不出人为制造的障碍。
无论是哑巴蔡玉珍、瘫痪的祖英妈,还是得不治之症的刘水,她们都因为身体的残缺,不同程度地受到世人的歧视、凌辱、践踏。
如果说身体生理性的残缺是上天注定的话,那么身体社会性的残缺就是人类社会造就的悲剧。
作家透过女性身体的不幸残缺,挖掘出历史的荒诞,社会进步而人的精神世界仍无所依附的磨难。
作者正是通过身体感官的残缺这一层面透视现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使文本获得一种形而上的意味:
在现代文明支离破碎的今天,人类还能前行多远?
是走进自己编造的绞索呢?
或是退守到原始的状态之中以保存那点美梦?
(二)家庭的缺失
家是温馨的港湾,是疲惫的灵魂得以休息的心灵驿站。
对于女性来说,家更是意味着一切。
家在女性的灵魂深处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女性物质和精神生存的源泉。
而东西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却没有温馨融洽的家庭,有的只是亲情的缺失、冷漠和对立。
《耳光响亮》里牛红梅的悲剧命运正是从父亲牛正国失踪后延续下来。
父亲的失踪,则意味着家庭的缺失,牛家人的生活和命运失去了依靠,变得无序混乱。
母亲的再嫁,使牛红梅的悲剧命运踏上了不归之路。
试想,如果父亲不失踪,母亲不改嫁,牛红梅就不会遭受宁门牙的无理强暴,就不会有“借腹生子”这一荒唐协议。
在牛红梅这段青春扭曲的成长史中,东西始终将悲剧性的故事情节安置在这个具有血缘家庭的内部,用家庭的缺失,父母的缺席和时代的动乱来彰显造成牛红梅悲剧命运的社会和家庭根源与可怕后果。
与牛红梅同样命运的,还有《白荷》里的白荷,《迈出时间的门槛》里的祖英,《相貌》里的云秀。
她们不幸命运的源头除了社会历史的原因,也均来自家庭的缺失,亲情的背叛。
或为了亲人的温饱,或为了逃离后母的虐待,或为了戏班的兄弟姐妹,她们不得不搭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在自然和家庭的双重奴役下命运变得如此不堪和不幸。
东西的目的,或许在批判社会荒诞历史的同时,还在于点燃现代人心中那关于家庭伦理亲情的火种,唤醒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让人们体验到作为一个鲜活的人的家庭需要和情感需要。
东西构建了众多生活在残缺家庭的女性形象,将笔触指向家庭缺失后她们的生存状态。
因为家庭的缺失就意味着她们必须无条件地面对自己的不完满状态,在不完满中只能以自己的身体去实现生命最大的完满。
(三)人性的扭曲
东西小说塑造了一个丑陋而扭曲的世界,各式各样的女性在时代的挤压下,在卑微晦涩的现实缝隙中,为生存而努力挣扎,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苍白麻木的精神重负。
没有大人物的大悲大喜,有的只是小人物的处心积虑,她们为生活所累,又不得不臣服于生活。
她们追求真理却达不到真理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论文 东西 小说 中的 悲剧 女性 形象 塑造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12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实施细则_精品文档.doc
12处方点评管理规范实施细则_精品文档.doc
 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_精品文档.xls
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_精品文档.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