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屯军自耕农化浅析文档格式.docx
明末屯军自耕农化浅析文档格式.docx
- 文档编号:16560102
- 上传时间:2022-11-24
- 格式:DOCX
- 页数:12
- 大小:36.92KB
明末屯军自耕农化浅析文档格式.docx
《明末屯军自耕农化浅析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末屯军自耕农化浅析文档格式.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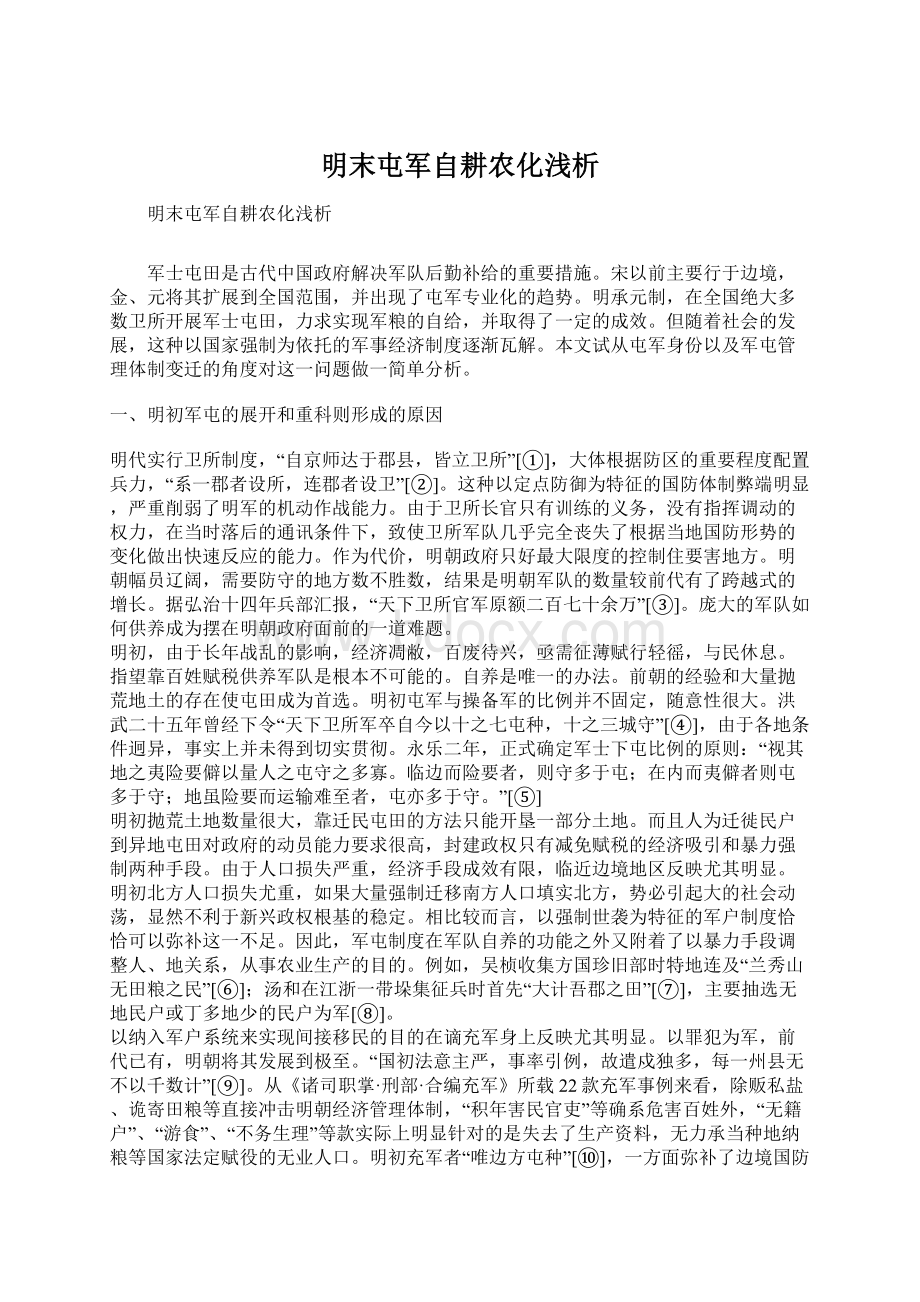
明初北方人口损失尤重,如果大量强制迁移南方人口填实北方,势必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显然不利于新兴政权根基的稳定。
相比较而言,以强制世袭为特征的军户制度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因此,军屯制度在军队自养的功能之外又附着了以暴力手段调整人、地关系,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
例如,吴桢收集方国珍旧部时特地连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⑥];
汤和在江浙一带垛集征兵时首先“大计吾郡之田”[⑦],主要抽选无地民户或丁多地少的民户为军[⑧]。
以纳入军户系统来实现间接移民的目的在谪充军身上反映尤其明显。
以罪犯为军,前代已有,明朝将其发展到极至。
“国初法意主严,事率引例,故遣戍独多,每一州县无不以千数计”[⑨]。
从《诸司职掌·
刑部·
合编充军》所载22款充军事例来看,除贩私盐、诡寄田粮等直接冲击明朝经济管理体制,“积年害民官吏”等确系危害百姓外,“无籍户”、“游食”、“不务生理”等款实际上明显针对的是失去了生产资料,无力承当种地纳粮等国家法定赋役的无业人口。
明初充军者“唯边方屯种”[⑩],一方面弥补了边境国防力量的不足,一方面又起到了强制流民回归土地,徙居、填实宽乡的目的。
这一施政导向为朱家后代所继承,不时予以运用。
如宣德五年,政府在处理外流人口问题时规定:
“不还者,同藏匿之家俱发所在卫所永充屯军。
若军卫屯所容隐者,逃民收充屯军,容隐之人依隐藏逃军例发边卫。
”[11]
要实现自养,屯军除了必须生产出保证自己最低消费的粮食外,还要提供相当的粮食供不下屯的军士食用,这决定了屯军必须按照较高的科则上缴粮米。
洪武年间,由于军屯刚刚展开,对军屯的科则没有统一的规定。
如太原、朔州等地的屯田一度免税[12];
西安等地屯田“税粮与民田等”[13];
凉州、西宁一带则以“十之二输官”[14];
宣州卫“岁征其半,余存自食”[15]。
尽管税制复杂,科则不一,但逐渐抬高税则,提高军队自养率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
例如洪武四年规定河南、山东等处屯田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16],远远高于民田。
到永乐年间,军屯已经全面展开,加之大规模的战争不断,对军粮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军屯科则出现大幅度的提高。
建文四年,朱棣上台后不久即宣布“每军田一分纳正粮十二石,余粮十二石。
正粮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上交,供本卫官军俸粮。
”[17]不过由于科则提高过多,能否实现朱棣自己也表示怀疑,因而在永乐二年制定屯田赏罚例时规定只要屯军余粮达到六石就算过关,管屯官不予处罚[18]。
永乐十二年,因屯军实在无法完成规定税额,朱棣不得不下令“余粮免其一半,止纳六石”[19],这一科则后来一直沿用到英宗即位。
洪武、永乐时期,屯田科则居高不下的原因,后人只是称“其田科则之重亦良有深意”[20],但未加深论。
笔者认为,所谓深意当与苏松重赋相同。
明初百废待兴,急需与民休养生息,但新政权的创建和尚未终止的与北元的战争都需要财政支持,能两方面兼顾的唯一方法是与绝大多数百姓休息,将轻徭薄赋的损失转嫁到局部头上,牺牲部分百姓的利益。
苏松地区经济较发达,自然成为“剪刀差”的对象。
至于苏松地区长期支持张士诚该受惩罚等理由纯属冠冕堂皇,表面文章。
明初军需众多,绝非百姓所能承受,世袭军户制度提供了稳定兵源,加大对屯军的剥削顺理成章。
只是此类深意不便明言,只能用“寓兵于农”之类理由掩饰。
为使屯军有能力完成任务,明朝政府转而牺牲部分民户的利益,大量拨膏腴田土与军,并且不限制屯军适当额外占田。
在河南,“国初重军伍,必先置屯田而后及于民,故屯之地腴而亩又赢”[21];
在安徽,“草昧之时,地广人稀,军强民弱。
方初下屯时,所占田地无限制,且未丈量,未经拨补,田亦有余,既经拨补,田益增羡……故今屯田一分,少者不下百亩,多则数百亩”[22];
在江西九江,“其上田皆属南昌九江卫,而次者以授民”[23]。
至于边境地区,土着居民本来就少,屯军占地所受限制更少。
当然也有例外,如河间府,由于开屯较晚,肥沃土地大多被民户占有,“屯田之地皆受而薄者也”,但“犹幸其田羡而可资也”[24]。
又如贵州基本为喀斯特地貌,土壤肥力很低,不适宜农耕,且分布星散,但由于数量有限,贵州屯军无法多占田土,一分地仅18亩[25]。
明初,“民多流离失恒产”,加之军官大多“畏法不敢虐下,故建卫从军,多安其役”[26],军屯取得了一定成效,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明中期的户部要员认为“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27]。
这种说法后来日渐增加,以至于影响到很多现当代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
其实,明初军屯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
万历时两广总督殷正茂在分析广东卫所屯田时指出:
广东卫所军原额约13万零900人,现存支粮食俸官军约3万人,每年消耗军粮米352000余石。
“查计原额屯田七千一百二十四顷有奇,纳米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二十三石,是以原额之屯供今日消耗之官军尚且不足,而必取资于民粮。
况国初官军全盛之时乎?
则有军有田之说或当时经略详于九边而略于边海,未可知也。
”[28]殷正茂不敢断言的九边屯田,成效也并不很好。
笔者在《明承元制与北边供饷体制的解体》一文中曾考证过大同地区军粮供应的主体始终是民运粮[29]。
宣府、蓟镇、延绥、固原等镇保留下来的屯田数据基本是正统以后的,无法反映明初情况。
但这些边镇从国防形势、下屯比例、土质条件、气候以及耕作水平大致和大同地区相当或更差一些,军屯发挥的作用应不至于有大的出入。
唯一不明确的是辽东。
正德时山东巡按周熊奏报辽东“永乐间常操军士凡一十九万,以屯粮四万二千有余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30],屯军所产不足全军食用;
天启年间户部臣则说“永乐十年辽镇岁收屯粮七十一万六千一百余石,以养该镇官兵九万余,京运亦止一万石而已”[31],军屯所出几乎完全满足全军需要。
不过二者都说明了一点,即辽东镇的军饷供应主要靠自己解决。
考虑到辽东地区明初政局一直很稳定,且大部分地区土壤腐殖质含量很高,土质肥沃,适合农耕,军屯生产水平较高应该可信。
不过这只是局部特例,并不代表全国水准。
明朝实行世袭军户制度,违背商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员和职业自由流动的要求。
屯军不仅要世代从军,还要被长期束缚于土地,既无土地所有权,又不能自主决定种植品种与方式,且屯田子粒远高于民田,俨然是政府的农奴。
低下的地位决定了明朝军屯必然败坏的结果。
明朝屯政败坏的过程也既是屯军争取摆脱低下地位的斗争过程。
对于屯政的破坏,以往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势要占耕屯田。
势要占田、占役军士的现象确实存在,且很严重,但终归有个限度。
势要为维持占役军士必要的再生产能力,必须给予其相应的种子、牛具以及休息时间,否则会召致其暴力反抗。
官与军之间的“阶级合作”应是明朝大部分时间内的主流,这一点从明朝中后期兵变的动因中即可以看出。
屯军的大量逃亡是其主要的反抗方式之一。
但这对于未逃屯军而言,逃亡屯军遗留下的大片屯地恰恰给其创造了另外一种摆脱困境的方式,即屯田私有。
个人认为,通过二百余年的努力,存留的大部分屯军已基本摆脱了事实上的农奴身份,转变为拥有土地的自耕农。
屯军要摆脱政府的严格控制,需要实现以下几个目标,即屯地私有、土地税则和民田统一以及解除服兵役的义务。
以下将就这几个问题分别论述。
二、屯地的私有化
获得事实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屯军首先要解决的问题[32]。
明初,为实现卫所之间的相互牵制,在屯地的分配上往往相互交错,不同卫所的屯田共处一地,本省卫所屯田远在隔省的现象很普遍,像直隶宁山卫戍地在山西泽州,屯田则分布于河南以及北直隶大名诸府县。
山西潞州卫屯田散布于河南、北直隶两省三府九州县。
偏桥、镇远等卫地处贵州却隶属于湖广都司。
极端的例子如南直隶定远县一县分布有南京英武卫等7卫屯田[33]、湖广均州守御千户所屯田散布于72处[34]。
这种“相维相制”的屯田分派办法以及由于江南水网密布,福建、两广等地山岭多地块小造成的屯田分散交错,给屯田的管理带来相当的困难,屯官很难有效巡视。
加之军政腐败,屯官怠惰,“优游城市,而不见阡陌之巡”[35],更使屯田管理近于无政府状态。
屯军可乘机私相典卖,无所顾忌。
明代屯田还兼有其它功用,简言之即“北方之屯田重在盐法,兼重马政而行之也;
中州之屯田专重马政而行之也;
浙直之屯田则以屯军子粒供造运船之用,有余者充补月粮;
福建则又不然,其屯田至多不若浙直之少”[36]。
这使卫所屯田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管理体系不统一,政出多门,容易相互推诿。
这无疑是屯军隐占屯田的良好条件。
屯军隐占屯田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即隐入民田、混入寄籍和隐入轻科余田。
明朝军屯不仅各卫交错,而且还常与民田相杂,在人口较为稠密的腹里如此,在边境亦然。
如大同,“军民杂处,地亩相连,加以王府牧马草场、将官养廉田地及随侍官校免买民屯,互相参错,若犬牙然”[37]。
民、屯田混杂的一个结果即军、民之间可以相互买卖甚至强占对方田土。
在明人的记载中大多强调屯军无理抢占民田。
例如:
缘海诸屯卫帅暴横为民害,往往择民膏腴田诬为荒废,据占自利,郡县不能制。
[38]
南京锦衣等卫屯田多在应天并直隶庐州、滁州等处地方屯种,递年夺占民田,不纳子粒。
及直隶苏州、建阳等卫所屯军亦如之。
[39]
弘治末年,因出清查事例,各军生奸,指邻近民田报作己力开垦,遂增余田名目……军田大率间杂民田中,四旁非尽山地,何自开垦?
军之余田,乃民之虚粮。
册籍已成,征收日久,小民赔粮,无能辩诉。
犹曰往事可诿也。
目今军人生奸得惯,沿袭而来,凡屯田系是水冲沙压、水涸抛荒,往往指邻近田为己田原有之数。
一佃其田,百端生害。
[40]
武黄二卫永乐中来屯,注籍强半。
恶有溪山,圈之。
而屯京山、黄陂。
所籍之田听民占焉,增税于官。
其籍犹藏武之史高氏。
弘治中,议覆屯。
高之后怀籍私示京民,曰:
“汝执此,不即嫁于彼乎?
”京人从而诉焉……自是注籍之家,田不加多,既输民租又纳军税。
侯……力白诸统,异议,不报。
惜哉!
[41]
成建制的军人和缺乏统一领导的民人相比优势明显,难免会不时争取获得一些额外之利。
类似现象如果不遇上敢碰硬骨头的地方行政官员干预,很可能会成为既成事实,一直延续下去。
史籍中多载军人夺占民田的原因与武臣通文墨者少,留下的史料稀少,现存史料的提供者大多是行政官员有关。
不过民户占有军屯土地的例子史籍中也不难找到。
如张燧称:
“屯政侵欺之弊难以枚举。
第所以致此极者,皆因屯伍之官不能照管,大半为豪民所占。
盖地广而赋轻,故豪民喜得,入手即报新垦于州县,而屯地自此消灭矣。
中间不肖之人或典或卖,或暂佃一时,久不能赎,则豪民之而不归”。
[42]
虽然强占民田的现象确实存在,但相当多的民田是购置所得,当无疑义。
军民互占田地有多重原因。
客观上,屯军户的人丁事产随着社会变迁会有所变化。
人口众多的屯军户田地不足使用,势必要通过购买或强占来补充。
主观上,“军士利于屯田之去籍可以免着伍也,则私相卖;
豪右利于屯田之无赋可以免征输也,则私相买。
”[43]
军民田地互占给屯军隐占屯田提供了条件。
弘治年间曾发现云南卫所把二万八千余亩屯田混入地方有司民田册籍内的事件,为儆效尤,明朝政府按盗卖官田罪给予从重处罚。
[44]不过从万历时政府再度严令淮安、凤阳等地“卫所屯田不许混入有司开册”[45]来看,类似的问题并没有被有效制止。
对于地方官而言,由于屯田隶属卫所,自己无权直接过问。
给清查军民田互相隐占造成了很大困难。
清查军占民田时,军人“一概将地赖为军装子粒”[46];
清查民田时,“奸民”又“窜之军屯王庄”[47],自己无权管辖。
更有甚者,部分地方官员处于保护地方利益的考虑,有意规避对屯地的清查。
如徽宁兵备道程拱宸袒护东流县百姓占夺南昌卫屯地,阻挠清丈。
[48]行政官员可以袒护部民,向来官声不佳的卫所管屯官只会变本加厉。
中央政府虽然感慨“职屯必利屯,若职民复利民耶!
”[49],但碍于不可改动的文武两分祖制,对其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必然副产品,只能是徒呼奈何。
在军民、军地双方的共同作用下,军民地相互混占的现象愈演愈烈。
发展到明末,连官方亦称“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狡民而诡军户,因循日久,茫无可询”[50],毫无办法。
明初,大批军士的家属到经济、生活条件较好的卫所随住。
由于卫所容纳能力有限,明朝政府曾几度下令在卫亲属除当房家小外一概回原籍听差。
[51]但有大批亲属不愿回乡,纷纷移住到卫所附近地区居住,成为附籍或寄籍军户。
在四川,“四川布政司左参议彭谦言:
四川成都前等卫、雅州等千户所旗军,自洪武间从军,子孙多有不知乡贯者。
今但正军、余丁一二人在营,其余老幼有五七人至二三十人者,各置田庄,散处他所。
军民粮差俱不应办。
乞行四川都司及抚民官勘实,就令各于所在有司附籍,办纳粮差,听继军役,庶丁粮增益,版籍清明。
从之”。
[52]这些人可以说是巧妙利用了余丁身份,为自己创造了最有利的局面,俨然是化外之民。
彭谦提议获准,加强了对这些人的管理。
但即便附籍,这些人也不安份。
正统三年,四川清军官员取勘各府州县人户,结果发现“有三姓五姓十姓合为一户者”,于是命令他们“俱各另为立户,应当粮差”,[53]严禁合户附籍。
现有科研成果显示,明代福建的军户有若干姓共用一姓合户立籍的现象,如福宁州孔、刘、谈、汤、贺等姓虚拟户名,詹、张、卓等姓以“全”为共同之姓,等等[54]。
这种现象在四川军户中同样可能发生。
前面所说的附籍人户中应该包括彭谦所说的军士家属。
尽管朝廷有严令,这些人却依旧如我。
嘉靖时胡世宁的奏疏中仍称“大户或十数姓相冒合籍,而分门百十家,其所报人户不过十数小户”[55],可见朝廷政令并未得到贯彻。
允许附籍给清勾带来了麻烦,一些军户“一家或三五人、十余人,止用一二人寄籍有司,其余隐蔽在家”。
兵部无奈,只好于景泰元年改弦更张,责令“不分年岁久近,除其该纳粮草仍于有司上纳,其人丁尽数发回军卫”[56]。
但这时兵部和户部之间出现政策上的矛盾。
户部于景泰二年制定的黄册攒造册式中规定“其军卫官下家人、旗军下老幼余丁,曾置附近州县田地,愿将人丁事产于所在州县附籍,纳粮当差者,听”[57]。
这种政策上的龃龉直到成化十八年才统一为“凡有卫所之处,附籍军丁无粮草者,尽发原卫当差;
有则户留一丁应纳。
丁老及有他故,仍于本卫取回一丁顶户”,原无籍名有产欲报者亦准一丁附籍。
[58]取消了绝大多数军户余丁寄籍附近州县的机会。
但到正德十六年,明廷又开禁,准许不足110户的里,“以附近流来有司、军卫人丁,及军民官员事故遗下家人子弟,寄居日久,置成家业者补入”[59]。
可见,成化十八年的条例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仍不断有卫所军户余丁移居附近州县,置产治业。
为不使其成为化外之民,明廷只好开禁。
由于军卫附籍制度的存在,大批富有的屯军或余丁乘机购置民田,成立游离于卫所和地方政府管理之外的寄庄,进而将附近屯田诡入寄庄。
一些民户也不时避入寄庄以躲差徭。
军卫佥派差役,则称已经附籍地方,承当民差;
地方征派粮差,则谎称仍隶卫所,已有差遣。
由于军民之间的相互利用以及管理系统上的问题,使寄庄问题成为明朝地方政府的一大难题,尤以屯民田地错杂的东南地区为重,也因此为行政官员逐渐介入卫所事务提供了机会。
为解决在卫留住家属的生活问题,政府允许其垦种部分田土,且征税科则较轻,甚至“永不起科”。
有余力的屯军本人也可在分地之外,另垦荒地。
如永乐时规定“军官及军下舍人、家人、余丁自愿耕种者,不拘顷亩,随其开垦,子粒自收,官府不许比较”。
[60]正统元年奏准,“陕西军余地亩如民田五升起科,月粮仍旧官给。
其屯田正军该纳余粮六石,余丁地亩亦科如民田。
”大同、宣府边卫亦如例实行[61]。
正统七年,令自开垦荒田每亩纳粮五升三合五勺[62],等等。
科则不一使屯军开垦荒田的积极更高,兼之分地与新垦田土一般较近或相连,使屯军有机会混淆分地与垦荒地之间的界限,将分地占为己有,或与贫瘠余地置换。
更有甚者,故意把分地抛荒,舍此就彼,等待政府发布新的垦荒命令,然后在复垦,谋取轻则科则。
另外,正军、军余所开垦的余地允许典卖转让,致使屯地也被逐渐纳入典卖的行列,给清理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以宣州卫为例,洪武时,屯田正军人给40亩,“岁征其半,余存自食,谓之原额……法惟承佃,不得易卖”[63]。
“宣州卫田溢于军,本多芜没。
其后荐经垦辟,科税转轻,故有起科、改科、今清之目。
官舍军余于法皆得领佃,私相买卖。
然其为屯田,一也。
”[64]到嘉靖时已经是“原额屯田多为豪强兼并”[65],难于清理。
宣德以后,由于操军大量逃亡、国防形势的变化以及漕运的需要,大批屯军被征调操备或转为漕运军,原种屯地转归余丁合法耕种,事易时移,到明中后期甚至产生“正军充伍,余丁拨屯,例也”[66]的说法。
余丁下屯,既代种正屯,又自种余地,更便利了对屯地的隐占置换。
与屯田被屯军逐渐隐占为私有相伴而生的是屯地私相典卖的盛行。
典卖之风盛行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由于贫富分化,富户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丁,贫户人丁寥落,无力耕种,典卖尚可稍有收益。
正统以后,由于军士逃亡现象日渐严重,强壮屯军被大量抽调从事守城操练,家口较少的军户只能把屯地交给妇孺耕种。
“屯田虽设,率以付老弱妻孥,既不能执耒秉锄,又不能具牛种,则佃之他人,否则弃为污莱”[67]。
正统以后屯田子粒改折征收的地区愈来愈多,相当多的屯军或者由于改调别差,或者另有生财之路而离开土地,转入城市生活,原领屯地只好典佃,时间久远者甚至“漫不知伊田所”[68],结果领佃者趁机进一步典卖,致使田主不清,纠纷从起。
二是由于屯田在法律上“有典无卖”,买主要冒一定风险,因而有意压低屯地价格。
以湖广为例,“民间交易三十亩之价可得七八十金;
军曰有典无卖,价只二十金以下。
[69]”地价低廉,又可以借机躲避差役,自然大受富裕民户欢迎。
第三点,也即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官豪的欺压和侵夺。
屯军无力抵抗,只好卖掉田地,一走了之。
对此史籍中的记载颇多,无需赘述。
屯军有典卖田地的现实需求,腐败的明朝政府也在一旁帮忙。
本来屯田地土和民间土地一样有相应的册籍存档,可供调阅,但由于管理不当,到成化间已经是“各都司卫所原行文卷多有朽烂,间有存者,旋复改洗,以致无籍,官旗人等乘机作弊”[70]。
一些卫所的鱼鳞册虽然保存了下来,由于害怕得罪官豪之家,往往也是像陕西诸卫一样“宁匿而不出”[71]。
由于屯政败坏,卫所管屯武官的作用日渐受到怀疑。
发展到嘉靖四十二年,朝廷终于下了决心,下旨将军屯管理权移交屯地所在地区的州县行政官员,“不拘军旗余丁,俱听提调……其卫所管屯官止许督率旗甲人等布种上纳,不许经收钱粮。
”[72]在陕西,为便于招商垦荒,甚至一度不允许管屯官“亲身下屯”[73]。
管屯武官权力被大幅度剥夺,自然心有不甘,不免会肆意篡改有关册籍文档,胡乱派发土地由票,为本部屯军谋取私利,使之买卖屯地尽可能趋于合法以及在军民土地纠纷中占据优势。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到明末,典卖屯地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丝毫不顾忌国家禁令。
如在泗州,屯军将逃亡军士遗下屯地“典当于农民,而坐收不赀之利。
久则直以为己物而立券卖之,虽得半价且甘心焉。
或姑留少许以备稽查,或归罪田邻以遂乾没。
凡所伍无不皆然,而远乡屯营尤无忌惮……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卖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廉也。
而一买之后,视之不啻若世业”。
[74]在福建,“异时以典卖军田为讳,今民间显然相授受,按亩估值,其价几与民田埒,虽屡下清核之令不能禁”[75]。
面对屯田隐占、买卖之风,明朝政府内部也发生意见分歧。
一些人认为应坚决打击占耕屯田、私相买卖之风,如杨一清提出:
“行管屯官按籍稽查,有占种者责限自首,免其问罪……如仍欺隐,事发依律问遣”[76]。
庞尚鹏认为应“严加查禁,许自首者负罪,有能告者即以其田界之”,但对新垦荒地应允许其“永为己业”[77]。
一些务实的官员则提出清屯的目的在于确保屯粮能按原额征收,至于由谁来上缴并不重要。
如正德间尚宝卿吴世忠在清理蓟镇屯田时指出:
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
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
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卖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
田仍给主,价亦免追……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
惟在租税不失原额。
……从之。
[78]
不过从日后的记载来看,吴世忠的建议并没有被广泛推广。
嘉靖初年的基本政策是“首正还主,价不入官,人不治罪”,试图通过免于处罚来吸引屯军自首改正。
不过这一政策明显有利于卖地的屯军,而不利于买地的民户,“遂致军人不论远近典卖及将置买民地、逃军遗业妄肆告争”。
无奈之下,只好回到“价必入官,人必治罪”的老路上。
[79]
激进的一派则提出认可屯地买卖的建议。
如《怀庆府志》的作者认为:
治家如治国,有为者治万亩而有余,无为者易百亩而不足。
田荒芜而赋税何出?
此则典卖者势之所必至也。
强夺富人纳价之田而归之本主,是以拂人情而讼繁兴。
且如人孰不爱其子,岂待君人者之禁?
……若两省巡抚会文,立为一定之法。
凡民买军田、军买民田,每亩岁输银五分与本业主。
大约每亩三分,在军足以完两税,所余二分足以备军装;
在民三分足以备粮马,所余二分足以供杂差。
军买军田,则两税随轻重完于管业,外二分以资军装。
而近年所加地亩差银一切革去。
若然则贫军百亩之田虽卖而岁得银二两以资行装,田倍而所得亦倍之,又何至于逃哉?
……此虽迁就之说,然亦足军士省词讼之要法也。
[80]
这一建议不仅认可了屯田私有的既成事实,还提出利用政府力量干预屯地买卖,以求军民两不吃亏的具体措施。
不过其执行前提是明确屯地原主,这在明末显然已经无法办到。
不过,本条建议的提出,反映了在明末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思考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说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已经在上层建筑中有所反映,这是本建议的最大价值所在。
虽然明朝政府在大政方针上继续坚持屯军、屯田相互匹配不得变乱的政策,但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明廷也不得不在局部做出让步。
嘉靖九年,明廷批准巡按御史方日乾的建议,准许“南京镇南等卫荒芜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量力开垦。
待成熟之后照旧纳粮,仍令永远管业,不许补役复业者告争”,[81]在客观上承认了屯田可以私有。
在方日乾的《抚恤屯田官军疏》[82]中另有一更大胆的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明末 自耕农 浅析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