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Word文件下载.docx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Word文件下载.docx
- 文档编号:16381631
- 上传时间:2022-11-23
- 格式:DOCX
- 页数:11
- 大小:36.76KB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Word文件下载.docx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Word文件下载.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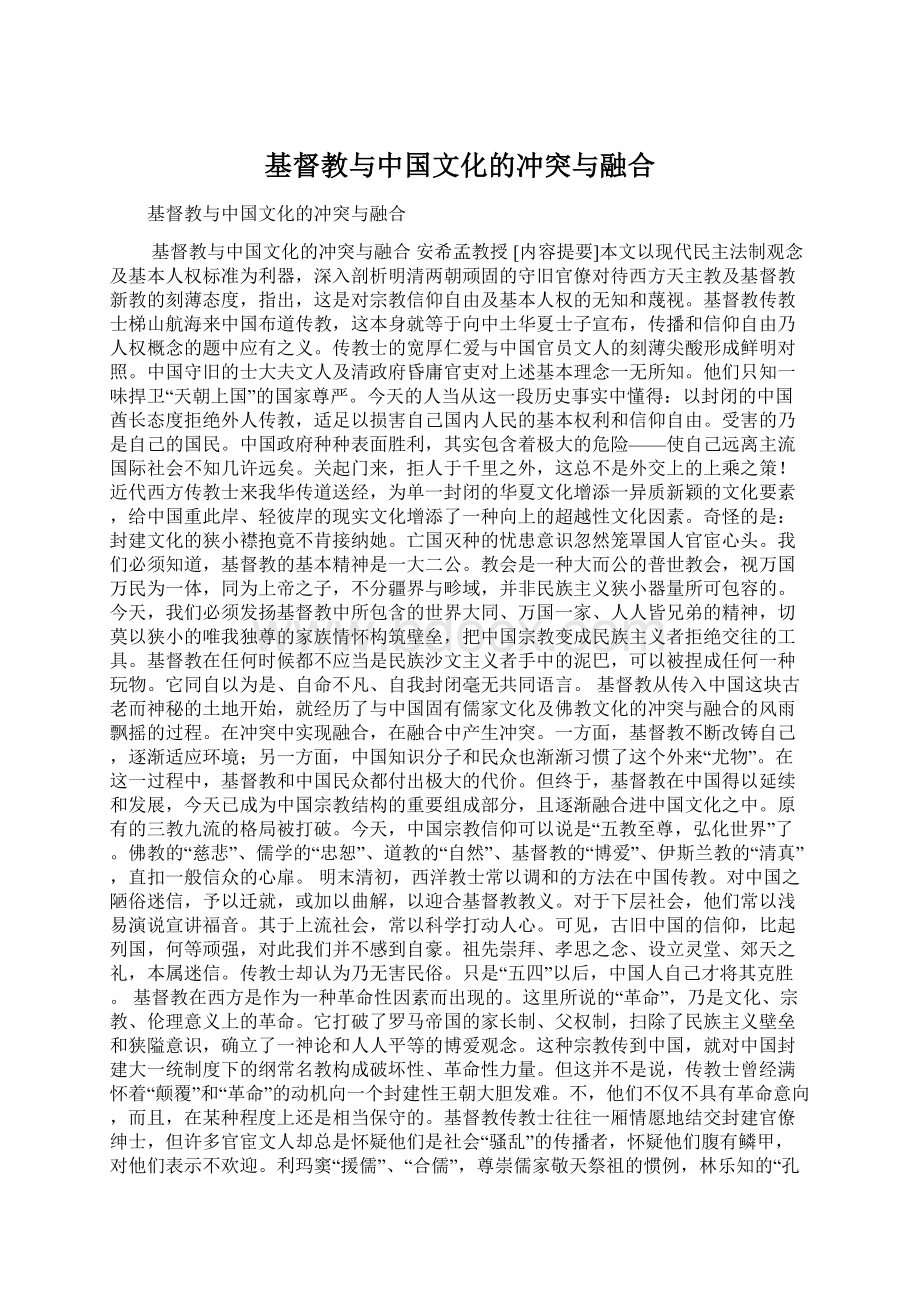
明末清初,西洋教士常以调和的方法在中国传教。
对中国之陋俗迷信,予以迁就,或加以曲解,以迎合基督教教义。
对于下层社会,他们常以浅易演说宣讲福音。
其于上流社会,常以科学打动人心。
可见,古旧中国的信仰,比起列国,何等顽强,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自豪。
祖先崇拜、孝思之念、设立灵堂、郊天之礼,本属迷信。
传教士却认为乃无害民俗。
只是“五四”以后,中国人自己才将其克胜。
基督教在西方是作为一种革命性因素而出现的。
这里所说的“革命”,乃是文化、宗教、伦理意义上的革命。
它打破了罗马帝国的家长制、父权制,扫除了民族主义壁垒和狭隘意识,确立了一神论和人人平等的博爱观念。
这种宗教传到中国,就对中国封建大一统制度下的纲常名教构成破坏性、革命性力量。
但这并不是说,传教士曾经满怀着“颠覆”和“革命”的动机向一个封建性王朝大胆发难。
不,他们不仅不具有革命意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当保守的。
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一厢情愿地结交封建官僚绅士,但许多官宦文人却总是怀疑他们是社会“骚乱”的传播者,怀疑他们腹有鳞甲,对他们表示不欢迎。
利玛窦“援儒”、“合儒”,尊崇儒家敬天祭祖的惯例,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思想,某些传教士不是面向大众,而是走“宫廷路线”,这一切表明他们并不想触动封建社会基石的一丝一毫,不敢对传统礼俗和信念发出稍许疑问。
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确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逐渐站稳脚跟。
另一方面,顽固守旧的封建官绅中一些人,似乎也看到了基督教的理论与实践确实会在不知不觉中危及封建制度的安全。
尽管从法律上讲,他们所捏造的传教士“图谋不轨”、“谋我中华”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但从思想与文化方面来看,他们的疑虑和惊惧也许不无道理。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固有本土文化是一种异质文化。
它打破了儒术独尊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新的因素。
基督教禁止拜偶像,而中国社会却普遍重视祭祀祖宗,设立祖宗牌位,祭悼亡灵。
基督教排斥上帝以外的任何神祗,而中国社会“自天地日月星雷风雨以至山川城社门行井溜,莫不有神”,民众不仅按时致祭,而且随时祈祷、求福、求寿、求雨、求晴、求子女、求升官、求发财、求太平。
基督教主张男女平等,对男女同堂听道、聚会,并不忌讳,而中国人则格外注重男女之大防。
中国社会到处讲风水、算命、占卜,基督教则反其道而行之。
基督教主张“人类一体”说和“世界一家”说,中国传统却特别注意“严夷夏之防”和“尊王攘夷”,具有浓厚的排它性。
中国人因而斥天主教为“不敬祖”、“不祀神”、“男女混杂”、“破坏风水”、“无父无君”。
传教士挟西方科技文明和社会理想而来,的确是对中国旧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皇权、父权、夫权统治和三纲五常的否弃,给封建迷信活动带来震荡。
尽管如此,传教士在政治上远不是革命的。
他们是改良的。
传教士的主观动机和基督教文化带来的社会后果,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因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汇”,不应当是指基督教被儒学及中国习俗同化,而应是基督教文化被中国信教群众接受、理解,在中国生长扎根,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构成要素,居于合法地位,而仍不失其信仰特质。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这是我们很可夸示于人的。
但我们也深知,一种古老而不死的文化很可能是一堆沉重的包袱。
基督教是西方外来文化。
假如它能使古老中国焕发青春与活力,假如它能有效地阻遏古老文化的僵死气味蔓延,并从根本上革新中国文化,那么,它就不失为一种健康革新的力量。
然而不幸,基督教未能尽其所能地发挥批判优势,便一头钻进中国古老文化的怀抱。
外国传教士尽管试图对中国旧文化作出批评,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向顽固的孔孟之学屈服。
近代西方科技、宗教、哲学、文学、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等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人始终坚持“中体西用”说,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西学之为“用”的器物层面的文化,而对西方本体文化(即哲学与宗教神学),则断然拒绝。
中国人对危害国家社稷朝廷的西方宗教、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及深层次的哲学,全然不加理睬。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必须从根本上接纳世界文化中的美好遗传。
基督教原本是标举世界主义和“人类一家”的旗帜的。
但到了中国,却被歪曲为民族的、国家的宗教,被迫挂起民族主义和邦国主义的旗帜。
这可以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不幸命运。
基督教成了卫国保家保种的攻伐异己的掩护。
假如基督教能充分发扬其对中国古旧文化的冲击与批判的作用,或许它会受到更多的中国学者的欢迎。
对基督教从内部所做的人为阄割,使之成为为皇室、为家庭制度服务的国家主义宗教。
这可以说是基督教两千年最悲惨的命运。
一、耶稣会士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努力16世纪下半叶,古老的中国开始同年轻的西方直接交往。
西方世界成了这一文化交往的主动一方,封闭的中国处于被动而勉强应付、步步设防的一方。
这一交往的中介恰恰是基督教传教士。
由于他们的筚路蓝缕的努力,西方科技在中国得到传播。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经由他们的努力传入西方。
令人感到惆怅的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竟然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而不是中国的文化人。
他们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遇到的首要敌人竟是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及其臣民,尤其是中国文人。
16世纪以前,中国和欧洲通过“丝绸之路”偶有往还,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真正的思想沟通和文化交锋,因而彼此并不十分理解。
即使是享誉中外的《马可·
波罗游记》,也没有向西方介绍多少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经籍,更没有给中国人带来西方科技、哲学与宗教思想。
耶稣会士频频向西方发出盛赞中国的书信和报告,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耶稣会士采取灵活的传教方针和迎合中国习俗的策略。
然而不幸,中国知识分子仍旧认为传教士们是在推行有害于华夏“礼义之邦”的“西夷”的伦理价值观念和科学,赤裸裸地表现出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敌视态度。
不幸的根源在于,中国是一个宗教与政治、教权与政权难以分离的国家。
任何宗教观念都被认为是“颠覆”计划的一部分。
甚至传教士帮助绘制地图,也被当代中国人认为是为外国制定作战“计划”,是绘制“军用地图”。
传教士用《圣经》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努力,也被当今时代的人认为是“否定”中国文化。
20世纪后半期倍受政治熏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比别人更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
尽管如此,耶稣会的大部分人却仍旧主张将天主教与中国哲学加以“调和”。
耶稣会士来华以后,主张孔子哲学具有“优越性”,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具有“一致性”,并认为“六经”中上帝及天就是基督教的“天主”等。
中国守旧的文人对此并不领请和激赏。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作出这种回应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儒、佛、道中多数人仍旧以疑惧的目光注视着“外来”宗教,因而冲突大于融合不知多少倍。
从根本上说,基督教文化与敬祖事天的儒家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大文化体系。
如果华夏士子能以坦诚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洋文化、用以弥补中土炎黄文化的不足,则中国文化会发生新陈代谢革命性的变化。
这毋宁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
但囿于惰性思维的中国王公大臣、士子文人,以封闭排外为最高宗旨。
中国教会于是标榜自我封闭、自我颂扬、自我布教。
这种排外意识竟达到令人恐怖的高度。
同世界性开放格局相比,中国士子文人,在排斥异端方面居于列国之“最”高水平。
所幸在20世纪将近谢幕的当儿,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大批基督教文化研究学人和基督教学术研究机构。
他们是基督教教会以外的学者。
他们并非“虔诚”信徒,也没有熟读经书。
但他们在译介转述基督教学术方面不遗余力,崭露头角。
在文、史、哲、经、法诸领域,都有这样一批襟抱开放的知识分子。
他们完全没有旧式文人和某些封闭的基督信徒那种狭小的器量。
应当说,这种态度实足以代表中国基督教的未来。
中国的基督教应当抛弃“体”、“用”、“本”、“末”的思维惯例,而应当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弘扬基督教本来就有的“天下为公”的教义,打破心胸狭小的封闭民族心态。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近年追随出国潮而到西方攻读基督教神学的颇不乏人。
他们中有的举家移民,成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桥梁。
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优秀的基督教学者,这些学者已蜕去了旧式文人的蝉壳,具有开放的心态。
兴许他们可以代表中国基督教的未来与发展。
这两部分知识分子,极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吸纳基督教知识的进程。
他们的贡献,有时竟超过了封闭的纯教会的学者和信徒。
这里,问题的关键显然不是知识差距,而是眼光、气魄、胸襟、见识、洞察力等非理性方面的问题。
须知,基督教原本就不是封闭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国家主义宗教。
它视人类为一体,海纳百川。
这正可以弥补华夏文化的欠缺。
这些基督教文化学者视中西文化的贯通为“双向互动批判性”融合。
他们不是器量狭小的旧式文化人,他们并不抱残守缺,相反,却对旧的文化采取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诚然,我们应当感谢传教士融合西洋宗教与中土文化的煞费苦心的努力。
但中西文化是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上生长起来的。
相对而言,明清之际西方以商业背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海外拓殖文化视人类为一家,人人皆兄弟。
这种观念是比较先进的。
今天,人类已成为一体,可以说,无一国一家之私事可以逃避国际共同法则。
一种行为若触动个人的正当权利,定会遭到举世谴责。
这不能不说是人类一大进步,而这种进步,的确始自明清之际世界格局的大变化。
由此看来,传教士的来华,其意义不仅在于带来西方科技与宗教,抑且在于打破了民族主义壁垒,带来了“人类一体”的观念。
以此种观念看清王朝的知识分子,则别有洞天。
如许大受说:
“彼诡言有大西洋国,彼从彼来,涉九万里而后达此。
按汉张骞使西域,或传穷河源抵月宫,况是人间有不到者,《山海经》、《搜神记》、《咸宾录》、《西域志》、《太平广记》等书,何无一字纪及彼国者。
”①这表明清朝士大夫的知识偏狭。
他们压根不知道欧美各国。
在这种锢闭心态支配下的中国士子,抱残守缺,因而断难谈到中西文化融合。
它们之间,有的只是冲突,很难沟通,应当以西方先进文化克胜中土残缺文化,取而代之,而不是什么融合、结合。
任何不是以西方基督教制胜中国残缺文化,而是以中学化解容纳西学的努力,都是使老大帝国苟延残喘的痴心妄想。
今天,以西方之学化解、冲击固有的东方守旧之学,大势已定,势所必至。
我们应当欢呼“人类一体”,“万国一家”的大时代的到来,我们切不可以华夏亘古文化抗拒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切不可做旧文化的殉葬品。
二、明清之际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合儒、援儒、补儒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单相思”。
对此,中国儒学的代表者们一点儿也不领情。
明朝中国儒学已发展为理学,理学家们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因此明清之际曾经发生过天主教与理学家及佛教的争论。
文化上的争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益的,只要不逾越法制常轨,或者,只要不是假借法律的名义置论敌于死地,这种争论越激烈,就越能激发奇想与智慧,促进学术的繁荣。
然而在中国一方,“平等争鸣”是不可思议的,“斥异端”乃是天经地义的。
天主教传入中国,首先遇到佛教的反对。
佛教不是中国本土文化。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佛教不占主导地位。
因此,利玛窦一开始就制定联儒反佛的路线。
佛教徒也不示弱。
当时有名的祩宏(云栖)和尚,写了《辩天四说》,对天主教提出三点反驳意见:
(1)天即理,所以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宰;
(2)灵魂是轮回的,而不是不灭的;
(3)孔孟学说是美满的,所以不需要天主教“补益”。
这表明,佛教也吹捧儒学以反对天主教。
双方都以儒学“卫道士”面孔出现。
在中国一方,儒生们认为,儒学“完美无缺”,不需要西方学说补充。
认为称西方为“大西”,一个“大”字就表明有野心。
中国士子的锢闭的心态于此历历可见。
邹维琏《辟邪管见录》认为“天主”这一称号凌驾于三王周孔之上,“从来大变,未有甚于此者。
”张广湉《辟邪摘要略议》认为传教士“以彼国之邪教,移我华夏之民风,是敢以夷变夏”,认为中国风俗,不可更改。
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喜欢从政治上想问题,总是“政治掛帅”。
何以“以夷变夏”就是大逆不道?
马克思主义不也是“夷”吗?
这些封建卫道士像害怕农民起义一样害怕天主教。
惯于为大众的灵魂与思想信念负责的“救世主”们,总以为离开了他们的“路线”,天下就会大乱。
如李灿《劈邪说》担心天主教“惑世诬民”会引出“十倍白莲”的“烈祸”。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天主教其实并没有被农民起义所利用。
如果它真的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那倒毋宁说是一件好事。
传教士的“宫廷路线”,决定了他们不能与中国社会最下层中富于反抗精神的贫苦百姓结合起来。
他们担心这会贻误“传教大业”。
然而,即使如此,统治者也还是怀疑他们有“煸动叛乱”动机。
这真是传教士的莫大冤枉。
西方学说在中国的命运与中国学说在西方的命运大不相同。
现代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承认,明清之际,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欧洲地中海沿岸的资本主义曙光,中国似乎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落后。
那么,为什么后来的几百年中国衰落并且遭到入侵呢?
这恐怕有文化上的原因。
明末,中国学说传入欧洲,受到欧洲先进人士的欢迎,引起了思想上的“启蒙运动”。
欧洲人博采众长,对中国思想采取吸收和同化的办法,以东方思想为利器,向欧洲陈腐的社会上层建筑发动攻击。
中国人却努力拒斥西方思想。
这给我们以启迪:
应当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一切以“为我所用”为目的。
孔子的学说在中国并非进步学说,也谈不到科学性与革命性,但在西方却起了酵母的作用。
同样,16世纪天主教的学说在西方正受到新教的批评,但传到中国,如果加以发挥,亦可以掀起社会狂澜。
中国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包容的气质。
像徐光启那样的人,只是区区少数。
王文杰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一书中说:
“儒家礼教在这四千多年的古国里,有它根深蒂固的潜力,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石。
中国顽固的士大夫素来以生于文物礼仪之邦自诩。
他们除了承认传统的礼俗和旧文化的权威外,不肯亦不屑向任何外来的精神文化低头。
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来自异邦的异教,简直是异端邪教,与洪水猛兽一样。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不是二千年前儒家老师的经义吗?
……所以教案乃是中国旧传统旧礼俗对新的西洋宗教势力的排斥和斗争,它是中西精神文化的冲突。
”这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纷纷扰攘的教案问题的最为鞭辟入里的论述。
它点出了宗教冲突的实质。
在日渐腐朽、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中,官绅士民各阶层反对基督教,言人人殊,但反对基督教的基本理由不外以下几种:
一种是出自排外惧外的自大心理,认为传教士必定怀抱侵略中华的动机;
一种是出自道听途说,认为基督教行妖术邪术,有邪僻鄙劣的行为;
一种是出自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担心基督教会煽动下层民众反抗,危害中国社会安宁;
还有一种是站在儒家自大立场上,斥基督教为“不合义理”。
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中国人视之为“侵略”,传教士被视为“侵略者”。
诚然,“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的传入与列强侵略中国这两件事具有同时性,但发生在同一时期的事件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性质。
二者有联系,但同时却可能有区别。
从传教士方面来说,他们“传播福音”的活动早在殖民主义者向东方掠夺之前就开始了。
只是由于中国海禁森严,他们不得其门而入。
有的“学术”文章把传教士搭乘西洋货船来东方,作为传教士“配合”经济侵略而实行“文化侵略”的证据。
然而,你搭乘商船,并不表明你参与商人的商业活动。
你搭乘货车,并不为车主的一切行为负责。
中国人奇特而古老的株连做法,被嫁接到外国人身上。
传教士搭乘商船,无论如何不应当被认为应当为商人的行为负责。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屡遭迫害,外国使领馆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正当权益,也自在情理之中。
当今我国住外侨民,当然亦受我国政府保护。
至于他们中某些人依势欺人,违反中国法律,则自当别论。
从中国方面来说,封建王法的确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
某些守旧大臣和文人并非因为传教事业同船坚炮利联系在一起才阻挠基督教传入。
我们不应当以任何理由为闭关锁国政策辩护。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拒传教士于国门之外。
对于大厦之将倾的满清王朝及深受儒学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教士有武力后盾与没有武力后盾都是一样。
总之,对西方洋教是应当群起而攻之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传教活动与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不可混为一谈。
文化史家应当视宗教交流为文化交流题中应有之义。
许多人并不了解,西方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步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宗教同国家政府不再是合二而一的了。
19世纪后半期,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基本上不是由政府决定,而是由宗教团体中热心分子自发组织的。
新教尤其如此。
新教不带任何官方色彩,它本身就是民间性质的组织。
从倡议传教、物色人员到筹措资金,乃至远洋航行,以及在中国建立传教据点,都不是由外国政府、军队或商人集团决定的。
在中国,宗教同政治结合在一起,宗教常被政府操纵,故此中国人也想当然地把基督教传教事业视为具有政治性质,视传教士为受外国政府派遣的“别动队”。
晚清末年,一般知识分子认为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对传教活动格外警惕,是没有理由,也是不必要的。
他们的怀疑与恐惧,他们的宣传与文章,往往言过其实,危言耸听,不够客观谨慎,缺乏真凭实据,有些甚至纯粹出于主观臆测和想象。
如1860年(咸丰十年)侍讲学士殷兆镛在一份奏章中对跨国传教很不理解。
他不知道,宗教自由天然地包括在世界各地传教的自由。
今人普遍承认,西方民间建筑(包括教堂建筑)宏伟壮丽,而中国民间建筑则不能与西方民间建筑相比,因为中国民间建筑不得逾越规矩,不得超越“皇宫”。
外国教士在华建教堂,竟因其建筑华丽而被视为“有野心”!
太平天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更使那些封建卫道士感到自己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许多人认为太平天国“叛乱”是基督教传教的结果,以为这是传教士“图谋中国”的表现。
有些人反对基督教,与其说是出于“爱国”,不如说是出于“忠君”。
如光绪年间的周汉,就曾经出计献策,陈说驱逐传教士的战略战术。
他在遗嘱中说他自幼精研兵法,从军以后参与平发、平捻、平回、平苗战役。
可见他多次镇压农民起义。
他准备再平一次“天主教”。
清朝末期,中国官绅所煽动的各种反教的文告揭帖,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维护儒家传统。
儒家向来以“内圣外王”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并以现世为其理想寄托之所在。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是唐虞三代,甚至是比这更古远的理想的伦理世界。
他们的最高要求是“崇正黜邪,尊华攘夷”。
在他们看来,“尊孔孟则不容异教,戴朝廷则屏斥外夷”。
外国人传播基督教,背弃拜天祭祖的礼仪,因而引起他们的切齿痛恨。
士儒对孔孟“圣学”坚信不疑。
晚清教案,其策划者往往是士绅人物,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往往是反教的“急先锋”。
蒋敦复在给英国大使的信中说:
“中国之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出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教外,即入乎禽与兽之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教敦仁之至,义之尽,天理人情之正,无一毫矫强于其间。
”1像这样排外攘夷的腔调,今人听起来很不顺耳。
但你不能否认,即使是21世纪,仍有不少国人怀抱“宗教主权”的概念,拒绝传教之人于千里之外。
中国的知识分子出身科名,熟读四书五经,囿于八股章句之学,志在出仕致位,认为“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记载”,都是荒诞不经之论。
他们拳拳致意于华夷之辨。
如果“夷夏无别”,则“人道沦胥”。
他们认为中国是“三纲五常之所系,政教典礼之所出,戎夷蛮狄之所瞻仰”,因而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忧心如焚,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王炳燮认为,宗教文化的交流乃有害于中国“圣人之教”,最好是锁国隔离:
“中国之人自有中国之教,为中国之子民,即当尊重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
”2王炳燮于同治十一年(1872)上奏折鼓吹“中外有别”,说:
“中外之防,自古所严,一道同风,然后能治。
……袄教妖异约书鄙陋,斤斤计较,何关损害,臣所谓不必论者也。
”3对外国人传教,不论其动机如何,都应拒斥。
同治五年(1866年),大学士倭仁在一道奏疏中反对以夷人为师,他认为这样一来,“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4光绪二十四年,湖南省的周汉发布名为“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自称为周公孔子之教徒,愿做封建制度殉葬祭品。
他大声疾呼:
“我周公孔子之教被洋人败坏极矣!
”“自大清定鼎……自遵周公孔子之教以来,又未有鄙薄纲常伦纪之事……一入耶稣,而父母祖宗视若仇冠,妻子儿女尽变娼妓矣!
一修铁路,而险阻关津直同大道,秀灵庐墓变为荒丘矣!
”他全然站在封建迷信立场上,对基督教连同现代科技文明一古脑儿加以反对。
修铁路会震动祖坟之坟山贯气。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通省绅耆士庶公告》提出:
对信奉基督教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诛”,“如既齐心协力,则上报大清皇帝,下保天下百姓,永扶周公孔子之教,胥于是乎在矣”。
如此不讲法制,岂不天下大乱!
人人可诛,全国共讨。
这很象“文革”的“群众专政”!
最能代表一般封建官绅心曲的,是曾国藩的《讨粤匪檄》(1854年),他对亘古之奇变有些伤心。
他以“扶持名教”自任,指责: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此岂独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他公然无视教徒人身安全自由,号召“抱道”君子打倒天主教,他宣告对此予以嘉奖:
“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恕以卫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5俨然一副封建孔孟之学的卫道士嘴脸!
不过我们要问,谁赋予他们如此权力?
三、反教风朝中的民族主义排外情绪中国官绅反对基督教所使用的手段,往往违反儒家所提倡的理性和笃实精神。
他们给传教士所列举的罪名,包括炼丹术、房中术、祈禳、咒巫等,都是无稽之谈。
这些谣言惑众,往往造成许多教案惨剧。
如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由于群众误信教堂拐卖幼孩及育婴堂“杀害婴幼儿”、“挖眼剖心”所致。
有的人甚至说某传教士“有眼盈坛”。
曾国藩调查天津教案后向朝廷报告说,所谓教堂“拐迷人口”、“养幼孩”、“挖眼剖心”,都是谣言。
反教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内“男女混杂”、“诱奸妇女”、“讵目取睛”、“丸药惑人”、“骗取童精红丸”等。
这类传说,大都是由于对天主教的误解和中西礼俗的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基督教 中国文化 冲突 融合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数学科考试大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