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隐喻与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疾病隐喻与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 文档编号:13507115
- 上传时间:2022-10-11
- 格式:DOCX
- 页数:5
- 大小:21.97KB
疾病隐喻与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疾病隐喻与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疾病隐喻与文化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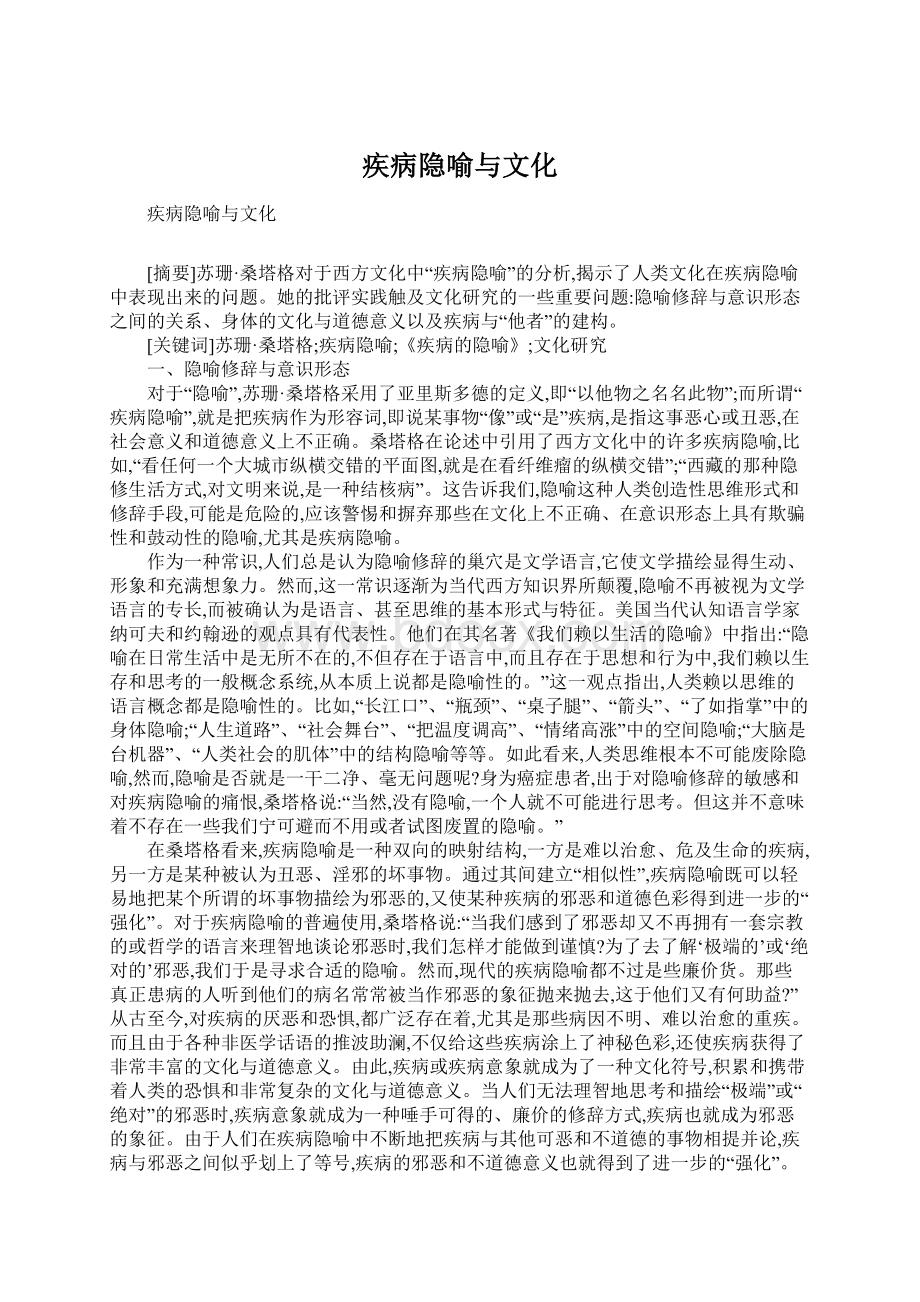
桑塔格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而所谓“疾病隐喻”,就是把疾病作为形容词,即说某事物“像”或“是”疾病,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
桑塔格在论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疾病隐喻,比如,“看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
“西藏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对文明来说,是一种结核病”。
这告诉我们,隐喻这种人类创造性思维形式和修辞手段,可能是危险的,应该警惕和摒弃那些在文化上不正确、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欺骗性和鼓动性的隐喻,尤其是疾病隐喻。
作为一种常识,人们总是认为隐喻修辞的巢穴是文学语言,它使文学描绘显得生动、形象和充满想象力。
然而,这一常识逐渐为当代西方知识界所颠覆,隐喻不再被视为文学语言的专长,而被确认为是语言、甚至思维的基本形式与特征。
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他们在其名著《我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
“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
”这一观点指出,人类赖以思维的语言概念都是隐喻性的。
比如,“长江口”、“瓶颈”、“桌子腿”、“箭头”、“了如指掌”中的身体隐喻;
“人生道路”、“社会舞台”、“把温度调高”、“情绪高涨”中的空间隐喻;
“大脑是台机器”、“人类社会的肌体”中的结构隐喻等等。
如此看来,人类思维根本不可能废除隐喻,然而,隐喻是否就是一干二净、毫无问题呢?
身为癌症患者,出于对隐喻修辞的敏感和对疾病隐喻的痛恨,桑塔格说:
“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
”
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隐喻是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一方是难以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种被认为丑恶、淫邪的坏事物。
通过其间建立“相似性”,疾病隐喻既可以轻易地把某个所谓的坏事物描绘为邪恶的,又使某种疾病的邪恶和道德色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对于疾病隐喻的普遍使用,桑塔格说:
“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谨慎?
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
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
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
”从古至今,对疾病的厌恶和恐惧,都广泛存在着,尤其是那些病因不明、难以治愈的重疾。
而且由于各种非医学话语的推波助澜,不仅给这些疾病涂上了神秘色彩,还使疾病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由此,疾病或疾病意象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积累和携带着人类的恐惧和非常复杂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当人们无法理智地思考和描绘“极端”或“绝对”的邪恶时,疾病意象就成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廉价的修辞方式,疾病也就成为邪恶的象征。
由于人们在疾病隐喻中不断地把疾病与其他可恶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论,疾病与邪恶之间似乎划上了等号,疾病的邪恶和不道德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对病人,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桑塔格看来,政治领域的疾病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无外乎煽动暴力,并使严厉的措施正当化,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修辞手段:
“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
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关于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桑塔格列举了许多例子。
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的瘤子”;
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癌瘤”;
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是”梅毒患者。
可以说,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很可能是对疾病意象的暴力运用,它激发的不是理性思考而是非理性的狂热。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疾病意象所积累和携带的恐惧与邪恶被抛向了某个政治事件,从而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彻头彻尾的邪恶,这就大大增加了指责者的本钱,使得严厉的措施合法化。
英国学者安德鲁·
本尼特和尼古拉·
罗伊尔在论及比喻时指出:
“对修辞性语言的操控与开发对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甚至经济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就是由我们用以谈论它的各种修辞手段所调控的。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强调隐喻等修辞手段在人类政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各种语言修辞与某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醒人们注意隐喻等修辞手段潜在的意识形态意图。
桑塔格对于疾病隐喻的分析正是一种隐喻修辞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她的批评实践让我们再度审视这样一个事实:
隐喻,不论它在文学艺术和日常表达中创造了多么美妙的言词,它都是一种修辞;
而按照其本义,修辞是一种使用语言或其它符号去说服他人和影响他人态度的技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说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个事物,并不是为了更好地、更鲜明地说明和形容这个事物的实际状况或特征,而是为了“说服”的目的,这时的隐喻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手段。
隐喻是一种表情达意的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文化“症候”,因为它携带和传达了某种文化假设、道德意义与意识形态意图。
因此,对于许多形式的隐喻,应该保持一种警惕和谨慎的态度。
比如,战争隐喻就是一个值得揣摩和审视的隐喻,因为“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战争隐喻还是可取的、必需的,如抢险救灾中的“众志成城”、“奋战到底”、“人民战争”等等这些唤起团结和激发斗志的隐喻。
对于战争隐喻,我们要警惕的是它可能激发的非理性、狂热和盲从。
二、身体的文化与道德意义
桑塔格明确指出其写作《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
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
这一次,我把那种具有唐吉诃德色彩和高度辩论性的‘反对阐释’策略运用到了真实世界,运用到了身体上。
”在文学艺术领域,桑塔格提倡的“反对阐释”是一种形式主义美学宣言,目的是反对把文学艺术减缩为内容、意义和思想而忽视了文学艺术中蕴含的感性体验。
因为在她看来,阐释就是通过各种话语赋予世界以意义,无论这些意义是道德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
“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
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
阐释是把世界转换成这个世界。
”以上论断,可以视为桑塔格的“反文化”宣言,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全面反叛,因为正是这套意义与价值系统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妨碍了人们通过“听”和“看”来获得对于世界的体验。
桑塔格对于疾病的道德意义的剥离,是其文学艺术领域的“反对阐释”策略在身体与疾病问题上的运用。
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权力铭刻其中的场所。
英国的阿雷恩·
鲍尔德温等学者指出:
“人的身体是文化的客体尽管人的身体是由一种不容置疑的自然基质组成的,其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组成。
”[6]从我们身体的外观,到状态,再到活动,都具有某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规范。
大多数文化研究学者对于身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如何塑造和规训我们的身体,比如,文化如何为社会个体的男性化或女性化提供向导和训诫;
二是批判某一文化赋予某种身体形式的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如黑人的身体往往携带了更多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属于第二种,它关注的对象也是身体,是患病的身体,它的目标是清理疾病的道德意义。
对于疾病,桑塔格是一个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她坚信:
“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原因———如双球菌之于肺炎,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因此,极有可能,将来也会为癌症找到类似的单一的东西。
”基于这种对疾病的科学主义或“生理主义”看法,桑塔格历数了特定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学的话语,尤其是迷信话语、道德话语,建构有关疾病的“神话”和文化道德意义的现象。
其中,桑塔格尤其反对疾病的宗教迷信解释和“心理学”解释,因为这些有关疾病的幻象和神话,不仅透露出人们对于疾病生理方面的理解何其贫乏,而且全都认定患者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比如,《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中所体现的古代世界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
结核病被认为是那些敏感、消极、对生活缺乏热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的病,这些人在活力和生命力方面有明显缺陷;
癌症被认为是一种激情匮乏的病,癌症患者往往是那些性压抑的、克制的、无冲动的、无力发泄火气的人。
疾病是否应该有道德意义?
桑塔格有关疾病的“去意义”策略和“生理主义”态度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
然而,当这种“生理主义”涉及艾滋病时,桑塔格就遭到了许多批评。
对此,英国学者安吉拉·
默克罗比就曾指出:
“她的小心翼翼和谨慎态度激怒了批评家。
她避免谈论艾滋病的文化意义和艾滋病的政治意义紧密结合的程度。
”默克罗比认为,艾滋病的意义比癌症更加深远,与身体政治的结合也更加紧密,艾滋病与性冒险、毒品、同性恋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可以传染给所有人。
因此,桑塔格对于艾滋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避而不谈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对于这种争议,当今世界的官方主流文化对于艾滋病问题大都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
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对导致艾滋病的某些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但对于患者与疾病本身则操持一种给予同情和反对歧视的态度,这无疑又淡化了疾病本身的道德意义。
人类生活在一个文化意义的海洋,其中有许多意义是有关身体的压制性、耻辱性意义,它们构成了桑塔格所谓“影子的世界”的一部分。
桑塔格力图去除患病的身体所承载的道德意义,呼唤一种更加开明、宽容和进步的文化的到来,这种文化将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桑塔格的批评实践还彰显了当今文化研究一贯的批评路线和立场:
在人类的历史上,围绕着下层阶级、女性、黑人和少数族裔的身体形式,有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对于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来说,摈弃和清理那些具有压制性、歧视性的意义与价值,是一条远未走完的道路。
三、疾病与“他者”的建构桑塔格说: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
”疾病有关社会个体的身体,也会转化为一种社会身份。
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坏事,那么大多数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患了这种疾病,总会觉得在道德上低人一头,于是患者就获得了一种他者身份,一个健康王国的“他者”。
桑塔格的批评实践所代言的群体,就是作为“他者”的某些疾病的患者。
她的相关论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患者或病人被“他者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与疾病有关的其它形式的“他者化”过程,它们有的基于地缘和民族问题,有的基于政治和殖民统治问题。
黑格尔曾使用过“他者”这一概念,他认为如果没有对“他者”的承认和认识,人类个体无法获得自身的“自我意识”。
比如,主人和奴隶是互为定义的。
表面上主人好像无所不能,但实际上,他需要奴隶来确认自身,即他的自我意识的获得依靠奴隶的存在。
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传统中,“他者”也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
“他者”的存在帮助或强迫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和价值观念来确定其自身的位置在何处。
英国学者丹尼·
卡瓦拉罗指出:
“‘他性’是所有社会身份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他者就在我们之中。
当一种文化、社会或团体把某个个体排斥做他者时,它试图排除或压制的实际上是它自身的一部分.”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是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如女性、黑人、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疾病 隐喻 文化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稻草人》精彩读书笔记精选多篇.docx
《稻草人》精彩读书笔记精选多篇.docx
 与精神病患者的沟通技巧ppt课件PPT资料.ppt
与精神病患者的沟通技巧ppt课件PPT资料.ppt
 立洲酒店物品采购清单表格文件下载.xls
立洲酒店物品采购清单表格文件下载.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