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霞与孤鹜齐飞.docx
落霞与孤鹜齐飞.docx
- 文档编号:12448757
- 上传时间:2023-04-19
- 格式:DOCX
- 页数:7
- 大小:21.15KB
落霞与孤鹜齐飞.docx
《落霞与孤鹜齐飞.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落霞与孤鹜齐飞.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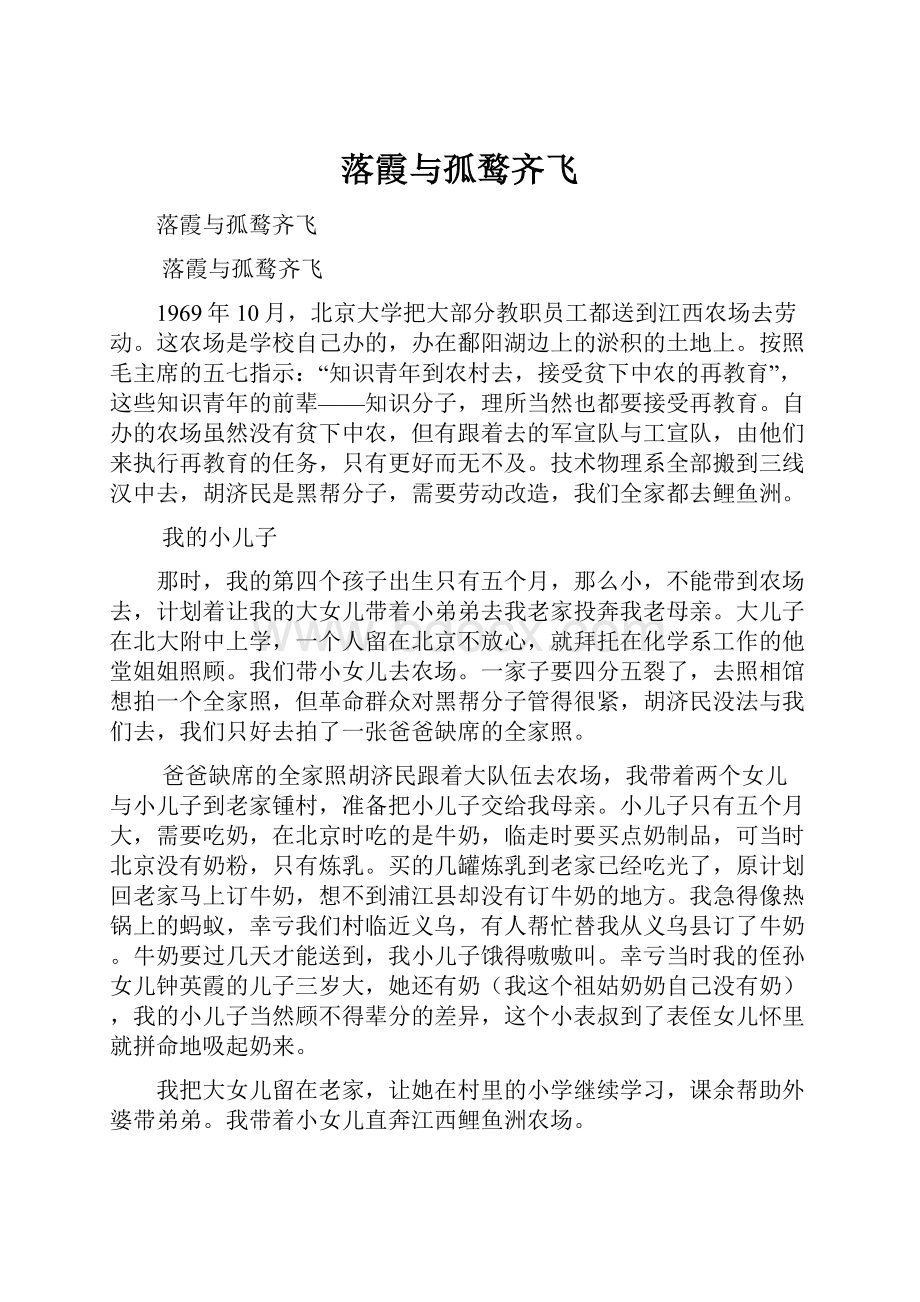
落霞与孤鹜齐飞
落霞与孤鹜齐飞
落霞与孤鹜齐飞
1969年10月,北京大学把大部分教职员工都送到江西农场去劳动。
这农场是学校自己办的,办在鄱阳湖边上的淤积的土地上。
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知识青年的前辈——知识分子,理所当然也都要接受再教育。
自办的农场虽然没有贫下中农,但有跟着去的军宣队与工宣队,由他们来执行再教育的任务,只有更好而无不及。
技术物理系全部搬到三线汉中去,胡济民是黑帮分子,需要劳动改造,我们全家都去鲤鱼洲。
我的小儿子
那时,我的第四个孩子出生只有五个月,那么小,不能带到农场去,计划着让我的大女儿带着小弟弟去我老家投奔我老母亲。
大儿子在北大附中上学,一个人留在北京不放心,就拜托在化学系工作的他堂姐姐照顾。
我们带小女儿去农场。
一家子要四分五裂了,去照相馆想拍一个全家照,但革命群众对黑帮分子管得很紧,胡济民没法与我们去,我们只好去拍了一张爸爸缺席的全家照。
爸爸缺席的全家照胡济民跟着大队伍去农场,我带着两个女儿与小儿子到老家锺村,准备把小儿子交给我母亲。
小儿子只有五个月大,需要吃奶,在北京时吃的是牛奶,临走时要买点奶制品,可当时北京没有奶粉,只有炼乳。
买的几罐炼乳到老家已经吃光了,原计划回老家马上订牛奶,想不到浦江县却没有订牛奶的地方。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亏我们村临近义乌,有人帮忙替我从义乌县订了牛奶。
牛奶要过几天才能送到,我小儿子饿得嗷嗷叫。
幸亏当时我的侄孙女儿钟英霞的儿子三岁大,她还有奶(我这个祖姑奶奶自己没有奶),我的小儿子当然顾不得辈分的差异,这个小表叔到了表侄女儿怀里就拼命地吸起奶来。
我把大女儿留在老家,让她在村里的小学继续学习,课余帮助外婆带弟弟。
我带着小女儿直奔江西鲤鱼洲农场。
当时,我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非常热中。
我觉得自己出身不好,一辈子背着剥削家庭思想包袱,丈夫又是黑帮分子。
现在孩子又要为父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背包袱了,我真想在农场做脱胎换骨的改造,与胡济民一起改造成劳动的知识分子,或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干脆一个劳动者。
让孩子只以父母为骄傲,而不是负担。
在农场,大部分人住的是大草棚,由于我们带着小女儿,特别优待我们,分给我们一间小草屋。
草棚与草屋都是知识分子们自己们盖的,很简单。
在土地上埋上几根木头柱子,钉上几根横梁,周围垒上土坯,上面盖上稻草就成。
草屋里用木板钉了一大一小两张床,我与小女儿睡大床,胡济民睡小床。
江南多雨,住了没几天,天下起了雨。
半夜三更,女儿把我叫醒了。
“妈妈,我的被湿了。
”我起来一摸女儿的被,她的脚后湿了一大块。
原来屋顶漏了。
好在有原来打铺盖用的塑料布与打铺盖的绳,我与胡济民忙着在两个床顶上拉上一块塑料布。
在箱子里找出一条被单,衬在女儿脚后。
忙完了躺在床上,胡济民因白天劳动累了,一倒下又睡着了。
我听着屋外的风雨声,屋内漏雨滴在塑料布上的‘嗒、嗒’声,久久无法入睡。
我想起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好像就是我们这草屋的写照。
杜甫在受尽茅屋的折腾后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
”的呼吁,而且有“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的豪言壮语。
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真有意思,好像‘寒士’要比‘不寒的士’要多,可是还要喊出: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自我标榜。
好像唐朝的知识分子为了有间牢固的房子也很不容易;现在的知识分子,像我们这样的大学教师,倒基本上有‘广厦’住,可是却把‘广厦’给空着、锁着,到这荒原来住阴暗潮湿的草屋。
本来是为下一代转播知识的‘传道、受业、解惑’的教师,却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来进行向劳动人民的转化。
为了明天的劳动,我希望赶快睡着。
可睡眠这玩意儿,你越想睡越睡不着。
我想杜甫肯定也是睡不着才做起《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可惜自己不是一个诗人,否则也可以写诗。
再一想,不是诗人又怎么的?
我想每个人的大脑中肯定都有一小块是用来做诗的,很多人没有去用它,所以不是人人都是诗人。
不开发就荒芜,不用白不用;指挥劳动的那块大脑肯定是另外一块,让这块休息着明天指挥劳动就是了。
反正睡不着,不妨来开发开发做诗的这块大脑,我就一句一句地想了起来:
北风吹雨草屋漏,点点滴滴进心头。
广厦恐有鼠雀窜,书籍应被虫蠹游;
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想愈僵愈自由;
五七道上筋骨换,休留苦难给孩儿。
我一句一句地再重复地记几边。
好像终于自己战胜了自己,像阿Q那样自豪起来,坦然地入了睡。
我们技术物理系到鲤鱼洲来的人比较少,合在数学系的四连里作为一个排。
冬天来了,我们排的第一次挑担劳动,是去给红花草施肥。
红花草学名紫云英,头年下种,施肥后来年春天长起来,灌上水犁掉作为稻田的肥料。
我们给红花草施的肥是一些烂稻草,盖在红花草上既可以当肥料,又可以保温。
看起来这劳动并不重,一条扁担,两个簸箕,铲上两铲潮湿腐烂的稻草,挑着在田埂走约一百米,到田里不用放下扁担,只要分别将两簸箕一悠,稻草肥就倒在田里了。
我从小在农村,虽然是地主阶级小姐,不用下地干农活,但耳染目濡,对如何干农活还是有些经验的。
因此,挑担、走狭小的田埂都要比从小在城里长大的人要能干一些。
第一天老嫌簸箕里红花草少;好像只有使劲地压自己才能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压出来,加速改造自己似的。
可是晚上回到草屋里,就感到浑身酸疼,胡济民更是走路也摇摇晃晃,拿起一个脸盆想洗脸,手连脸盆也几乎拿不住。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穿衣服,感到肩膀一阵刺痛,一看,乖乖,肩膀又红又肿。
第二天还得继续挑肥,扁担再放到肩膀上,那滋味真不好受。
想不到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的转化还真不容易,只有咬牙熬着。
怎么办?
怎样才能减少一点肩膀疼痛的感觉呢?
让脑袋中做诗的那小块发动起来吧!
把负责疼痛的那一小块脑子挤掉,至少让它麻痹一下。
我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开始了,一边挑一边在脑子中又做起诗来:
7.8pt;margin-right: 0cm;margin-bottom: 7.8pt; margin-left: 0cm;mso-para-margin-top: .5gd;mso-para-margin-right: 0cm;mso-para-margin-bottom: .5gd;mso-para-margin-left: 0cm">寄调卜算子 寒风紧紧吹, 汗水阵阵冒; 压走满身书生气, 红日胸中照。 劳动得新生, 永走五七道。 待到来年春风吹, 遍地红花笑。 这首词(能算词吗? )后来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刊登,我俨然成了连队里的诗人。 随着庄稼的生长,五七战士们进行了各种劳动。 由于我们与劳动人民不一样,劳动人民劳动就是劳动,五七战士劳动还有改造思想的任务。 因而劳动人民能用的工具,在我们这里都不合法。 农民拔秧苗用一两头平的特殊凳子坐着,我们不行,蹲着受不了可以跪着,但就不能坐着,胡济民就是跪在水田里拔秧苗的。 插秧时拿秧苗的手不能放在膝盖上,而且决不能站起来直直腰。 戽田(即在稻田中除去杂草的过程)时不能用戽田的工具(江南戽田一般用一条长竹竿头上装一个铁圈这样简单的工具,),一定要用两只手在稻根旁边摸。 由于不能蹲着摸,一蹲,屁股就要影响后面的稻子,因此人要折成基本相等的两折。 鲤鱼洲是鄱阳湖边淤积的一片荒地,在这片田地上劳动时,虽然看不到湖面,但周围也看不到山。 地上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天上是蔚蓝的天空,鄱阳湖上有很多海鸥,白色的海鸥随着漂浮的白云或嫣红的晚霞在天上潇洒地飞翔,使人不禁要想起王勃的诗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不知道“鹜”是一种什么鸟,我想肯定就是海鸥。 劳动不但使我看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美景,还使我看到了“扫帚星”。 扫帚星就是彗星,我小时候听到人说天上有一种“扫帚星”,半夜三更会出来,非常好看。 我们家乡空气非常清新,晚上在晒谷场上看天上的星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 我非常想看到扫帚星,很想拼着一晚上不睡觉等着扫帚星出来,但总是不成功,不是被母亲强迫着去睡就是自己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鲤鱼洲常常要夜战,筑堤、挖渠、建桥、都要夜战,在夜战中,我看到了“扫帚星”,虽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看,但终究是圆了我童年的梦。 我大女儿到老家时已经是小学六年级,不久,小学就念完了,她很想上中山中学去念中学。 可是不成,一个地主的外孙女、黑帮分子的女儿,在农村里是不能上中学的。 虽然我们村的人对我母亲、女儿都非常好,对我母亲的生活有很多照顾,但政策不能随意变通。 我不能让我大女儿失学,连忙请了假把大女儿与小儿子接到鲤鱼洲。 那时,我大儿子也从北京来到农场,我们一家子在鲤鱼洲又团圆了。 但是,始终只有小女儿与我们住在连队里。 大儿子与大女儿都住在五七中学里,小儿子在五七幼儿园。 只有在农闲时才能把小儿子接回来与父母团聚。 因而我这个做妈妈的,没有任何家务事,只顾自己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就是了。 办幼儿园的人原本是普通的职工与教师,她们只顾把孩子们喂饱、看好,因而像喂小猪那样喂小孩,一个个都喂得胖胖的,身上也干干净净。 鲤鱼洲夏天很热,有时气温高达四十多度,她们把孩子们脱得一丝不挂地排着队,一个个挨着走到阿姨跟前给洗澡冲凉,因而一个夏天,没有一个孩子身上长痱子的。 但是,孩子们一个个都变成小傻瓜,我小儿子从外婆那里刚接来时,会叫妈妈、姐姐,会做各种动作,在幼儿园里呆了几个星期后接回来时,傻乎乎什么也不会了。 由于农场接触不到贫下中农,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再教育未免有些缺陷。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第二年冬天,农场把一些五七战士组成一个个小分队,‘拉练’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连也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当然,最需要改造的我也榜上有名,五、六个人的小分队由一个工宣队师傅带队。 农场把我们用汽车先送到南昌。 汽车是货车,在车斗里把这些五七战士们像活猪一样地塞,挤得无法喘气。 汽车沿着鄱阳湖边的大堤开得飞快,大概革命的司机同志根本没有把车斗里的生物当人。 汽车一转弯,巨大的惯性把靠车斗边站着的人从膝盖上面起在空中划了一个圆锥面。 幸亏膝盖以下被行李以及其他人挤得紧紧的,才保持了圆锥顶点的稳定性。 到了南昌,要休息一个晚上。 在学校招待所放下行李,工宣队师傅带着小分队出去吃饭。 走过汤包店,一阵香味扑鼻而来。 “师傅,我们吃汤包去! ”数学系的林三猛高兴得跳起来。 汤包就是小笼包子,一咬一包汤,在南昌是很有名的,对肚子里很少油水的这些五七战士真是莫大的诱惑。 林三猛的大名我已经忘了,他当时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身体很好,到鲤鱼洲后,猛干、猛吃、猛睡,因而连队里都叫他林三猛。 “不行,吃面条去。 ”工宣队师傅板着脸。 到了面馆,面馆中挤满了人,恰好有别的小分队的同志刚吃完,把位置让给了我们。 “你们吃的什么面? ”林三猛向他们打听。 “肉丝面。 ” “师傅,我们也来肉丝面! ”林三猛又高兴起来。 “不行,来阳春面。 ”阳春面就是面汤里放点葱花的那种面条,是最低级的。 第二天的早饭,工宣队师傅要林三猛买些大饼来吃。 林三猛出去转了一转,说只有卖油条与豆浆的小铺,根本没处买大饼。 那就去吃油条与豆浆吧。 大家在小铺中坐定,师傅让林三猛去买,命令他豆浆要白的,即淡的。 林三猛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师傅,那小姑娘说,白豆浆她们不卖,一定要加糖,怎么办? ”那卖豆浆的小姑娘在那边抿着嘴笑。 “真胡闹,那就加糖吧! ” 吃过早饭,大家背上包裹就出发。 这包裹包着一条被与一条褥子以及换洗的内衣,背在背上,相当有份量;手里还提着一个装面盆等梳洗用具的网兜。 要去的大队离南昌有120华里,可以坐汽车,也可以坐一段船。 但小分队什么交通工具也不用,就用两条腿走,这是锻炼的任务之一: “拉练”。 农场不但替小分队联系好要去的大队,而且在离南昌50多华里处的一个公社里给他们准备好中饭。 等他们步行到该公社,已经是下午两点钟。 把背上的包裹一放下,大家发现已经像《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那样,有了停不下来的习惯性动作,没有包裹反而不会走路了,一走就往前冲,只好互相扶着点;因为路上从没有放下过背上的包裹,略为休息或上厕所都是背着它的,它似乎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中饭以后的70多华里的路程,对大家真是个严峻的考验。 林三猛已经把我手上拎的网兜拿走了,他手上已经有了四个人的网兜,他去买了一条扁担,索性把自己的包裹也从背上拿下,连包裹带网兜一起用扁担挑。 嘴里还不断地念着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来鼓励大家。 不知道贫下中农们对小分队进行了什么再教育,反正我觉得在农村的两个礼拜生活得很开心。 江西的农村使我有仿佛回到老家的感觉,看着又说又笑的姑娘与小伙子们,仿佛他们就是我幼年时的小伙伴。 劳动比农场还轻,饭很好吃,蔬菜很新鲜。 1971年夏,北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撤消了鲤鱼洲农场,我们一家回到了北京。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落霞 孤鹜齐飞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搭船的鸟》教案.docx
《搭船的鸟》教案.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