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docx
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docx
- 文档编号:11924006
- 上传时间:2023-04-16
- 格式:DOCX
- 页数:15
- 大小:29.11KB
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docx
《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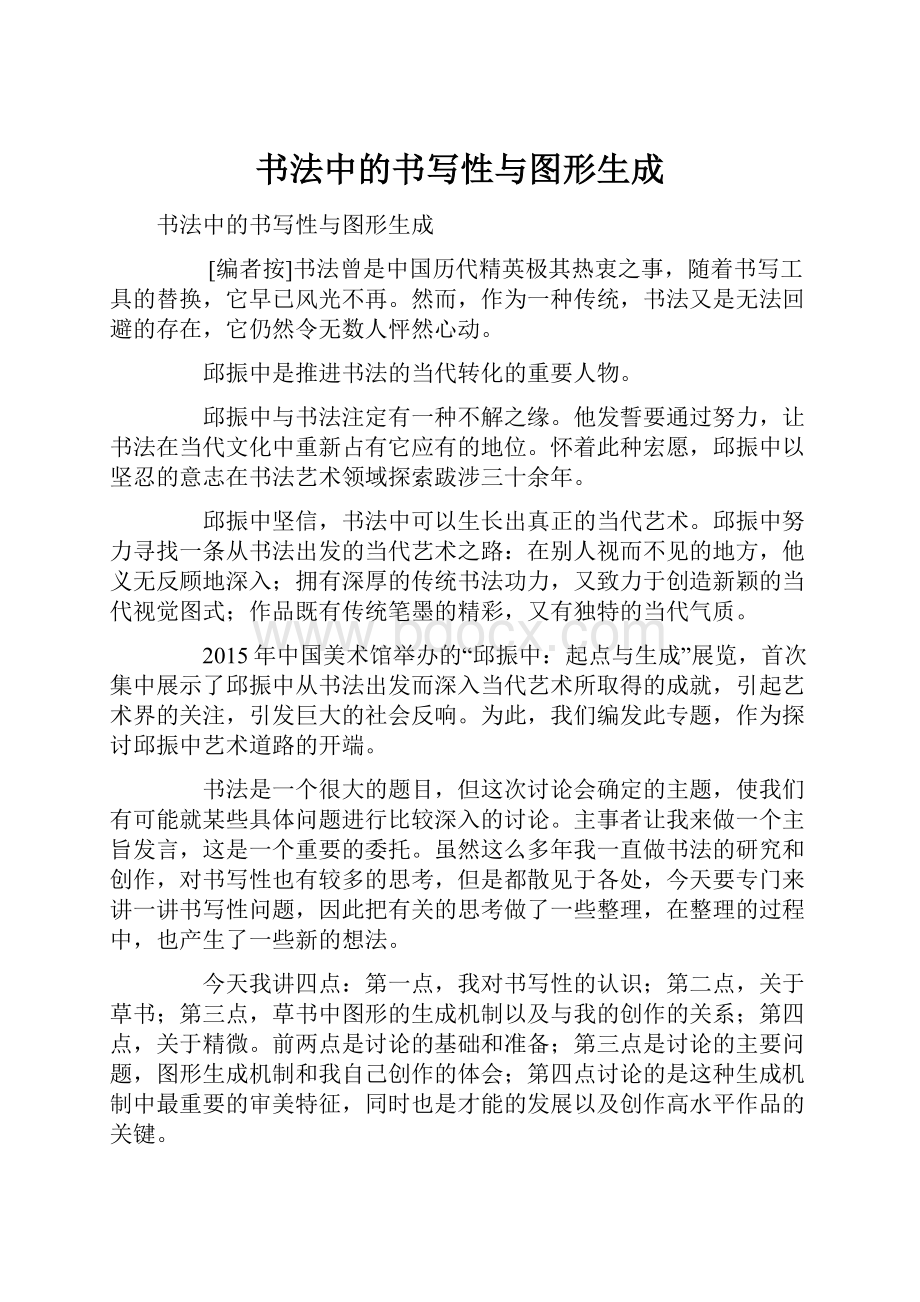
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
书法中的书写性与图形生成
[编者按]书法曾是中国历代精英极其热衷之事,随着书写工具的替换,它早已风光不再。
然而,作为一种传统,书法又是无法回避的存在,它仍然令无数人怦然心动。
邱振中是推进书法的当代转化的重要人物。
邱振中与书法注定有一种不解之缘。
他发誓要通过努力,让书法在当代文化中重新占有它应有的地位。
怀着此种宏愿,邱振中以坚忍的意志在书法艺术领域探索跋涉三十余年。
邱振中坚信,书法中可以生长出真正的当代艺术。
邱振中努力寻找一条从书法出发的当代艺术之路:
在别人视而不见的地方,他义无反顾地深入;拥有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力,又致力于创造新颖的当代视觉图式;作品既有传统笔墨的精彩,又有独特的当代气质。
2015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邱振中:
起点与生成”展览,首次集中展示了邱振中从书法出发而深入当代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引起艺术界的关注,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为此,我们编发此专题,作为探讨邱振中艺术道路的开端。
书法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这次讨论会确定的主题,使我们有可能就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主事者让我来做一个主旨发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委托。
虽然这么多年我一直做书法的研究和创作,对书写性也有较多的思考,但是都散见于各处,今天要专门来讲一讲书写性问题,因此把有关的思考做了一些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今天我讲四点:
第一点,我对书写性的认识;第二点,关于草书;第三点,草书中图形的生成机制以及与我的创作的关系;第四点,关于精微。
前两点是讨论的基础和准备;第三点是讨论的主要问题,图形生成机制和我自己创作的体会;第四点讨论的是这种生成机制中最重要的审美特征,同时也是才能的发展以及创作高水平作品的关键。
这四点都围绕书写性的问题而展开。
(一)“书写性”
我先说一说我对“书写性”的认识。
“书写性”不仅在书法领域,在当代艺术中它也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什么叫“书写性”?
我的理解是,“书写性”指的是视觉作品中笔触的运动感与连续性。
这是著名的美国画家汤伯利的作品(图1)。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童年以来一直渴望的任性书写的快感。
笔触流动,永无止息。
汤伯利是当代艺术中对书写性运用得最彻底、最精彩的一位。
当代艺术中的书写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
汤伯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很多画家,书写性的呈现各有不同。
法国画家米沃特的作品(图2)与他的前辈已经有质的区别。
例如马瑟韦尔,是用小笔触画出一个巨大的、类似笔触的块面(图3),米沃特用的虽然是刷子,但是是一次性的挥运,这里表现出很高的难度,一是笔触的运动节奏要控制得非常好,笔触本身也需要有变化,此外靠一次性挥运完成的作品,空间要非常精确。
――后面讲精微的时候我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中国艺术中的书写性当然非常突出。
可以说,书法把中国艺术中的书写性发挥到极致。
这里说的,一是技巧的微妙、复杂,二是作品累积的巨大数量。
(图4)
至于中国书法中的书写性为什么能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首先可以说到工具和材料的特殊性、对语言表达的不满、对文字书写的表现力的无限渴求等等,更深入的讨论需要专门的时间,不是今天能够展开的。
西方也有书法――可能我们一谈到西方,人们会觉得西方没有书法,其实西方也经常有书法比赛。
我的一个朋友,是柏林艺术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海报设计专家,他送了几本他的书法作品集给我。
他年轻的时候经常获得德国的书法比赛大奖。
它们都是硬笔作品,但并不缺乏表现力,当然,跟中国书法完全不一样。
――有机会我想应该对他的作品做一些介绍,这样我们就会消除一些见,对西方的书法也会有深一层的认识。
关于连续性。
中国书法有比较严格的顺序,但我们所说的“连续性”,严格的顺序不是其中的必要条件。
例如大部分绘画中我们都无法指出创作过程中笔触的顺序,绘画中一般也不包括某种对笔触顺序的规定。
我们所说的“连续性”是指创作时各笔触之间的统一性,以及把所有笔触看作一个整体时,笔触之间的间隔亦成为运动的有机构成部分。
如伦勃朗的素描,线条断开,但在线条整体的构筑中,时间似乎从未间断一作品中的所有线条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
(二)草书
中国书法有各种书体,但是草书无疑是最为充分展现中国书法书写性的书体。
很多人认为《古诗四帖》(图5)不是旭的作品,但有意思的是,所有擅长草书的书家都对这件作品赞赏不已。
在他们心中,这件作品到底是不是旭写的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作品已经成为狂草所取得成就的一个标志。
草书线条的流动性、连续性――也就是我们说的书写性,在这一类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书写中推移速度的变化、线条形状的变化和线条部运动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令人目不暇接。
这种自由,这种节奏变化围的广阔,是其他书体不能相比的。
下面我从“线质”、“运动”、“空间”这三个方面说一说我对草书的认识。
“线质”指线条的“质地”、“质感”,是书法线条最显著的特征,它包括线条的视觉特征以及它们带来的审美感觉。
更细致的分析可以说到线条肌理、边廓形状的一切变化,以及对线条质地的复杂感受。
决定一件作品“线质”的主要是运动、力量以及“水一墨”的运用。
工具、材料无疑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但它们从属于作者的操运。
接下来我说一说“运动”。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毛笔线条与钢笔线条、西方绘画中的线条――比如刚才看到的两位西方艺术家作品中的线条不同的地方:
西方绘画中线条两侧的轮廓(我称之为“边廓”)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线,也就是说,线条的边廓、形状很少变化;而书法中的线条边廓变化非常丰富。
在草书中,很多时候无法划分出一个个独立的点画,作品呈现出一条连绵不断的线,同时这条线边廓的变化十分丰富。
这种边廓的变化是书写时复杂的动作导致的结果。
这些运动反映在线条边廓和质感的变化上,但运动本身却隐藏在线条的边廓之。
为此,我们在思考有关问题的时候,提出了“部运动”的概念。
我们用毛笔写字的时候,除了笔在平面上的推移,它在点画的部还有复杂的运动,我们把这种运动叫做毛笔书写时的“部运动”。
部运动只是在用毛笔书写时才出现,硬笔书写时一般不存在部运动。
由于每个人每一次书写都有微妙的差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毛笔书写的部运动积累了无数的形态。
换句话说,永不重复的部运动,导致了毛笔书写部运动无与伦比的丰富性。
在研究部运动的时候,可以取一个点画或者一段线,对它的边廓一毫米一毫米地进行仔细的观察,然后从这种线条轮廓的变化推测点画书写时的运动方式:
怎么控制笔,自然地书写出这一边廓。
至于如何通过边廓的变化分析线条的部运动,我在《关于笔法演变的若千问题》一文中有详细的讨论。
西方追求书写性的绘画中,线条的推移是明显的,其节奏的丰富性和表现力绝不下于中国书法。
但是它的部运动无法与中国书法相比。
1923年出版的斯基的《点、线、面》,是视觉艺术形式分析的开山之作,书中对视觉图形的构成元素――点、线、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是整个著作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线条自身的变化和线条部的运动。
原因很简单,整个西方艺术史中,艺术家从来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他们为什么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有复杂的原因,但就现象而言,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可以说,西方的线条仅仅是推移,而中国是部和外部运动叠加在一起,所以它的变化更为丰富。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变化最丰富的徒手线的集合,而在草书中,速度、节奏、质地变化域限的广阔,使它成为世界上一切徒手线中的极致。
我们再讲讲草书中空间的问题。
在汉字的使用中,只要不影响到容的辨识,字结构的处理是非常自由的,比如说“大”字,只要让我们看到“大”字的基本结构就可以了,至于一个笔画的长、短、正、斜,都没有关系。
但是草书里把这种自由又提高了一个量级:
如果按规定结构书写,由于省略、重叠等原因而无法识别时,仍然被承认、被接受。
例如图5,就这么几十个字,要把它读下来,恐怕专攻草书的人都做不到。
再如怀素《自序帖》,是大家都熟悉的作品,如果没有释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把它通读。
草书的简省,使得多一个弯、少一个穿插,便是不同的另一个字,但作者书写时根本不把草书规放在心上,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它成为一件杰作。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默认了艺术家对草法的偏离。
这给人们使用草书带来了困难。
特别是狂草,根本无法使用在实际生活中。
草书创作中人们处理大小、疏密等各种空间关系时具有完全的自由,不过限制仍然存在:
人们对既有的典结构的记忆。
记忆典结构是书法学习中不可逾越的一环,它成为绝大部分书法作者创作的基础和始终不会消失的隐形模式。
这种模式使人们在草书的临摹与创作中遇到了困难。
例如对狂草经典作品的临摹。
书法史上几乎见不到一件令人满意的狂草临摹作品。
因为狂草必须根据周围情势随机处理空间与结构,任一细节都是作者临机应变的产物,作者的自由、所受到的制约、瞬间感觉的应对,都融合在每一细节中,因此狂草的临摹绝不是空间和结构的复制,而只能是充分领悟原作背后的感觉并充分把握作者所使用的技巧后,在某种程度上的运用和发挥――这已经超越了所有对“临摹”一词的定义。
简而言之,作者在草书中所被应许的自由,成为临摹者、后来者的陷阱,只有逃过这一关的人们,才可能真正进入草书的状态。
还可以说说草书的即兴性带来的一些特点。
线条的即兴性,使它变成一个活的东西,它只是往前挺进,来不及回头省察,前途也难以预料,只有不顾一切地前行。
“生长”成为描述它的唯一有效的词语。
作品的空间也就在这种“生长”中不断涌出。
至此,我们对草书的空间性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三)我的草书与绘画中图形的生成
有了对书法、对草书的基本认识,现在我来谈谈草书中图形的生成机制以及它对我绘画创作的影响。
一般学习书法,都是一个一个地掌握单字的结构,熟练以后,学习怎样把它们缀合起来,组织成一个整体。
书法作品中,风格不论怎样变化,单字结构都是一个核心的、关键的环节。
篆书、隶书、楷书、行书,无不如此,只有草书,有所不同。
草书分为小草和狂草,小草单字分立,由单字构成作品,与其他书体没有根本的区别,但狂草作品中部分单字空间融合在一起,空间组织便有了质的变化(图6),不过大部分时候单字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
我在学习、创作的过程中,随着对草书把握的深入,感到作品中线所分割的单元空间才是书法构成的关键。
我理解的草书,是一种随着书写的展开而不断生长的结构和空间。
关注有形的结构还是关注结构所围合而成的空间,本无质的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人,单字结构在日常使用中所形成的独立状态都是难以逾越的感觉模式,因此以结构为主导的感觉状态,无疑更容易受到惯习的影响,而以单元空间为主导的书写状态,更有利于破除日常应用带来的感觉模式。
也只有这种感觉状态,才能够在创作的进行中,关注到纸幅上每一空间的品质。
――这便为字空间与字外空间的融合、为书法所积累的空间成就与现代视觉艺术空间成就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当我不断粉碎对字结构的感受,把感觉的重心移到对单元空间的感觉上来时,我的视觉系统和感觉系统得到了根本的改造。
我在草书的创作中希望利用对单元空间的敏感真正破除单字之间、各行之间的界限,让作品中的所有单元空间都成为具有独立的、可以自由组织的、具有相同结构性质的空间,这些空间在作品中重新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结构,富有新意,富有表现力的结构。
书法创作必须在一次性的挥运中作出每一空间都经得起反复推敲的作品,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但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
这是我2007年一组作品中的一件(图7)。
我的书法创作差不多四五年就有一个变化,这是处在两个阶段之间的作品。
在这一阶段,我想获得两种东西:
一,线条的质感,我希望达到笔尖落纸的瞬间――第一个毫米,就有力、丰满、变化、流动,而且它是作品运动的整体、节奏的整体中的有机成分。
书法史上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二,作品中的每一个空间――笔画生成的每一个空间,都是有创造性的、协调的、有表现力的空间。
这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书法创作是一次性的操作,一件书法作品包含众多单元空间,只要有一个空间处理不妥,作品便告失败。
这对线的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2012年的作品有了新的进展。
(图8)
“邱振中:
起点与生成”展出了九件铅笔诗稿,这是其中一件。
与前面的作品相比,单字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单字之间的空间已经与其他空间融为一体。
作品似乎已经不再是单字的连缀,作品难以划分出单字的界限,只有一个空间一个空间地检索,才能勉强识别那些单字的结构。
在这件作品里,各字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它或许为草书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空间关系。
任何书法作品的书写,都有对文字的意识、线的推移、新的空间的出现一即是说,不断书写笔画、墨线往下延展、新的空间不断出现。
我在书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感觉始终集中在线的推移和每个空间的形成上。
比如“记忆中的故乡”这一行,开始书写之前,当然头脑中得出现这几个字,但是感觉中这些字的出现跟线条的推移几乎是同时进行,而通常的书写中,是意识中一个字出来后,再写出这个字;下一个字出来,再写下一个字。
大家不妨拿笔写一下“远上寒山石径斜”这几个字,注意你书写时文字的出现和书写的关系。
很容易发现,字的意义以及它的形状――标准的结构、概念化的结构先出来,然后你再去写这个字。
或者说,字义出来以后,你字的结构才出来。
但是我在写这组作品的时候,几乎一个字(不是一句诗)刚出来,笔画、空间紧接着流出,一直往前赶,甚至压着字义、催促着诗句往前赶。
原来是字义出现之后线结构开始出现,现在是文字容出现的瞬间线条便迫不及待地扑上去,没有丝毫间隙。
“迫不及待”――对,就是这样的关系。
这是一种崭新的感觉。
在感觉和书写的这种流动中,单字结构上的边界几乎彻底消失。
――笔下出现的所有空间性质没有任何区别,真正成为我所希望的性质完全相同的空间构件。
作品由此获得重新组织的无限可能。
这里当然有一个前提:
在平时的训练中已经获得自由调整空间性质的能力,以及随时把字间空间、行间空间融入其他空间的能力。
这最后的一击,不过是把文辞、线条、空间的关系再做一次调整和融合。
也许这是草书最有意思的地方:
便于连写的简省的结构和速度带来的可能性。
行书也许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它无法消弭两字之间的间隔,部空间无法完全融入周围的空间中。
它书写的速度不会对文辞的推出造成压力。
但是草书能够迅速地组织结构和空间,能够追赶着、压迫着你对字义的感觉。
这已经是书法创作中一种新的“结构-图形”生长的机制:
依然凭靠某种规定(文辞),但空间、图形随机地、不可预计地生长。
这种线与图形-空间的关系,同时呈现在我的绘画中。
在我的绘画作品中,有关图形生成的感觉更早得到发展。
原因大概是,我的绘画不拘泥于形体的准确,从而得到更多的自由,而文字结构的约束力是我在更长的时间里要去与之搏斗以致最终达到共处的东西,它在我感觉中留下更深的刻痕。
不过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这两个领域的感觉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使我不断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状态。
1995年,我在日本,任文部省外国人教师。
那时我非常喜欢色彩,准备回去以后一边教书法一边画我的油画。
课余多暇,笔墨就在手边,随手画点水墨,想为以后的油画创作准备一些构图。
就这样开始水墨创作。
一动手便停不下来。
这是最早的作品之一(图9)。
那天手边实在没什么东西可画了,我想,算了,画我的左手吧。
但是画着画着,我就不愿意老老实实地画下去了,画到指头――画五个指头太没意思了,一边想着,一边就随意画去,你看,借助笔触的动势,就这么画下来。
已经不是指头的概念了。
很多人问我,这件作品画的是什么。
它的含义,不在于你画的是什么,而在于你每一笔下去的感觉,它的空间、它推移的过程、每一笔里可能蕴含着什么。
可以说,每一笔都涉及到一个人使用毛笔的历史,而个人的历史又与毛笔使用的整个历史息息相关。
今天的讲述,我只是对个人的心理史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其实它跟我们传统中运用毛笔的历史、线条制作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7年初,我离开日本,按惯例都要做一个展览,这是为展览做的一批绘画中的一件(图10)。
这是一件墨色很淡的作品,画完以后,放在地上,一看,太淡了,好像没完成。
我没拿去展览。
我想,要加点什么,然后我又不知道加点什么,没感觉。
回国后,过了三年,打开一看,非常完整。
感觉改变了。
盖了个章,作品完成。
这件作品对于我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两点:
一位英国批评家问我,你认为中国现代水墨的标准是什么?
或者说,什么是一件好的现代水墨作品?
我说,两点,第一点,笔墨,起码要达到黄宾虹、齐白石――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准。
第二点,图形。
这个图形必须在20世纪的绘画里是新颖的、独创的。
第一点是在中国围里的比较,第二点是在世界美术史中的比较。
这里只说第二点。
我多年前就跟画画的朋友聊过。
1987年,徐芒耀刚从法国回来,住在中央美院招待所。
我那时还没调美院,正在美院讲课,也住在招待所。
我们聊起绘画,他说现在绘画太难了,拿起笔边说边比划,这种构图有了,那种也有了,你说哪一种构图世界上没有?
全有。
不是说你这个细部有一点不同,那是每件作品都会有的,我们说的是整个作品构思、方向、类别上的差异,坦率地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因为是淡墨,所以每个笔触都非常清晰,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掩盖你线条上的失误,而这件作品的空间也十分复杂,笔触叠合、交织,形成层层叠叠的空间,所有空间都不允许有任何失误。
――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外,水墨绘画,创作时墨色比成品深很多,你只能看着湿漉漉的画面对空间的得失进行判断,但留给你判断的时间很短,你不能停下来。
整个过程很像草书创作,只是笔触的重叠与草书有所不同。
《状态-Ⅶ》(图11)是我对一束千枯的百合花的速写。
那是花瓶里一大捧放了很久的百合花,千枯的花瓣和叶片形成的空间结构极为复杂。
它突然间打动了我。
我赶快把它抱到工作室,到处找纸,迫不及待。
匆忙中找到的是一叠切好的铜版纸。
大家都知道,今天没有谁会用铜版纸去作画,但我不管。
我急着要把感觉记录下来。
我一边找纸一边想,我一定要用最浓的墨,用草书的线条,把这些空间记录下来。
我在瓶花中寻找合适的局部――像邮票那么小的局部。
几分钟一。
瓶花的这一面画得差不多了,又转过花瓶另一面。
直到把那叠纸画完。
两天一共画了八十多幅。
这是其中几幅。
画这组作品非常兴奋,或者说,狂喜。
我想,这怎么是我画出来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创造图形的习惯,因此所有作品都会有一种相关性,但我绘画的结构不是这种风格,这个作品跟我原来的作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画出来的?
但它们确实是我画的,而且独特。
究其原因,这些绘画有物像作为支点,又不完全依赖物像,笔触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和个性,不受拘束,但图形生成时,我的感觉又远远地监视着图形的生长,使它处于某种图形构成原则的观照之下。
它与我的草书创作的差异就是支点的不同:
一个是文辞,一个是物像。
图形生成的过程、机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笔触的节奏和生命活力,成为图形生成的核心。
物体成为支点,感觉、笔触、图形围绕它而自由飞翔。
这种图形生成方式享有充分的自由,而新颖的图形生成方式决定了作品空间构成的新意。
(四)精微
前面我在强调细节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精微的问题。
在草书的流动感、构图的完整性上做得不错的人不少,只有我们在精微上提出要求,才能把一些最精彩的作品跟一般的作品区分开。
有一次,我与语冰聊到中国当代艺术,聊到中国跟西方的差异。
他说西方的绘画讲究精密,中国的绘画讲究韵味。
说得非常好。
我想,恐怕很多人在阅读中国美术史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受。
但是我回去接着想下去,发现中国也有细到极致的一面,但是不用精密这个词,它叫什么呢?
它叫“精微”。
“精微”和“精密”这两个词语义有差异。
精微,指的是细小、微妙,更多的倾向感觉、直觉,不可量度;精密,有细微、一丝不苟、精确的含义,与度量有关。
一个要精确到数字,一个只关心引发的感觉。
中国人很早就有精微的意识。
南朝王僧虔《书论》就讲到这么一句话:
“纤微向背,毫发死生。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差那么极小的一点,感觉就彻底不一样了。
做到这一点就是生,差那么一点就是死。
构成上极小的差异,导致作品水准的根本区别。
这是从南宋构的作品里挑出的一个“必”字(图12)。
这件作品水平不高,但它恰恰反映了宋代书写的一般状况。
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观察作品的的时候我们要细致到什么程度,才能发现问题并做出我们的判断。
分析的目的,是找到它隐含的动作和得失。
用经典作品做例,有些笔画隐含的动作太复杂,分析的准确性也难以验证;此外,经典作品与现代书写距离太远,现代书写中的缺点一般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反映。
宋代一般作品中的书写方式,与今天的书写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们按笔顺来观察。
首先是仔细观察边廓,同时分析书写时控制笔锋的部运动。
长撇承接上一字而来,起端尖细,左侧边廓有一弧形突起,右侧边廓挺拔,直至左下方笔画的顶点,部运动简单平直;向上勾出的一端,右侧光洁,左侧粗糙,显而易见,是笔锋处于右侧的偏锋所致,作者对上挑的动作信笔为之,未加控制;接下来的笔画,基本保持中锋,接近右下角时,上侧边廓有一段枯笔,这是因为速度过快,墨水跟不上所致,转笔没有停顿,与前一端笔画感觉保持一致;中间一点承接上一笔按下,向右下方运行,到达位置后紧接着向左下方撇出,笔毫分布的宽度占笔画长度的一半,且笔毫分叉,挑起时并无控制笔毫椎体的动作;其后左右两点,流畅而有弹性,但均是简单地按点画外部轨迹运行。
这样的观察、分析,使我们触摸到作者书写时的动作。
如果挑选若干不同时代的作品进行分析,对中国书法笔法部运动演变的历史会有一清晰的了解,也可以由此对当代书法创作有一深切的认识。
这样细致的观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做到很多原来以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会让我们发现很多从来没被注意过的重要特征,重新构建书法的历史和批评。
今天我只能简略地说到这些。
关于“精微”,再举一个例子。
黄庭坚《砥柱铭》(图13)的真伪,是个争执不下的事情。
在这里我只指出一个细节。
这件《砥柱铭》所有的捺笔结束的时候,笔尖都画出一个很小的额外的弧线。
但是搜检黄庭坚其他所有作品,在长捺结束时,笔尖的指向就是这个笔画所指的方向。
没有人指出过这个细节的差异。
我们可以断定,《砥柱铭》的捺笔反映了书写者潜意识中的书写习惯。
一个人潜意识中的书写习惯,一定会表现在他所有的书写中,至少是他某一时期的书写中,而不会仅仅出现在某件作品中。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对精微的关注,能解决许多不同方向的关于书写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精微”和“精密”在汉语中语义的差异。
刚才已经讲到,由“精微”我们会想到精妙、微妙,而“精密”使我们想到的是“一丝不苟”、“不差分毫”。
像这样一件绘画,它是罗伯特?
曼戈尔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图14),高3米,宽5米,就几个色块,几个单线图形,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是作品有一种精密,令人惊叹。
你不能设想移动其中某个构成元素――哪怕极微小的一点,还能保持原有的精彩。
它的精密与中国的精微有相同的地方:
完成的作品中,任何构件都不能相差分毫。
但是西方的这种精密是一种静态的平衡――暂且这样说,中国的精微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构成元素的运动性质让人感到它随时会脱离这种平衡状态。
有一篇传为颜真卿的文章,叫《记旭笔法十二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笔画的失误可以补救,也就是说当这笔写得不太理想的时候,可以在别的地方补救过来。
这是中国式精微的一个例子。
我有时候去观察一棵树或者思考一棵树:
我们没见过世界上两棵一模一样的树。
肯定是没有的。
为什么?
原因可能并不复杂:
生长。
生长是一件永远不会重复的事情:
有机体的生长受到极为复杂的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书法 中的 书写 图形 生成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铝散热器项目年度预算报告.doc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