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docx
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docx
- 文档编号:11324262
- 上传时间:2023-02-26
- 格式:DOCX
- 页数:23
- 大小:39.26KB
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docx
《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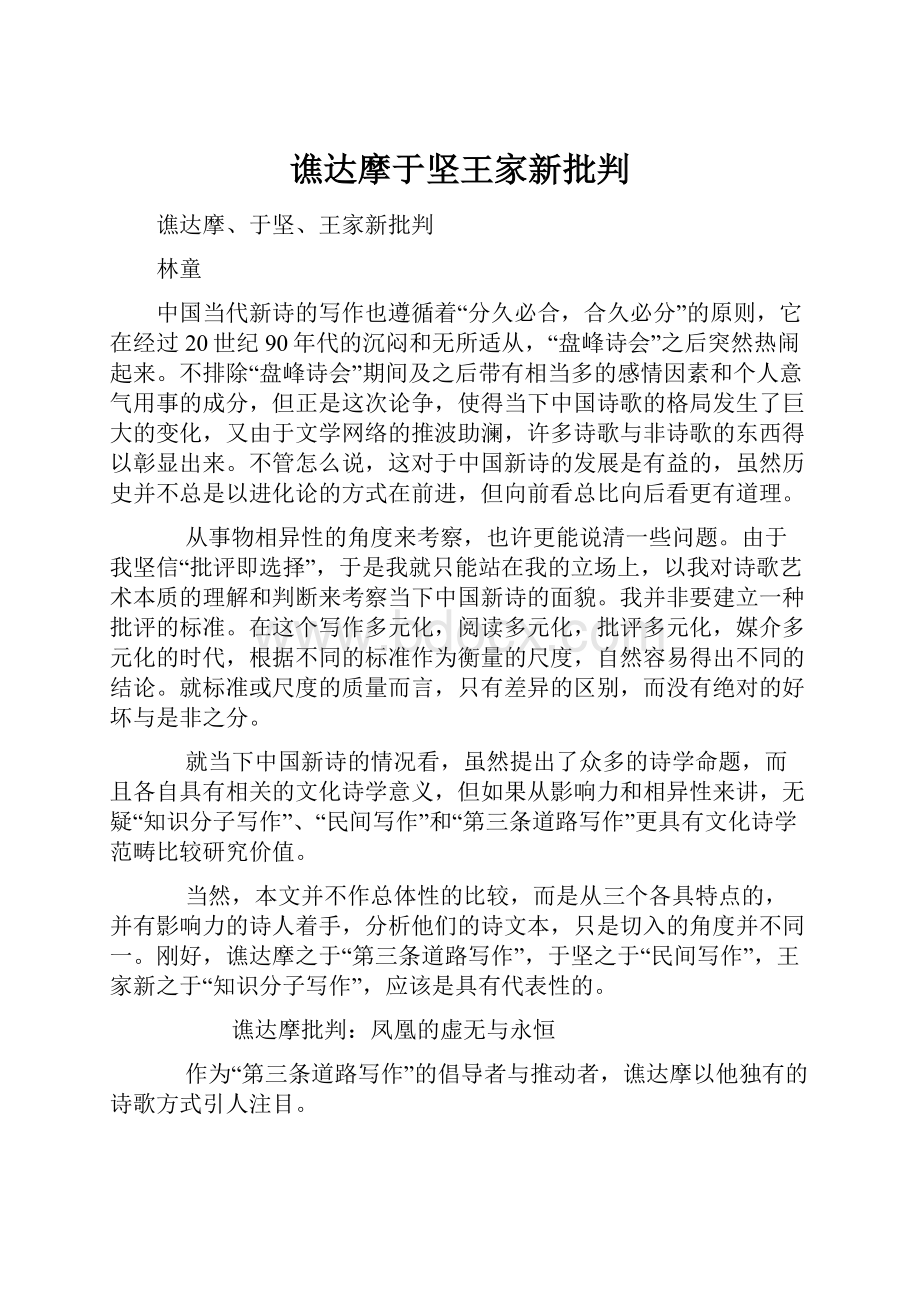
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
谯达摩、于坚、王家新批判
林童
中国当代新诗的写作也遵循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原则,它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沉闷和无所适从,“盘峰诗会”之后突然热闹起来。
不排除“盘峰诗会”期间及之后带有相当多的感情因素和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正是这次论争,使得当下中国诗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又由于文学网络的推波助澜,许多诗歌与非诗歌的东西得以彰显出来。
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有益的,虽然历史并不总是以进化论的方式在前进,但向前看总比向后看更有道理。
从事物相异性的角度来考察,也许更能说清一些问题。
由于我坚信“批评即选择”,于是我就只能站在我的立场上,以我对诗歌艺术本质的理解和判断来考察当下中国新诗的面貌。
我并非要建立一种批评的标准。
在这个写作多元化,阅读多元化,批评多元化,媒介多元化的时代,根据不同的标准作为衡量的尺度,自然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标准或尺度的质量而言,只有差异的区别,而没有绝对的好坏与是非之分。
就当下中国新诗的情况看,虽然提出了众多的诗学命题,而且各自具有相关的文化诗学意义,但如果从影响力和相异性来讲,无疑“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更具有文化诗学范畴比较研究价值。
当然,本文并不作总体性的比较,而是从三个各具特点的,并有影响力的诗人着手,分析他们的诗文本,只是切入的角度并不同一。
刚好,谯达摩之于“第三条道路写作”,于坚之于“民间写作”,王家新之于“知识分子写作”,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
谯达摩批判:
凤凰的虚无与永恒
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倡导者与推动者,谯达摩以他独有的诗歌方式引人注目。
从年龄来看,出生于1966年的谯达摩与于坚、王家新并不属于同龄人。
按照目前流行的诗歌史的划分观点,于坚、王家新在“第三代”,谯达摩在“中间代”,似乎比较研究的基点不好确定,但由于有了“盘峰诗会”,诗人年龄的差别根本就不构成任何问题。
谯达摩的诗歌写作,并不存在对事物重新命名的焦虑,而且也不会对他的创造性构成负面影响,相反,他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处理得相当从容。
这得益于中国诗歌传统的滋养。
我现在理解的反传统,并非将传统从我们的意识与思维中驱逐出去,更不可能从我们的血液中加以彻底的清理,甚至于也无法真正区分出哪是精华哪是糟粕,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人们总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混为一谈。
我也不赞同所谓的“古为今用”,表面看来这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实是典型的工具论。
科学技术可能是按照进化论而不断地向前发展,文化则未必如此。
因此,反传统不是简单的继承,也不是说超越就超越了,而是创造。
无论是作为诗歌写作者,还是作为诗歌研究者,都不应该忽视谯达摩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我现在主要谈他的长诗《凤凰十八拍》。
它的题记很有意味:
“凤凰”夜半犹啼血
不信“东风”唤不回
这是从“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得到的启发。
这首诗完成于2000年6月,它正是谯达摩在“盘峰诗会”之后思索的重要诗歌文本。
在对“盘峰诗会”的看法上,我和谯达摩并不一至。
我在当时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观察着中国诗歌的变化,自认为没有处于云遮雾罩之中,而且“盘峰诗会”后中国诗坛的格局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是从相对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其意义的:
无论是从诗歌史的角度,还是从诗学命题的角度,它的确成为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分水岭!
从诗学命题来看,这次会议之前,似乎只有一个已用了十多年的“第三代”,在这之后,诸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九十年代诗歌”、“个人化写作”、“口语写作”、“70后诗歌写作”、“下半身”、“中间代”、“荒诞主义诗歌”等等,虽然被有的人讥为这是一个“命名”的时代,好像具有占山为王的味道,但是,不论是“真命题”也好,还是“伪命题”也罢,只要被命名,它必然有其合理性,而且总要比命名的缺失好。
一般来说,只有学霸或惰性极强者才不希望旧的格局被打破。
我认为文学的命名往往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随意性,很难符合科学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反科学主义的。
谯达摩认为,“盘峰诗会”是一场闹剧,他是就“盘峰诗会”本身而言,正因为如此,那个时候,他和莫非、树才等投入了相当的激情从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建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题记”所包含的信息了。
不过,真正具有文化诗学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以2000年出版的《九人诗选》为其标志的。
2000年9月底,我与谯达摩的相识,预示着“第三条道路写作”必然要向诗歌艺术本质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演进。
事实证明,正是我与达摩的共同努力,才使“第三条道路写作”不至于断裂或夭折。
这种焦躁感表明:
谯达摩的确是一个诗歌使命感很强的诗人。
它恰好与正诗的从容构成明显的对照。
这部长诗是借助了小说的结构与音乐的结构。
第一拍 序曲:
凤兮凰兮。
凤与凰在火焰之上获得新生。
第二拍 凤求凰。
春天苏醒后的讯息。
第三拍 婚礼进行曲。
凤与凰在充满禅意的热闹氛围中进入洞房。
第四拍 孕育。
新的凤凰在时间与空间中孕育。
第五拍 诞生。
新凤凰的诞生。
第六拍 童年协奏曲。
凤凰童年的故事。
第七拍 成长。
凤凰的成长过程。
第八拍 漫游。
凤凰游学。
第九拍 劳动圆舞曲。
凤凰的耕耘与收获。
第十拍 太阳。
凤凰在思考与行动。
第十一拍 月亮。
凤凰被迫远走他乡。
第十二拍 森林浪漫曲。
寻找新的道路。
第十三拍 闪电。
凤凰的灵魂慢慢复活。
第十四拍 霹雳。
凤凰涅槃
第十五拍 寰球之舞。
凤凰在舞蹈。
第十六拍 插曲:
凤兮。
凤的新思索。
第十七拍 插曲:
凰兮。
凰的新思索。
第十八拍 世界交响曲。
凤凰的新世界。
但它仅仅是借助了小说的结构,在这个看起来很完整的故事,实际上叙述方式却并不真的完整。
因为这部诗的目的并不是要给读者讲故事,在本质上它还在于抒情。
结构上的叙述与内容上的抒情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尝试与创造。
我曾给这种类型的诗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抒情史诗”。
这个叫法是否恰当,还可以讨论。
如果我们非要从诗歌叙述学的角度来考察,其实也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和传奇色彩的世界。
虽然其间也有凤凰的涅槃,但与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比起来,要明快得多,全然没有那种悲剧英雄的激昂和环境的压力,因为《凤凰十八拍》叙述的是凤凰的成长过程,其主题是:
寻找。
我们也能够看出,谯达摩在诗中对音乐的思考。
现在,仍有不少人在批评诗缺少读者的时候,认为是诗歌写作者的问题:
不好懂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诗离音乐越来越远。
殊不知,这与诗歌写作者关系并不大。
人们没有看到诗与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这与传播媒介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在传播媒介还不发达的远古时期,诗歌不分家,不只是中国为诗的泱泱大国,西方的文学正宗不也是诗歌吗?
只不过还有与诗歌走得很近的戏剧。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印刷术的改进,使得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长篇小说的兴盛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诗已不再是唯我独尊的文学样式了。
我们注意到,明清时代是我国长篇小说的时代,它与西方工业革命是同步的,这绝对不是巧合。
而科学技术的革命,它的影响更深广。
当电视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进入了所谓的读图时代,诗从前台走向幕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歌却借助于传播媒介的东风与青春激情的歌星,几乎可以零距离地与读者(观众、听众)沟通。
民众是需要狂欢的。
因此,那些认为诗要如何如何的想法,的确是出于良好愿望的一厢情愿。
很明显,诗很难再借助于音乐的壳重新回到大众,除非是为了某种需要,由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强制执行。
这并不是说,诗与音乐就真的绝缘了。
重建诗歌的音乐精神,我的理解是:
诗完全能够借助音乐的成分,丰富诗歌的表达手段。
《凤凰十八拍》对音乐的借鉴,的确很有特色。
它不但体现在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借鉴,还表现在对西方音乐的借鉴上。
从总体来看,它是一部大型交响曲,而在每一拍中,也是由音乐组成。
只要看看这些小标题就知道了:
婚礼进行曲、童年协奏曲、劳动圆舞曲、森林浪漫曲、世界交响曲。
可以说,《凤凰十八拍》对音乐的借鉴,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这可以理解为是对诗歌音乐精神的复活。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长诗在结构上,并不只为我们提供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再深入研究的话,还会发现它相关的特征。
从整体来看,它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构形式,但各拍的结构方式,因内容的变化而并不相同,使得全诗既整饬又富于变化。
以第一拍的第一、二意义单元为例:
凤兮:
在火焰之上诞生 在火中 凤兮:
在火焰之上睡眠 在火中
收集灵魂 骨架 大陆架 娶妻生子 劈柴
斜斜插入大海 凤兮:
在火焰之上 挑水 在火焰之上:
凤兮
飞翔 在火中歌唱:
凰兮 凰兮 凰兮 研究所有的火 从红色开始
凰兮:
在火焰之上漫游 在火中 凰兮:
月亮在火焰之上
打开天窗 打开世界之门 寻找太阳 在火中
蜜蜂飞进来 蝴蝶飞出去 编织花篮 观赏花轿
凰兮,凰兮,弹奏火焰上古老的琵琶 太阳的花轿 凤的花轿
(这是第一个意义单元) ( 这是第二个意义单元)
这两个意义单元,以及后面的三个意义单元,都是每段四句,在诗句的构成上,相似性很明显,这也适宜于后面的各拍。
在意象的营造上,“火焰”的意象不断地出现,成为本拍的中心意象。
但对于这一中心意象的理解,可能会因人而异,它因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因而意义丛生。
同时,凤与凰相互构成互文性,它指凤与凰所在的内容是可以互换的,并且是可以合并的,即凤与凰在火焰之上诞生、漫游、睡眠,在火中做相关的事。
按照常规的叙述方式,既然凤与凰才从火焰之上诞生,那么后面就应该叙述它们的事了,可是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它们的出场只不过是为了孕育新的凤凰。
“凤求凰”,在理解为两性相吸与两情相悦的同时,自然容易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存在原型性的影响,但在谯达摩的诗中,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女性的光芒。
最具典型的,恐怕要算他的代表性作品《穿睡衣的高原》:
此刻睡衣醒着,收藏蝴蝶和钻石。
这是依山傍水的宫殿
点一盏煤油灯可以龙飞凤舞,两盏灯可以升天。
此刻溶洞湖湿。
此刻她如鱼得水
她的睡衣突然被风拿走。
迷醉的山峦扑面而来。
漫山遍野的羔羊,啃着青草的乳房。
这首描述大自然的诗,的确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山水诗有很大的不同,亲切而温和,充满想象力。
这是“一种收割灵魂的吟唱”。
如果《穿睡衣的高原》还具有某种私秘性的话,《凤凰十八拍》则完全是开放性的,似乎凤凰世界都在狂欢:
春天苏醒 一万亩荷花 这是春天唯一的信息
走进十万亩湖泊 所有的荷花
凤在飞 凰在唱 同时面对太阳
一万只凤飞向十万只凰 所有的凤同时面对凰
凤求凰兮:
凰以荷为裳 (同左)
以太阳为方向
凤求凰兮:
凤以整个大海为家
以滚滚波涛为床
后边只是单节有所变化,而变化也是有规律的,双节则完全一样。
其中心意象为“春天”、“荷”、“太阳”、“大海”。
或许正是这样的结构方式,这一拍非常适合于朗诵,并具有波涛一般的气势和效果。
很有意味的是,如果说在“凤求凰”中体现着“道”以及浪漫主义精神,那么“婚礼进行曲”,却处处弥漫在佛教的关怀之中:
“绿叶”、“红花”、“木鱼”、“袈裟”、“观音”、“菩萨”、“禅林”、“宝塔”,等等。
最初接触这部诗时,我也感到迷茫不解。
其实,很多地方的民俗不就是这样的么?
如果非要寻求其文化上的隐旨,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不正是儒佛道的冲突与融合吗?
另方面,这与谯达摩研究佛教文化相关。
而在“孕育”中,用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时间”、“空间”为中心意象,由名词性短语来结构,形成急促而期待的节奏。
在时空之中,新的凤凰诞生了。
虽然还很弱小,但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厚的土壤。
在归属上:
“祖父的凤凰 父亲的凤凰 我们的凤凰”;在时间上:
“黄昏的凤凰 子夜的凤凰 黎明的凤凰”;在根植上:
“泥土的凤凰 小草的凤凰 大树的凤凰”;在季节上:
“春天的凤凰 夏天的凤凰 秋天和冬天的凤凰”;在光与热上:
“太阳的凤凰 月亮的凤凰 星星的凤凰”;在文化上:
“孔子的凤凰 耶酥的凤凰 释迦牟尼的凤凰”。
到了“童年协奏曲”,泛化的凤凰回到了具体,成为谯达摩的自叙传。
在1966年4月,“拉着一车翅膀 拉着一车理想”的凤凰,从群山到黄土高坡,再到河流、乡村、城市,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却“找不到方向”。
然而凤凰的“成长”,却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曲折,这种轻松愉快的语调,我甚至怀疑这才是童年的生活。
难道是在交响乐的演奏中,需要一种乐器的独奏?
所以“漫游”不但回到了集体演奏,而且更是万方乐奏:
古今中外的科技、文化、经济、历史、军事、体育、自然、文学、艺术等,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凤凰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漫游,的确大开眼界。
这些纷至沓来的意象群,因以词语的方式出现,真是电闪雷鸣,万马奔腾。
差一点也成了“词语的集中营”。
凤凰的漫游也收获颇丰,但它并不满足以往的成就,不以过去有多么辉煌而洋洋自得。
或许那些耕耘与收获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所以要重新估量一切价值!
“火焰”失去了自由,凤凰也只得“怀抱灯笼 远走他乡”,需要一次重要的蜕变,就必然要寻求新源泉。
新的道路在哪里?
“凤凰的道路一直通向湖泊”。
湖泊是凤凰的道路吗?
这与“朦胧诗”有无关联?
因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岛的“深不可测的眼睛”,但那是因为“迷途”的缘故,这是否暗示了谯达摩的困惑?
显然,必须要有新的变异的因子,才可能出现新的基因,才能够进行重新选择。
而似乎在突然之间,“闪电”来了。
闪电,它暗示着秩序的变化:
毁灭与重生。
闪电前的环境,虽不能说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或是除了过度的欲望就了无生机的“荒原”,但九十年代诗歌的不断沉沦与诗人们“惶恐滩头说惶恐”,构成九十年代诗歌的风景线。
也许,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九十年代的诗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自我暗示的结果,这源于诗人与诗评家浓厚的“悲情情结”。
凤凰觉得方向的迷失,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幸并没有随波逐流,而在反思:
“时间之箭环绕太阳/内心无限光明/凤凰的内心无限光明”,而在“时间之箭不知去向”后,“凤凰的灵魂慢慢复活”。
“闪电”必然要伴随着“霹雳”。
在雷霆中,凤凰才能真正脱胎换骨。
按说,为了与雷霆万钧的气势相对应,行文也应该汪洋恣肆,但这一拍却显得非常平静,由两句具有对应关系的名词性短语组成一段:
山的声音
水的声音
“声音”为中心意象,其它的部分只是变换修饰性成分:
种子与泥土,真与善,云与雨,血管与骨头,塔尖儿与木鱼,白莲花与舍利子,磨刀人与磨刀石,秃鹫与菩提,鸟与虫,太阳与月亮,陆地与海洋,永恒与虚无,火与光,天堂与地狱,然后又回到山与水。
在这个过程中,凤凰完成了轮回,孕育,成长,合欢,参禅,剃度,修行,体验,念经,超度,云游,打通经脉,彻悟,羽化,普度,并涅槃。
外在的喧嚣已内化为内心的平静,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从容。
重获新生的凤凰,以轻快的步伐舞蹈,从东西方吸取日月精华。
凤与凰,在火焰深处,开始了建设。
第十六、十七拍,结构方式一样,虽然仍以“火焰”为中心意象,但与第一拍相比,已深化与升华。
所以,凤在火中:
“掏空一切:
鼻孔,耳朵,小肠和大肠”;“尊重一切:
姻缘,命运,线和绣花针”;“领略一切:
高原,草原,盆地和沼泽地”;“品尝一切:
空气,水,肉和果核”;“关心一切:
吃饭,穿衣,天文和地理”;“点亮一切:
晨昏线,煤,乌鸦和海底隧道”;“浇灌一切:
生命,爱情,珍珠和玛瑙”;“倾听一切:
福祉,苦难,高山和流水”;“化解一切:
狂风,暴雨,癌和梅毒”;“分析一切:
松脂,琥珀,金环和银环”;“恢复一切:
火柴,纸,信仰和崇高”;“麻醉一切:
烟枪,嘴唇,贪婪和权力”;“感悟一切:
土地,森林,秋天和死亡”。
凰在火中:
“洗濯一切:
灰尘,毛细孔,蕾和根须”;“采撷一切:
露水,营养,红豆和相思梦”;“清理一切:
吸尘器,庭院,小路和大路”;“点缀一切:
日常生活,工作,睡眠和理想”;“垂钓一切:
倒影,涟漪,网和篷船”;“孕育一切:
友谊,春天,幸福和万家灯火”;“捕捉一切:
萌芽,花蕊,心跳和火烧云”;“解放一切:
青春,小蛮腰,诗歌和信天游”;“阐释一切:
风铃,乳房,地震和活火山”;“烹调一切:
履历,档案,人生和墓志铭”;“拯救一切:
罗曼蒂克,美,玻璃和花岗岩”;“珍惜一切:
岁月,粮食,彗星和沧海桑田”;“完成一切:
冰雕,飞翔,雪和小小寰球”。
这两拍完全可以互换,实际上,它们本身就是互文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表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
一种新的秩序被建立,我们注意到,这种新的秩序并不是唯我独尊的。
在凤凰的世界里,凤凰并不是百鸟之王,而是劳动者,既有神性,也有人性。
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其实,它所具备的意义在于:
人人都可为凤凰。
这当然也是一种乌托邦。
实在不难理解谯达摩在阐释“第三条道路写作”时,表明“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道路”了。
以虚无与永恒为文化理念,达到“从虚无开始,到虚无结束”,“从永恒开始,到永恒结束”。
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即整体”的命题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如果仅从单个作品来看,可能会对某些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但如果我把眼光放开一些,无论从横向还是从纵向进行比较研究,许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那些既表达时代并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只要不是纯粹为了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又超越了时代精神,而且够得上真正意义的文学文本,便很可能具有永久的价值。
它们对后世的影响,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汉代女诗人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对《凤凰十八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最有比较的意义,还应该是现代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
这种影响的积极因素就在于:
谯达摩从《胡笳十八拍》与《凤凰涅槃》吸取了供自己创造的营养。
而“影响的焦虑”对他似乎根本就不算一回事。
的确,我们见识过无数的案例:
在学习别人的时候,不但表现为“影响的焦虑”,更有甚者,完全被他人的汪洋大海所淹没。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在于个人,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群人,甚至一个时代。
难道我们真的就如此缺乏创造性?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胡笳十八拍》是一个真正的诗歌文本,《凤凰涅槃》是一个真正的诗歌文本,而《凤凰十八拍》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诗歌文本。
于坚批判:
乌鸦在雄辩
平心而论,我并不喜欢于坚的诗!
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忽视于坚的诗,尽管他的名气很大,也为许多人推崇。
曾有几次,我试图去读,比如《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零档案》,还有其它的很多诗歌。
多是读了几行就放弃了,所以我只记住了他的诗歌的标题,究竟写出了什么,很隐隐约约。
这绝对不是出于我对于坚诗歌的偏见,相反,我一直对敢于创新和能够创新的人心存敬意。
可以说,于坚正是在朦胧诗为自己争得地位的时候,他已完成了对朦胧诗的转变。
我注意到,从年龄来看,出生于1954年的于坚,甚至比顾城还大两岁,完全可以算是同龄人,而且我也相信于坚在写作的初级阶段,深受朦胧诗的影响,并从朦胧诗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因此,于坚对诗歌的敏感力是非常锐利的。
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于坚的“作品xx号”中。
比如《作品1号》:
“在那个黄颜色的阳台/和一只美丽的蚊子/我深深地相爱”。
我们很难想象朦胧诗中会出现这样的意象,即使出现这种意象,也会用“蚊子”业已形成的传统意义,把它当作坏的典型。
在这一点上,朦胧诗与意识形态的写作并没有在话语上区分开来,因为它们都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济世情怀。
只是意识形态的写作要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把个人情感从诗歌中放逐出去,而只允许空洞的公众情感横行无忌。
为于坚获得诗名的是《尚义街六号》。
不知为什么,我在读这首为人所推崇的诗歌时,一下子就想到了李亚伟的《中文系》。
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极为平常的生活场景,而且这些生活场景与大家的生活状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让人惊呀:
嘿,诗歌还可以这样写!
这似乎说明,生活就是诗:
尚义街六号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
打开烟盒 打开嘴巴
打开灯
不要说在当时,就是现在,这也是很多城市所拥有的现实。
虽然于坚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但我们已从他的环境描写中看到:
生活场所之恶。
奇怪的是,老吴这个人物出场之后,只来了一个特写,就消失了。
而有关恶劣场所的背景介绍,主要还是为了表达于坚的情绪:
“墙上钉着于坚的画/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凡高”。
我没有见过于坚的画,估计不太有特色,不然,于坚就不会放弃绘画而走诗歌写作和散文写作之路了。
当然,这未必就是说自己的画不被人欣赏,如此理解也太拘泥于凡高这个人物所传递的信息。
而应指于坚的诗不被人们所接受和欣赏的苦恼与不平,因为这种情绪在后面还有表达:
“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
于坚是自信的:
“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
的确,人们在谈论于坚早期的诗歌时,很容易谈到《尚义街六号》。
这首长达九十多行的诗,并没有分段,虽然它讲了几件事。
老卡、李勃、老吴、于坚的事构成了意义相对独立的单元。
如果稍微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全诗的结构比较混乱。
这不仅仅指它该分的地方没分,更重要的是指其叙述的混乱。
以第一层次为例,在“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房子”之后,老吴的出场本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在老吴刚一露面,马上就转到对大厕所的描写,而要知道老吴这个人的情况,却要在李勃的故事中了,使得老吴的出场突兀而没有用处,反而对诗的结构有极大的损伤。
如果我们把这首诗当作一个整体结构来看的话,它与现实主义小说及中国古代小说倒很相似。
我是指这首诗叙述的琐碎及作者的出场。
在传统小说的叙述中,作者(叙述者?
)往往忍不住要出来发表高见。
当然在本诗中,涉及到于坚的地方,做到了有节制的牢骚满腹,以一个弱者的面目出现,往往能博得人们的同情。
实际上,这首为于坚带来声誉的诗,除了它本身的特色以外(取材与叙述既不同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诗歌,也不同于已引起广泛关注并开始取得话语权的朦胧诗),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于坚所传达的姿态,因为在当时,第三代诗人处在意识形态诗歌与朦胧诗的双重压力之下,自然要为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达摩 坚王家新 批判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冰豆网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Java程序设计》考试大纲及样题试行.docx
《Java程序设计》考试大纲及样题试行.docx
